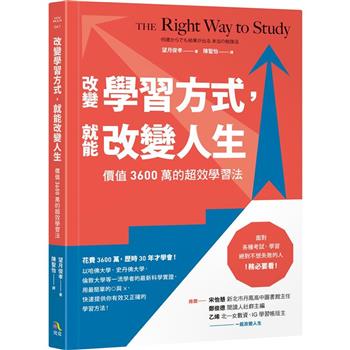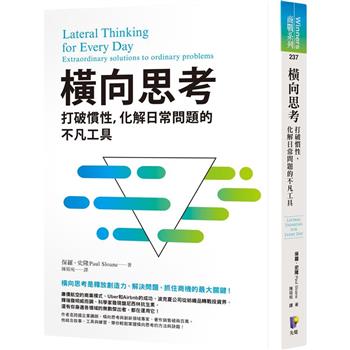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緬甸就像一個得了癌症的女人。她知道自己病了,但她還是照常過她的生活,彷彿一切沒事一樣。她拒絕看病。她與人交談,人們也跟她說話。他們知道她得了癌症,她也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但沒有人說破。」
北韓之外,另一個備受關注的極權國度:緬甸
半世紀的軍事統治,讓曾是世界糧倉的緬甸陷入民不聊生的慘境,也成為一個全民受到嚴密監控、真實與虛假難以區分的詭異之地。緬甸政府不但關押數量龐大的政治犯,2008年的納吉斯風災也因為獨裁者的無能與阻撓,造成14萬人死亡。2010年底,長期遭到軟禁的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終於獲釋,2012年初再次投入選舉,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個飽受蹂躪的佛塔之國,是否能順利開始轉變?
名列二十世紀偉大政治小說家的歐威爾,年輕時曾在緬甸駐紮五年,擔任帝國警察,然而甚少有人提及這段經驗對他小說創作的影響。他的《緬甸歲月》、《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宛如現代緬甸悲劇歷史的寓言三部曲,緬甸知識分子也因此稱他為「先知」。
本書作者拉金是通曉緬甸文的美國記者,從九○年代起多次祕密到緬甸查訪,她透過走訪歐威爾在緬甸的駐紮路線,對緬甸社會進行第一手觀察,甚至與當地知識分子組織讀書會。拉金以優美的遊記散文,娓娓道出緬甸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到被軍政府極權統治的悲劇;不但巧妙銜接歐威爾的生平著作與緬甸的政治社會境況,更生動呈現了當地人在高壓統治下的一言一行。
作者簡介:
艾瑪.拉金(Emma Larkin)
艾瑪.拉金是一位美國記者的化名。她在亞洲出生、成長,在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學習緬甸語文。以曼谷為基地,廣泛地以亞洲為採訪報導的對象。從一九九○年代至今至緬甸多次進行私下採訪。除了本書,亦有《萬事皆壞:緬甸的災變故事》(Everything is Broken: a tale of catastrophe in Burma)。
譯者簡介:
黃煜文
資深譯者,譯有《王者之聲:宣戰時刻》、《鴨子中了大樂透》、《為什麼是凱因斯?》、《歷史的歷史: 史學家和他們的歷史時代》《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等多部作品。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秘書長/楊宗澧 專文推薦
楊照、張鐵志、張娟芬、胡晴舫、鴻鴻、賴樹盛、柯智豪、董事長樂團、孫友聯、閃靈Freddy 齊聲力挺
媒體推薦:
具高度原創性的獨特之書……第一流的旅行文學。
──《華盛頓郵報》
哀傷、引人深思且氣質獨特的融合之作,既是文學查訪也是政治遊歷,不僅以緬甸詮釋歐威爾,也以歐威爾(特別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詮釋了現代緬甸的悲劇。
──《紐約時報》
研究透徹又迷人……傑出。結合了文學評論與堅實的田野報導,拉金捕捉了緬甸最好與最糟的一面。
──《舊金山紀事報》
一本嚴肅的、報導文學的回憶錄……機敏、好奇的拉金其實根本不需要歐威爾的幫忙,來描繪這個她深愛的國家輝煌卻令人沮喪的肖像。但她的技法確實非常好,有時還非常深刻……是這個國家與其人民不安的側寫。
──《新聞週刊》
這是好一陣子以來,有關東南亞最與眾不同的旅行記述,它所呈現的威權體制圖像,比任何一位作者(甚至歐威爾本人)所寫過的要更加真切。
──《Mother Jones》
名人推薦: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秘書長/楊宗澧 專文推薦
楊照、張鐵志、張娟芬、胡晴舫、鴻鴻、賴樹盛、柯智豪、董事長樂團、孫友聯、閃靈Freddy 齊聲力挺
媒體推薦:具高度原創性的獨特之書……第一流的旅行文學。
──《華盛頓郵報》
哀傷、引人深思且氣質獨特的融合之作,既是文學查訪也是政治遊歷,不僅以緬甸詮釋歐威爾,也以歐威爾(特別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詮釋了現代緬甸的悲劇。
──《紐約時報》
研究透徹又迷人……傑出。結合了文學評論與堅實的田野報導,拉金捕捉了緬甸最好與最糟的一面。
──《舊金山紀...
章節試閱
威權的烙印
──深入緬甸的社會觀察
楊宗澧(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秘書長、臺灣自由緬甸網絡發言人)
「思想罪不會帶來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最為人熟知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中,這句話彷彿預告了緬甸自一九四八年獨立以來,這國家將發生的諸多苦難都將來自「思想」。「老大哥」所帶來的無數良心犯,在整個緬甸社會當中至今仍是許多人的禁忌話題,卻也是許多緬甸人民永遠的印記──威權的烙印。
《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出版於二○○五年,書中密集引用《一九八四》作為「參考圖像」映射出當今的緬甸社會面貌,每章的標題都帶著讀者來到不同地點或地景看見如斯壯麗的緬甸,卻也同時在文首摘以許多《一九八四》語錄,隱喻緬甸社會內部的種種現象。作者艾瑪.拉金(Emma Larkin)在書中交錯著《一九八四》的情節與緬甸的真實人權景況,從虛幻的小說情節帶出緬甸人民荒誕無常的人生場景,威權體制下的軍人政府化身為「老大哥」,帶來了迫害異議人士、強迫勞動、種族清洗等人權侵害危機,這是緬甸多年來不變的殘酷事實,即使直到二○一二年的今天,當軍人改穿西裝,當翁山蘇姬獲釋,當歐美日等國家恢復與緬甸交流,難道這世界真的以為這座「監獄」就此改變嗎?你以為看到的「改變」稱得上「改革」嗎?不!緬甸確實是「變」得更快了,但真實的人權迫害現象並未完全改變,至少還沒改善到你可以忽視緬甸人權的地步!現在的緬甸,與其說有所變化,無寧看成是種變「幻」,一種虛實難料的改變。
我雖曾在二○○七年與非政府組織人士親自到過一趟泰緬邊境的湄宏順(Mae Hong Son)難民營,與緬甸難民短暫接觸訪談,這幾年也多次在泰國曼谷、泰緬邊境的美索(Mae Sot)與各緬甸海外流亡團體及各國非政府組織進行交流,但直到二○一一年,在臺灣一群長期聲援緬甸議題朋友的支持下,以及透過香港、泰國、緬甸等不同網絡組織的居間聯繫協調後,我才真正有機會踏上緬甸這塊土地進行第一手的社會觀察。
這趟緬甸旅途,陪伴我的恰好也是歐威爾的書,另一本較不為人關注的《緬甸歲月》。我在緬甸為期兩週旅行,一方面透過《緬甸歲月》發掘過去的殖民主義場景,一方面真實觀察到現實緬甸的「變幻」正真實發生。在仰光、曼德勒等大城的街道上,破舊殖民建築與資本主義下的現代大樓交織在城市中,即使離開仰光、曼德勒等大城,發展主義已成了另類殖民,其鑿斧之深隨處可見,沿路上我觀察到不少大型開發工程,而當中從事勞動的不少是老人、婦女及兒童,外資發展帶來的是環保衝擊、強迫勞動、強迫拆遷、社會不公與貧富不均的經濟人權危機。二○一一年以來的緬甸「開放」,只見帶來的新一波人權危機將是環境的、經濟的、社會的,也更加是全球性的。緬甸,此刻正在複製許多發展國家的鐵牢籠。
此外,與當地異議人士所屬地下團體以及政治犯家屬訪談後,則驗證了我談到關於「變幻」一詞對於改變「幻滅」的憂慮。在街頭,你會發現商品化的「切.格瓦拉」頭像在此已置換成「翁山蘇姬」,印有翁山蘇姬的T恤、海報以及月曆等各式商品隨處可見,甚至每天也可在各類報章雜誌看見斗大的翁山蘇姬照片輔助以新聞標題;與幾位異議人士會晤時,他們也坦言政治情勢確實有所鬆綁,異議者被政府「監視」的程度降低許多,所以此行我才得以在較為不緊張的政治氣氛下與異議人士及政治犯家屬碰面,否則以過去幾年來說,為了保護政治犯家屬的安全,通常是難以進行訪談的。然而,一般人所看不見的緬甸,雖有少數好消息,壞消息卻還是更多,在與政治犯家屬的訪談過程中,緬甸監獄內部的人治現象勝過法治,每所監獄管理方式不一,政治犯遭受的待遇也就不盡相同,獄中許多政治犯的醫療與健康情形不佳或遭受酷刑仍時有所聞,人民在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司法上公平受審的基本權利,充其量只能看到一絲曙光,然而這幽微的光亮,稍一不注意,隨時可能被「老大哥」一把吹熄,事實上,歷史也告訴我們,即便是翁山蘇姬,釋放後又再遭軟禁的事件仍殷鑑不遠。
長期以來,臺灣主流媒體普遍並不重視國際議題,距離臺灣飛行時程只有四個小時不到的緬甸,當然更不容易有機會獲得主流大眾的亮點關注,而中文資訊的缺乏,也自然使許多人對這封閉的國度理解有限。如今,令人慶幸的是使用中文的讀者終於有機會透過艾瑪.拉金的第一手資料,從她深刻的文字描述來目擊緬甸。
艾瑪.拉金,雖然是一位美國記者,但她在亞洲出生、成長,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唸書期間學習緬甸語,此後選擇在亞洲地區展開她的記者生涯,近十幾年來,她多次進出緬甸,終於在二○○五年出版《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這是一本打破旅行文學界限的遊記,艾瑪.拉金沿著歐威爾當年的緬甸足跡,重新以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角度,對緬甸社會進行深度考察。而近年來,臺灣已興起一股國際志工熱潮,許多臺灣年輕人奔向泰緬邊境或緬甸這陌生的國度進行「志願服務」或「公益旅行」,藉由這一本書,或許可以讓許多年輕讀者,得以從更廣的視角,深入窺見並認識緬甸,也期待有一天,更多來自臺灣或其他華文世界的旅人,從亞洲出發,開始書寫更多關於緬甸社會的變遷紀錄。
威權的烙印
──深入緬甸的社會觀察
楊宗澧(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秘書長、臺灣自由緬甸網絡發言人)
「思想罪不會帶來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最為人熟知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中,這句話彷彿預告了緬甸自一九四八年獨立以來,這國家將發生的諸多苦難都將來自「思想」。「老大哥」所帶來的無數良心犯,在整個緬甸社會當中至今仍是許多人的禁忌話題,卻也是許多緬甸人民永遠的印記──威權的烙印。
《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出版於二○○五年,書中密集引用《一九八四》作為「參考圖像」映射出當今的緬甸...
作者序
序言
「喬治.歐威爾,」我緩慢地說:「喬─治─歐─威─爾。」但眼前這名緬甸老人還是不斷搖頭。
這是下緬甸(Lower Burma)一處令人昏昏欲睡的港口城鎮,我們來到老人家中,坐在宛如烤箱的客廳裡。屋內空氣悶熱難耐。我聽到蚊子圍繞著我的腦袋,焦躁地發出嗡嗡的聲音,而我的耐性似乎也即將用盡。老人是緬甸的知名學者,我知道他很熟悉歐威爾。但他已經上了年紀;白內障使他的眼睛泛著牡蠣藍的光澤。當他重新穿好身上的紗籠(sarong)時,兩隻手還不斷顫抖著。我懷疑他是否已經失憶,而在失敗好幾次之後,我決定做最後一次嘗試。
「喬治.歐威爾,」我又重複一次,「《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的作者。」老人突然眼睛一亮。他看著我,一副意會過來的神情,然後開心地拍著自己的額頭說:「原來妳說的是先知啊!」
歐威爾於一九五○年去世,就在前一年,他的打字機遭到沒收。歐威爾住在科茨沃德斯(Cotswolds)的小木屋裡,這裡充滿綠意且舒適宜人。在養病期間,歐威爾經常整個人窩進電毯,但最後還是不敵肺結核的侵襲而離開人世。他的病床旁堆滿了各種書籍,其中有許多是討論史達林以及德國在二次大戰期間殘暴罪行的作品,有一本十九世紀英國勞工研究,幾本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說,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早期的一些作品。床底下還藏了一瓶蘭姆酒。
在療養院負責治療歐威爾的醫師們囑咐他最好不要再繼續寫作。他們說,不管是哪一種寫作,都會把他累垮。他需要專心靜養。歐威爾的兩個肺因疾病而阻塞,而且開始咳血。他的病情已到了關鍵時期,醫師對於病人是否能夠痊癒不表樂觀。即使他能痊癒,大概也無法繼續寫作,或者至少不能像過去那樣沒命地投入。然而歐威爾還是繼續搖起筆桿。他潦草地書寫信件、撰寫隨筆、評論書籍,同時還改正即將出版的小說《一九八四》的校樣。他熱切的心靈甚至正醞釀著下一部作品:中篇小說〈一則吸菸室的故事〉(‘A Smoking Room Story’),這本書打算重新造訪緬甸,這個歐威爾年輕時離開就未再回去的地方。
一九二○年代,歐威爾在緬甸擔任帝國警察。五年執勤期間,他總是穿著卡其馬褲與閃亮的黑色馬靴。帝國警察配備槍枝,是道德優越的象徵。他們巡行鄉里,即使位於大英帝國偏遠的一隅,他們也力求秩序井然。然而,有一天歐威爾突然無預警地返回英格蘭遞交辭呈。同樣突然的是,他開始了寫作生涯。歐威爾署名時不用自己的本名「艾瑞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而另取了筆名「喬治.歐威爾」。他換上流浪漢的破爛衣裳,在潮濕的倫敦深夜遊蕩街頭,收集貧苦大眾的故事。歐威爾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是根據他在遠東的經驗寫下的,但他真正成為二十世紀最受尊敬與最具洞察力的作家則是因為《動物農莊》(Animal Farm)與《一九八四》這兩部作品。
這是一段不可思議的命運安排,這三部小說居然體現了緬甸晚近的歷史。第一個連結是《緬甸歲月》,它記錄了緬甸在英國殖民時期的故事。一九四八年,緬甸從英國獨立,不久軍事獨裁者就阻絕國家與外界的連繫,發起所謂「緬甸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且讓緬甸淪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相同的故事出現在歐威爾的《動物農莊》裡,一群豬推翻了人類農民,自行經營農場,最後卻招致毀滅,這則寓言暗喻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最後,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描述的可怕而無靈魂的反烏托邦(dystopia),宛如一幅精確得令人心寒的今日緬甸圖像,一個被世界最殘忍與最頑強的獨裁者統治的國家。
緬甸有則笑話,說歐威爾不只為緬甸寫了一部小說,而是三部:這三部曲就是《緬甸歲月》、《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
一九九五年,我首次造訪緬甸,當我走在曼德勒(Mandalay)的繁忙街頭時,一名緬甸男子一邊快速旋轉他的黑色雨傘,一邊看似有所意圖地大步朝我走來。他露出開朗的笑容說道:「告訴外面的世界,我們需要民主,人民已經受夠了。」然後隨即轉身踏著輕快的步伐離開。就是這個:這稀罕而短暫的一瞥,已足以使我瞭然於心,緬甸並不像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樣。
我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在宛如明信片般完美的景致裡四處遊歷,無論是人聲鼎沸的市場、閃閃發亮的佛塔還是風華褪盡的英式山間車站,這一切都讓我無法相信自己旅行於一個世界人權紀錄最糟糕的國家。我認為,這是緬甸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全國約五千萬人口遭受的各種壓迫,居然可以完全隱藏起來不被外人發現。無孔不入的軍事諜報人員與密告網絡,確保沒有人能從事或洩露任何可能威脅政權的事。緬甸媒體──書籍、雜誌、電影與音樂──受到嚴格的檢查控制,政府的政令宣導不僅透過報紙與電視,也經由學校與大學傳布到全國各個角落。這些掌控現實的方法,背後由一股不可見卻又無所不在的力量牢牢支撐著,使全國人民無時無刻籠罩在拷問與監禁的威脅之中。
像我這樣的局外人,不可能看穿軍政府粉飾的太平景象,也無力想像在這種國家生活的恐懼與朝不保夕。而就在我努力瞭解緬甸生活面向的同時,我也逐漸感受到歐威爾作品的魅力。他所有的小說都在探索一個觀念,就是個人深受環境的箝制與束縛,不僅受到家庭的控制,也受到周遭社會乃至於權力無所不在的政府的宰制。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構思出最終極的壓迫形式,甚至創造出能描述這種壓迫的語言:「老大哥」、「一○一號房」、「新語」。
我再度閱讀歐威爾的小說──從我離開中學之後就再也沒碰過他的書──心中對於他與緬甸的關係深感好奇。什麼原因使他願意放棄殖民地的工作,選擇當一名作家?而在離開緬甸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又是什麼原因使臨終前的他將目光轉向緬甸尋求寫作的靈感?我開始想像歐威爾從緬甸看出了什麼,他也許尋出了某種觀念的線索,可以一路貫穿他所有的作品。我閱讀許多歐威爾傳記,但這些傳記作家似乎都低估了緬甸的重要性,沒有人對這個歐威爾曾經生活過五年,而且令他的人生產生重大轉折的地方進行研究。歐威爾當初駐在的城鎮就位於緬甸的地理核心位置,某方面來說,現在的我們仍有可能感受到歐威爾當初生活過的緬甸──將近半世紀的軍事獨裁統治,整個國家的風貌彷彿被凍結起來,過去的風貌許多仍完整的保留下來。然而實際走過歐威爾的緬甸,看到的卻是更陰森而駭人的景象:象徵歐威爾夢魘的《一九八四》,竟在這裡以令人不寒而慄的方式真實上演。
外國作家與新聞記者是不准進入緬甸的。偶爾有人混充觀光客而順利入境,然而一旦身分暴露,他們的筆記本與底片會遭到沒收,而人也隨即被驅逐出境。至於他們訪談過的緬甸人,遭遇的懲罰將嚴厲得多。根據緬甸一九五○年制定的緊急法令(Emergency Provisions Act),凡是提供外國人任何政府認為可能有害國家的資訊,最高可判處七年徒刑。雖然我是新聞記者,但我很少發表有關緬甸的報導,所以我仍有機會以觀光客或極少數外商的身分申請到長期居留簽證。為了把我的經驗寫入書中,我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協:我必須改變我訪談過的緬甸人姓名,有必要的話,連地點也會變更。然而在這種謹慎的過程中,我希望自己能找出一條道路,洞穿這個看似不可穿透的國家。
在我動身前往緬甸之前,我到了倫敦的喬治.歐威爾檔案館(George Orwell Archive),觀看歐威爾最後的手稿。當歐威爾於一九五○年去世時,他才剛開始著手一個寫作計畫。根據他的計畫,〈一則吸菸室的故事〉是一篇長度約三萬到四萬字的中篇小說,內容講述一名充滿活力的英國年輕人在緬甸殖民地潮濕的熱帶叢林居住之後,整個人出現難以回復的變化。翻開用大理石花紋紙張包裹的筆記本,前三頁布滿歐威爾潦草的墨水字跡,大致是故事的大綱與短篇插曲。我輕輕地翻覽整冊筆記本,發現後面的書頁空空如也。我知道,故事的剩餘部分還塵封於緬甸,等待人們喚醒。
序言
「喬治.歐威爾,」我緩慢地說:「喬─治─歐─威─爾。」但眼前這名緬甸老人還是不斷搖頭。
這是下緬甸(Lower Burma)一處令人昏昏欲睡的港口城鎮,我們來到老人家中,坐在宛如烤箱的客廳裡。屋內空氣悶熱難耐。我聽到蚊子圍繞著我的腦袋,焦躁地發出嗡嗡的聲音,而我的耐性似乎也即將用盡。老人是緬甸的知名學者,我知道他很熟悉歐威爾。但他已經上了年紀;白內障使他的眼睛泛著牡蠣藍的光澤。當他重新穿好身上的紗籠(sarong)時,兩隻手還不斷顫抖著。我懷疑他是否已經失憶,而在失敗好幾次之後,我決定做最後一次嘗試。
「喬...
目錄
目次
推薦序╱楊宗澧
地圖
序言
第一章 曼德勒
第二章 三角洲
第三章 仰光
第四章 毛淡棉
第五章 卡薩
後記
新後記
目次
推薦序╱楊宗澧
地圖
序言
第一章 曼德勒
第二章 三角洲
第三章 仰光
第四章 毛淡棉
第五章 卡薩
後記
新後記


 2015/06/11
2015/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