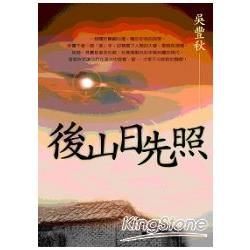名人推薦:
他們在此相遇、希望與愛
──關於《後山日先照》 郝譽翔
花蓮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特別得好像不是在台灣這塊島嶼之上。
對於從小生長在台北的我而言,花蓮的乾淨、開闊、寧靜與優雅,充滿了異國的情調。蔚藍浩瀚的太平洋,使人不禁想起了西雅圖,停泊港口的船隻,將要航行向未知的遠方。但若是一走進花蓮市鎮,深入大街小巷,卻又會發現處處是古樸的木造日式住宅,日本料理店,日本人的好禮、愛美與潔癖,根深柢固地在花蓮人身上留存了下來。
但花蓮的特別,還不止於此。
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閩南人,在花蓮各自佔據相當的人口比率,沒有哪一個族群享有獨大的權力。而除了原住民之外,大多數的人口都屬於新移民,移居來此,不過才兩三代而已,時間雖然短促,卻也使得花蓮人特別具有包容力以及開闊性。因此,花蓮不僅是台灣的縮影,它更兼容並蓄了台灣殖民史的多重樣貌,多種族群的交流互動,就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的俯抱之間,在這塊被稱為「後山」的狹長土地上。
《後山日先照》所記述的,就是如此獨特的花蓮,甚至可以說,是如此獨特的台灣。從後山,反照出來的卻是台灣族群的集體命運、情感與記憶。作者吳豐秋以樸素而誠懇的筆法,刻畫出生長在故鄉土地上的小人物們,雨綢、雅貞、雅慧、耕土、耕竹、北印、再添,許許多多的臉孔,彷彿就是出自於左鄰右舍,他們一一被文字召喚,打開家門,走出來,沿著寧靜的街道,走到山邊、溪邊、海邊,然後彼此相遇,認識,寄託希望,以及相愛。
小說中的主角,多半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老百姓,他們不同省籍,不同姓氏血緣,不同出身背景,但卻同樣誕生在一個多苦多難的時代裡,流離飄亡,因緣際會之下,來到了後山,在這裡落戶,札根,共同默默抵禦著戒嚴時期的政治壓迫,相互扶持。在他們的心目中,族群沒有藩籬,省籍和語言更不是障礙,他們唯一控訴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嗜食權力的統治階層,是無情的白色恐怖。因此在吳豐秋筆下的二二八,是一場獨裁者的專斷暴行,絕非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相殘。而令人動容的是,面對現實的肅殺逼迫,在不同族群卻同是「受害者」的小人物之間,那股自然流露的互助與互愛。
吳豐秋在海外從事民主運動多年,曾經因為政治因素,二十年之久無法回到台灣,濃厚的鄉愁與使命感,促使他寫下了這本書,也因此,這本小說沒有當前流行的前衛技巧,也沒有華麗雕琢的文藻,但他的寫作意圖卻是至為誠懇的,出自於土地與記憶的殷殷召喚,而這本小說的成就也是至為廣闊的,涵括了台灣複雜的族群遷徙、認同與歷史記憶。公共電視選擇將它改拍成電視劇,不僅讓更多的台灣人看見了花蓮,同時也讓大家從花蓮中看見了自己,看見了這塊島嶼的共同身世與命運。
花蓮文學向來自鑄一格,楊牧和王禎和的作品,均吸納花蓮多種族群文化的嘉年華美學,最能代表這一島嶼邊緣──背山面海的特殊位置,而《後山日先照》則是以紀實的筆法,架構出一部後山住民的命運史詩。所以「台灣」豈如某些政客所言,僅止於單一的定義而已?台灣錯綜複雜的身世,糾葛纏繞的歷史,原本深埋在土地之中,如今已透過文學家之筆,一一還原浮現而出,正等待我們去閱讀,去發現,去理解,並因此更加珍愛這座島嶼上的人們,所曾經攜手共同走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