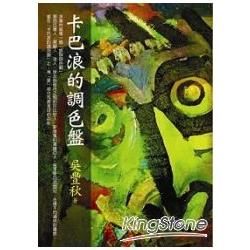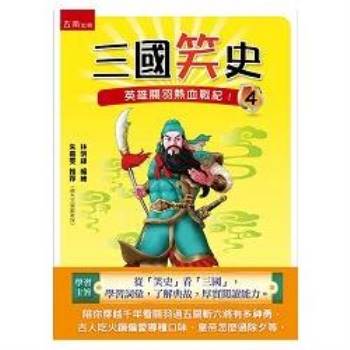媒體推薦:
推薦序/
族群的調色盤 顏崑陽
《卡巴浪的調色盤》是吳豐秋在台灣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後山日先照》,第二部是《漏網族》。這二部小說分別於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由躍昇文化公司出版。《後山日先照》更於二○○二年,被改編成連續劇,由李岳峰導演,在公視播出,造成轟動。旅居海外的吳豐秋也因此被許多台灣的讀者、觀眾所熟知。
《卡巴浪的調色盤》是一部充滿浪漫、理想色彩的歷史小說。
歷史小說雖有其想像、虛構的情節,卻也必須取材自某些歷史事蹟。這部小說所取材的歷史事蹟是十七世紀荷蘭、明鄭之際,台南赤崁附近水車村西拉雅人與荷蘭人、漢人交往、衝突、融合,最終卻被迫遷移的過程。
西拉雅是最早與荷蘭人、漢人接觸的平埔族原住民。台灣四百年史就從他們與荷蘭人、漢人的生存競爭開始。因此,他們夾在荷蘭人、漢人強勢墾殖之間,受害也最深;不但被迫從台南、高雄、屏東一帶,往南投埔里,甚至翻越中央山脈,向台東、花蓮遷移。到了現在,更由於文化、語言消失,政府竟然不承認他們的原住民身分。
吳豐秋之所以選擇西拉雅人的生存經驗做為歷史素材,可能和他出身花蓮有些關係吧!狹義的西拉雅人指的是居住在台南地區蕭壟、麻豆、目加溜灣、新港的四大社群;廣義的西拉雅人則另外包括了高雄大武壟、屏東馬卡道二個社群。他們遷移到後山,其中來自大武壟及馬卡道社群的西拉雅人,就定居在花蓮縣富里鄉的東里村一帶,建立大庄部落。吳豐秋在小說的「結語」就敘述到:「如今仍有數千西拉雅人後裔,生活在南自大庄(今花蓮東里),北迄馬太鞍(今花蓮光復)的狹長地區。」不錯,如今還居住在富里一帶的西拉雅人,大約有四千人。
從西拉雅人好幾次的遷移史來看,最大規模的遷移並非發生在十七世紀荷蘭與明鄭爭戰之際,而是在十九世紀的清代道光年間。這時候,西拉雅人也才翻越中央山脈,遠徙花東。從小說的「結語」來看,吳豐秋很清楚西拉雅的遷移史;然而,他會選擇十七世紀荷蘭與明鄭爭戰之際,描寫水車村西拉雅人的生存經驗與遷徙過程,應該有他想要表現的主題;他所關懷的焦點,並非西拉雅人的整個遷移史,而是以西拉雅人做為「族群調色盤」,所形成以「愛」為動力的族群融合。那麼,荷蘭與明鄭爭戰時期,正是多種族群交會,為了墾殖而產生彼此的衝突;這樣的情境最適合表現族群融合了。
超脫政治權力的對立、跨越族群血緣、文化的籓籬,而經由人性生具之「愛」,彼此交融為生命共同體。這似乎是吳豐秋始終秉持的浪漫、理想情懷,也是從《後山日先照》貫穿到《卡巴浪調色盤》的主旋律。我為《後山日先照》寫序,就已提出「愛─不分族群的歸鄉」這個詮釋觀點。另外,我還寫了一篇評論─〈跨越族群的圍籬〉,做為解讀《後山日先照》的視窗。這個觀點、這個視窗,如今移來詮釋《卡巴浪的調色盤》,竟然也還適用。在〈跨越族群的圍籬〉中,我這麼說:這樣大流落的時代,不分族群的亂離,他們如何可能「歸鄉」呢?怎樣的一個「鄉」,才能讓他們真正地安頓下來?這個「鄉」,就是不分族群的「愛」。
唯有依藉真實的族群之愛,才能根本地去救贖這時代的亂離。
十幾年過去了,吳豐秋的情懷一點兒都沒變,依然相信人性的善良、依然相信只有「愛」才是人類永恆的「鄉」。當那些強勢者的心眼中,唯有權力欲望,或者當族群之間橫亙著意識形態的籓籬時,弱勢者就只能吞忍著流落、飄泊的悲情;但是,在流落、飄泊的歷程中,他們終將以超越政權、族群的「愛」,獲得心靈的平安快樂。
在《卡巴浪的調色盤》中,水車村善良的西拉雅人之所以必須遷移,離開他們的家園,顯受到那些嗜食權力、剝奪財貨的荷蘭人與漢人所逼迫。不管是來自西方的殖民主──荷蘭人,或來自大陸的殖民主──漢人,尤其是明鄭王朝的官員們。對「原住民」的西拉雅人而言,他們都是挾帶武力的入侵者。早在卡巴浪的祖父達倫莫耶時代,西拉雅人就眼睜睜看著,大員(台南安平)外海突然停靠了十三艘荷蘭船艦,幾百名荷蘭士兵、水手和測量員把大礮、農耕工具和測量儀器搬上赤坎海邊,然後搭起帳篷住了下來。這些紅毛番完全不把赤坎十五個村落的西拉雅人放在眼裡。強徵勞役及糧食,就不斷在荷蘭人的槍口下發生。至於漢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不但一大群一大群長驅直入到內地,佔領最肥美的土地,大肆墾殖;甚且,明鄭王朝的官員更強橫地直接向水車村的西拉雅人徵收糧食。面對這樣的處境,卡巴浪就只能帶領他的族人,吞忍著流落、飄泊的悲情,遷移到一個沒有強取豪奪而允許他們過著寧靜生活地方。
在權力欲望無限擴張與意識形態堅固阻隔之下,人類便罹患了「愛的匱乏症」,相互攻伐,彼此壓迫。對照這種惡境,水車村的西拉雅人,以青年頭人卡巴浪和妹妹阿妮咪雅為主,就表現了那種超越政權、族群籓籬的「愛」。水車村就像一個「族群調色盤」,將西拉雅人、荷蘭人、漢人、埃及與蘇丹之間的奴比安人、菲律賓的畢薩亞人,甚至黑白混血兒,各種不同膚色的種族,都在「卡巴浪的調色盤」上,用「愛」融合成最美好的色彩。
卡巴浪是個天才的畫家,他能用「心」在調色盤糅合出各種最美好的色彩,而畫出人物的神韻。同時,他也是水車村西拉雅人的頭目,與妹妹阿妮咪雅兩人都非常仁慈、寬和,用同情心去包容、關懷、照顧各個不同族群的人;相對的,他們也接受了西方及漢人的文化,而實際使用在日常生活,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甚且,卡巴浪與奴比安族黑白混血的公主依蒂娜、阿妮咪雅與荷蘭醫生貝爾,他們跨越族群的愛情、婚姻,不正是「族群調色盤」所糅合出最美好的色彩嗎?
因此,在這部小說中,「調色盤」與「混血兒」是很主要的符碼,隱喻著吳豐秋所始終抱持的浪漫、理想情懷:超脫政治權力的對立、跨越族群血緣、文化的籓籬,而經由人性生具之「愛」,彼此交融為生命共同體,營造一個永恆的「鄉」。
吳豐秋之所以始終堅持這樣的情懷,應該和他個人的際遇與時代處境有著緊密的關聯。他在花蓮度過少年歲月,到台北讀完大學之後不久,便開始長期飄泊海外的生涯。戒嚴時期,他參與台灣民主運動,因而將近二十年間,被禁止返台。當他個人正被濃烈的「飄泊感」與「鄉愁」煎熬著;遙遠的鄉關,台灣社會也因為政客的操弄,而陷入權力鬥爭與族群對立的亂局中。
「浪漫」是出於爭脫現實世界種種理性或權威之枷鎖的感性衝動;「理想」則是不完美的現實世界所折射出來的完美圖像。從吳豐秋的個人際遇與時代處境,我們便不難了解,為什麼他會始終抱持著「愛─不分族群的歸鄉」,那樣浪漫、理想的情懷。很多人相信,文學有一種功能,那就是在悲苦的現實世界中,用語言意象為人們構造一個幸福、快樂的理想境地。因此,文學能給人帶來希望。吳豐秋的小說,實踐的就是這樣的文學觀吧!
因此,我可以說,吳豐秋是因為關懷人間之愛而寫小說,不是因為追求小說藝術而寫小說。他只是很素樸、很真誠地用「說故事」的形式,表達他始終堅持的那份情懷。在《後山日先照》裡,看不到繁複、奧妙的語言形式技巧;十多年後,這部《卡巴浪的調色盤》亦復如此。然而,吳豐秋的小說之所以感動我,不是由於專業性的語言技巧,而是那份流動在字裡行間的真誠情懷。
然而,我在讀完這部充滿浪漫、理想色彩的歷史小說之後,還是無法規避台灣當前現實社會惡質化的政治權力鬥爭,以及在國家認同的統獨論述中,被操弄的族群意識形態。理想與現實總是隔著天塹一般的距離;我在想像,卡巴浪帶領著西拉雅人以及融合在調色盤上的另類族人,從水車村遷移出去,最終真能找到一個沒有爭奪、沒有剝削的樂土嗎?
此刻,一種生命存在的蒼涼感,無可遏抑地從我內心底層湧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