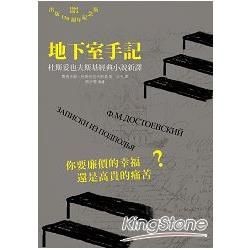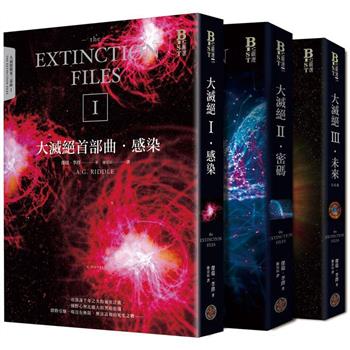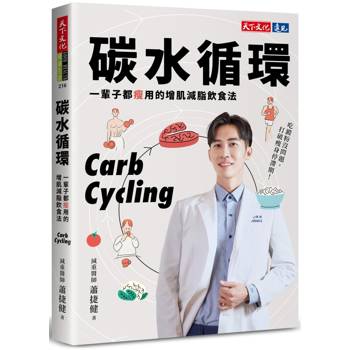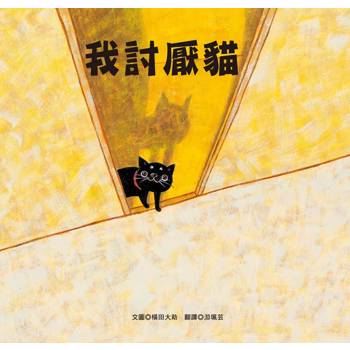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地下室手記》作品出版150週年紀念版(1864-2014)
◎全本俄文直譯,80餘則翻譯注釋,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熊宗慧專文導讀
◎俄國心理小說大師的入門首選,《罪與罰》到《卡拉馬助夫兄弟》長篇巨著的序曲
◎世界文學小說必讀經典
為什麼你們堅信只有幸福才對人有益呢?……或許,痛苦對人來說也一樣有益?
《地下室手記》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創作上的轉捩點,他從前期沉浸在小人物的人道悲憫、心理關懷中穿透而昇華,成了預見人類悲劇的哲學思想家,他「彷彿」藉由這部中篇小說告訴我們當時最缺乏而卻是世上最可貴的東西──個人的性格,並提出了一長串的疑問圍繞在這個中心主題上。
沒有人像我,我也不像任何人──「我是一個,他們是全部。」……我一直渴望他們的侮辱──這是淨化,這是最尖刻、最疼痛的意識!
小說談到「個人」對抗群體,講到群體盲從自然規律到個人自我意識覺醒的信念重生的過程,透過「地下室人」這個杜斯妥也夫斯基創造出的文學形象表現出來,他象徵一個退縮到自己內心角落的文明邊緣人。他「有意識」地將自己埋進心裡的地下室,而與群體的關係,一是在思想上辯證,二是在社會上吵架。小說即依此分為對比鮮明的兩篇,作者頗自豪地稱這類似音樂上的變奏形式,且兩者互補相得益彰。
首篇中,地下室人是一個看似精神分裂的中年退休公務員,用獨白方式談自己縮到角落的原由,憤世嫉俗又時而矛盾地貶低他人或自己,他自問自答暢談道理,從自己有病不看醫生談起,開始哲學性地扯到人的意識、利益、意志、理性、自然規律、欲望、自由、侮辱及痛苦的必要,它們種種既包容又矛盾的關係在他叨叨絮絮的詞語中,彷彿咒語似的從他口中不斷吐出,著實讓人既驚奇又直冒冷汗,如此高懸的心情轉至第二篇,卻是落到現實生活中「侮辱與被侮辱」的爛泥裡,他回憶起從前年少的學校生活至成年工作時的羞恥記憶,簡直是一路不斷被人侮辱的成長史,轉述了三個生動有趣的事件:讓路生悶氣、與同學聚餐吵架、上妓院找碴。
整個小說也帶出俄國當時的首都聖彼得堡的城市氣氛,雨雪溼漉、天色昏暗、孤獨陰鬱,地下室人像隻老鼠似的在這裡鑽進鑽出。作者試圖將整個時代,特別是負面的特徵放進這個人物形象中,對比綜合出別具一格的時代人物。
如果我們反覆咀嚼這些時而令人發笑時而使人瞠目的妄語,那麼,對於翻動人類靈魂、翻新社會生活的力量來源,或許將會有一番新的領悟。比如這個地下室人最後提出的問題:
哪一個比較好呢?是廉價的幸福,還是高貴的痛苦?
【評價】
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唯一讓我有所得的心理學家,他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好運之一。──尼采
格里帕策、杜斯妥也夫斯基、克萊斯特、福樓拜,,我認為這四位是我真正的血親。──卡夫卡
《地下室手記》是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他所有作品的中心要旨,是他思想的線索。──紀德
歐洲的年輕世代,特別是德國的年輕人,是把杜斯妥也夫斯基視為他們的典範,而不是歌德或尼采。──赫塞
他(杜斯妥也夫斯基)把所有的東西都混在一起了,又是宗教,又是政治……不過呢,他當然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所追求的有其深刻之處。──托爾斯泰
對我來說,《地下室手記》中有整個尼采。人們還不善於閱讀這本書,它的內容給了整個歐洲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論據。──高爾基
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殘酷的天才。──米哈伊洛夫斯基
杜斯妥也夫斯基不僅是偉大的藝術家,也是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心靈預言家,還是天才的辯證論者和最偉大的俄羅斯形而上學者。……他屬於基督教世界,其中已徹底顯露出存在的悲劇歷程……德國人在存在的表層,看到上帝和魔鬼、光明和黑暗的衝突,而當走進精神生活的深處,則只看到上帝,想到光明,這時對立便消失。俄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所揭示的是,上帝和魔鬼的對立、光明和黑暗的衝突,是位於存在的最深處。……上帝和魔鬼是在人的心靈最深處搏鬥……杜斯妥也夫斯基不像其他人(德國人),他發現悲劇的矛盾性,並不在於心理層面上,而在於存在的深淵中。──別爾嘉耶夫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地下室手記: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世界古典 |
$ 246 |
俄國文學 |
$ 246 |
俄國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地下室手記: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杜斯妥也夫斯基(F. Dostoyevsky, 1821-1881)
俄國小說家,探索人類靈魂奧祕的作家。著作影響世界文壇,並啟發尼采、愛因斯坦,以及二十世紀存在主義哲學思潮、龐克搖滾樂等多方領域。
出生於莫斯科,家中排行老二,父親為軍醫。十六歲時,母親因肺結核過世,與長兄被父親安排到彼得堡念寄宿學校,後來考進軍事工程學校,就學五年期間被他在作品中稱為「該死的這些苦役般的時光」。十八歲時,父親過世,傳說是因為對自己的農奴太過嚴苛而被殺害,這件事影響到了未來作家的心理發展。
一八四六年發表處女作《窮人》博得好評,在文壇展露鋒芒,被譽為「新的果戈里出現了」,從此展開他創作生涯的第一階段。隔年起,積極參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社團,著迷於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一八四九年因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被捕,判死刑槍決,主要罪名是公開宣讀禁書──別林斯基的《致果戈里的信》,臨刑前被沙皇赦免死罪,改判苦役流放西伯利亞。一八五九年,服完四年的苦役與五年多的兵役(這期間結了第一次婚),年底獲得重返首都彼得堡的權利,準備從文壇再起。從一八六○年起,開始了創作生涯的第二階段,與長兄合辦了兩本文學雜誌,出版《死屋手記》、《被侮辱者與被凌辱者》,以及創作風格轉捩點的《地下室手記》,為此後的重要長篇小說從《罪與罰》到《卡拉馬助夫兄弟》,鋪出一條充滿各式各樣的信仰懷疑的大熔爐之路,而同時他也透過這條創作之路,試圖在其中求得能夠拯救世界的「美」。
譯者簡介
丘光
國立政治大學東語系俄文組畢業,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文學碩士。譯作有:《帶小狗的女士: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當代英雄: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等。
杜斯妥也夫斯基(F. Dostoyevsky, 1821-1881)
俄國小說家,探索人類靈魂奧祕的作家。著作影響世界文壇,並啟發尼采、愛因斯坦,以及二十世紀存在主義哲學思潮、龐克搖滾樂等多方領域。
出生於莫斯科,家中排行老二,父親為軍醫。十六歲時,母親因肺結核過世,與長兄被父親安排到彼得堡念寄宿學校,後來考進軍事工程學校,就學五年期間被他在作品中稱為「該死的這些苦役般的時光」。十八歲時,父親過世,傳說是因為對自己的農奴太過嚴苛而被殺害,這件事影響到了未來作家的心理發展。
一八四六年發表處女作《窮人》博得好評,在文壇展露鋒芒,被譽為「新的果戈里出現了」,從此展開他創作生涯的第一階段。隔年起,積極參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社團,著迷於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一八四九年因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被捕,判死刑槍決,主要罪名是公開宣讀禁書──別林斯基的《致果戈里的信》,臨刑前被沙皇赦免死罪,改判苦役流放西伯利亞。一八五九年,服完四年的苦役與五年多的兵役(這期間結了第一次婚),年底獲得重返首都彼得堡的權利,準備從文壇再起。從一八六○年起,開始了創作生涯的第二階段,與長兄合辦了兩本文學雜誌,出版《死屋手記》、《被侮辱者與被凌辱者》,以及創作風格轉捩點的《地下室手記》,為此後的重要長篇小說從《罪與罰》到《卡拉馬助夫兄弟》,鋪出一條充滿各式各樣的信仰懷疑的大熔爐之路,而同時他也透過這條創作之路,試圖在其中求得能夠拯救世界的「美」。
譯者簡介
丘光
國立政治大學東語系俄文組畢業,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文學碩士。譯作有:《帶小狗的女士: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當代英雄:萊蒙托夫經典小說新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