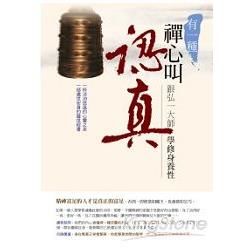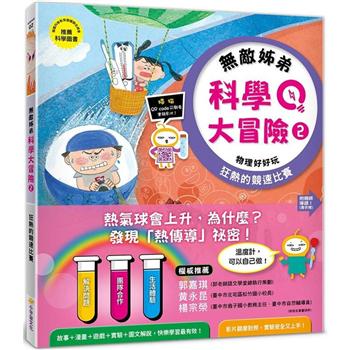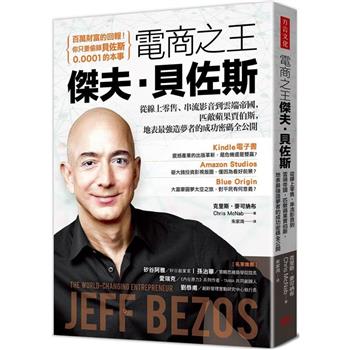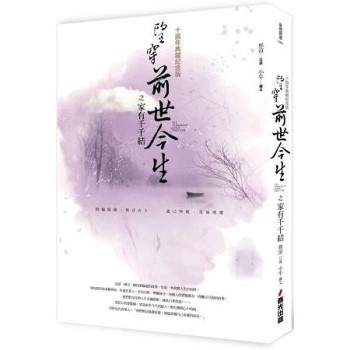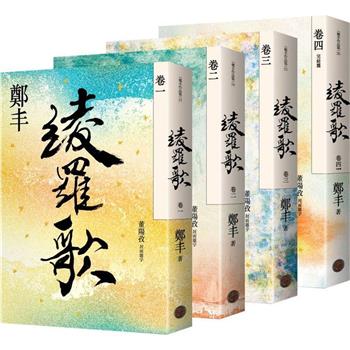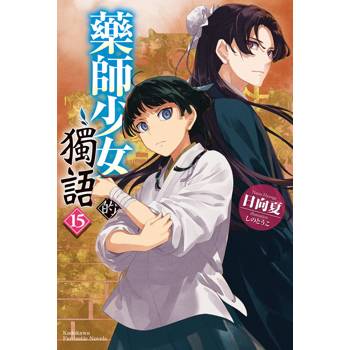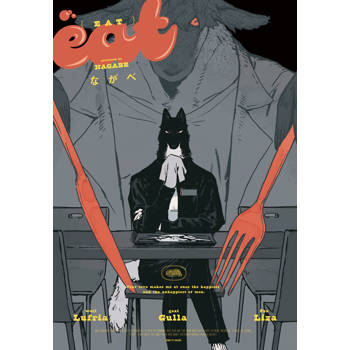序文
和大師去修行:活得好一點,更好一點
台灣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有一天啊,寶寶》一書中說:「讀書自由、私密、自說自話、自苦自樂……人生最令我們留戀的,都是一些我們也說不清楚的事吧。但是書啊,是我們塞給自己的希望,就算只是些妄想,割捨也不免惆悵。」書是我們送給自己的希望,好通透的說法啊!
書是希望,因為它有思想。古往今來,歷史上的每一位大師都是思想的合集,每一位大師都是一本厚重的書,一如我們要介紹的這兩位:李叔同和南懷瑾。為何將兩人放在一起呢?記得佛家有句話說:「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能擺脫塵世的困擾,就等於到達真實境界;否則,即使身穿袈裟、住在僧院,卻和俗人沒有區別。兩位大師雖然一個在塵世之外,一個在塵世之內,卻都經歷過塵世的歷練,最終擺脫了塵世的糾結,達到了身心自由的境界。
所謂看破紅塵,對有些人來說只不過是不入紅塵而已。我們大多數人對紅塵都是很留戀的,即使會有很多傷痛、痠楚、不盡如人意,然而,我們熱愛著俗世的生活。不娶妻生子的人是沒有資格講解人生的!幸好,李叔同和南懷瑾兩位大師即使經歷不同、人生看法不同,但他們都對世人充滿了愛。
愛是最大的智慧。因為有愛,我們可以從他們豐富淵博的人生閱歷,和清新平實的話語中,捕捉到智慧之光,探求人生真諦。李叔同和南懷瑾都是佛學大師,但他們是不同的。因為禪學將他們聯繫到了一起,因為不同的人生選擇,他們被區別開來。
李叔同是關注世事,卻又遠離世事的人,他在繁華之外看繁華。所以,他多關注於人自我的精神世界。精神富足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足;否則,即使富如國王,也會貧如乞丐。讀他,我們的內心會獲得一種空靈的美感,那是一種久遠的自然力量。在人世廝混許久的我們,或許已經很久不曾感覺到那種純粹的、不含任何雜質的靈魂的色彩。他使我們低下頭,開始審視自身,重新關注已被遺忘很久的自我的真實性。
南懷瑾是身在繁華而又笑看繁華的人,他是繁華世間的智者,得享繁華卻又不被繁華所累。如果說李叔同是隱居的禪師,那南懷瑾便是入世的佈道者。他更關注自身與外界的關係,在他看來,幸福的人生不是生存在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中,而是融入外界,在集體中體會融洽。於是,他講述人生種種人情世故,講處世哲學、生存策略,這一切,都是為了使我們更好地生活在人與人的世界裡。
在李叔同的精神家園中,我們不會嬉笑怒罵,更不會茫然徘徊。我們只會靜靜地思索,思索愛、思索人生,也思索自我。靈魂在這裡起飛,它隔絕了外界窺探的眼睛,使我們得享無人的自由和靜謐。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精神的家園是美好的,自由的精神世界對一個人而言,往往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只不過有很多人意識不到罷了。大多數人都在茫然中失去、錯過,就彷彿凍僵的人,對自己受損的機體毫無感覺,只留有些微的刺痛或麻癢。人們在外部世界的誘惑下,從精神家園出走,只留下靈魂深處寂寞的春草,獨自寂寞生長。遠遊啊,忘記歸期!一入社會,社會便成了永久停留的第二故鄉。
這第二故鄉留下了我們奮鬥的熱情、人生的朝花夕拾。我們在此安家立業,看遍了形形色色、光怪陸離,也嘗盡了冷暖交替、高低起伏。想活得好一點、更好一點,無論我們生來或者後來積極還是消極,這都是人類永恆的願望。想活得好一點,就要懂得多一點,於是我們按照南懷瑾的指引,重新了解身處的社會,努力練就高手的眼光和手段,或許會多幾分機智,減少幾許脆弱和柔軟,逐漸堅強。
如果,一個人想學習征服社會的手段,那麼,守護精神的家園才是最好的出發點。為了活得好一些、更好一些,為了在塵世獲得幸福,我們仔細聆聽兩位大師的叮囑……
如果用一句話來給此書做個總結,那便是:這是一杯淡泊悠遠的心靈之茶,也是一本處世安身的塵世經書。
如果你喜歡,請傾聽它靈魂的絮語,如果不喜歡,擱置一旁,任它在歲月裡深深埋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