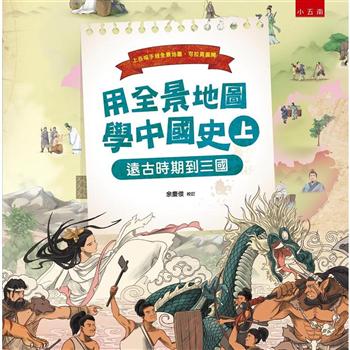巴黎公寓物語
「就算脫衣服的方式有魅力的女孩子很多,但穿衣服的方式有魅力的女孩子卻不是那麼多。」我喃喃地對自己複述著村上講過的真理,女孩坐在床角略顯吃力地正在把雙腿塞入煙管褲中。
她終於站起了身,穿上米色小羊皮外套,轉身走過來在我額頭上吻了一下,然後走出房間。不規則的金屬撞擊聲傳來,是在門口那只大碗裡撈鑰匙的每天例行公事,然後是開門和關門聲,高跟鞋逐漸遠去的下樓聲。
我伸了伸懶腰,從床上爬起,信步來到窗前低頭眺望,女孩正一手壓著敞開的公寓大門,對微微顫顫地進門的老太太說了聲日安,那是住我們樓下的奧勒麗女士,先生走很多年了,兩個兒子都在倫敦工作。她自己一個人住,每週一固定會有清潔婦來幫忙打掃房子,週二會有附近的超市送食材雜貨過來,周日是女士唯一出門的日子,上教堂,風雨無阻,最少在我們搬到這裡兩年來是如此。
對面的公寓窗戶半開著,在縫隙中我看到一雙發亮的黃色眼睛,那是尚─米
榭爾。
名字很老派的尚─米榭爾是一隻貓,我會知道他的名字是因為在那一家子搬過來的第一天,他老兄就沿著公寓外牆的排水管跑掉了,那家子人一整晚不時探出身子對著排水管的盡頭叫著:﹁尚─米榭爾,尚─米榭爾﹂,吹幾聲口哨之類的。
尚─米榭爾三天後自己沿著水管爬了回來,帶著楚浮<<四百擊>>最後一幕安東瓦在沙灘上回首定格的表情,縱身跳入敞開了整整三天的窗子。
那家子的女主人當晚想必迫不及待地把地板仔細吸塵了一遍。
後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尚─米榭爾在窗外曬太陽時,腳上都綁著一條紅繩,延伸到屋內的部分大概是被固定在什麼傢俱上,那陣子他如果和我雙眼對上了,都會露出柯林頓總統在聽證會時露出的那種表情。後來不再綁繩子了,他重新獲得沿著水管散步的權利,但也許是簽了新的豢養契約,從此他將自己的探險範圍下了限制,最遠不超過窗台種了很多植物的隔壁公寓。
窗台種了很多植物的公寓是一對老夫婦的,終年甚少關窗,翠綠的木本和草本盆栽取代了窗簾,將室內擺設遮掩得若現若隱。尚─米榭爾偶爾會縱身越窗而入,但大多在十分鐘後就會再越窗而出,那十分鐘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從沒搞清楚過。
天氣好的時候,灰藍色的公寓屋頂反射著陽光,視角度而定甚至會刺眼。爬在牆壁上的植物,每年週而復始地遵照著季節守則,從枯枝吐芽,到冒出進而長滿翠綠濃密的圓潤大葉,到在秋風吹拂下轉黃而紅,最後傾落一地焦黑。公寓向陽和背陽面的爬牆植物命運甚為不同,我聽說兩派在多年前曾為此鬧過分家,但最終還是糾纏不清,年復一年地上演著貧富差距的戲碼。
雨很常下。
下起雨來整棟建築濕濕潤潤,上百年的堅固牆壁吸了整整兩公分的水氣,笨重起來。屋頂大小高低不一的煙囪群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廢棄不用,但雨滴落在其上還是會敲打出不同音高組成的旋律。
那旋律比西邊鄰居家每天早上傳出的鋼琴聲悅耳多了。這家人搬入一年多來,小女兒演奏的永遠是那三四個旋律,從未曾顯示出進步的跡象,如果不是我們窗台上不斷長高的迷迭香提醒著,每天聽著同樣的錯音和重彈,我很可能會出現比爾‧ 莫瑞的錯覺。
這座喜歡立法規範的城市應該要再多一條法律,禁止嚴重缺乏才能的市民購買鋼琴,或出生在這世界上。
東邊鄰居是個友善的索邦大學學生,總是帶著微笑和我們打招呼。他的公寓大門和我們的正對,可能是這棟建築中最常開開關關的。曾經有一陣子我抱著研究的精神,每次聽到那頭的開門聲就立刻跑到自家門後,將眼睛湊到那小小的魚眼窺視孔,觀看他和來客親吻著打招呼。在那高度扭曲的畫面中出現過的、與他互啄臉頰的女性訪客,高矮胖瘦和打扮品味不一,唯一一致的是聲音總是高亢興奮。
偶爾大學生會辦派對,大約從晚上七點開始門就會開開關關個不停,嘻哈音樂的低頻節奏和年輕人們的高聲談笑透過牆壁傳過來,有時候會到讓人皺眉的程度。但他們大多遵守法式派對的原則,過了午夜來客就會逐一離去,門再度開開關關個不停,最晚凌晨一點一切就會歸於平靜。
只有一次,一個美麗的夏夜,他們決定徹夜不眠。過了午夜,震耳的音樂仍然迴盪在公寓中,一點、兩點、三點,女孩將努力埋在棉被中的頭抬起來,問我是不是該叫警察?我搖了搖頭,回答說: C'est pas sympa,她只好疲倦地把頭再度埋回棉被中。
女孩是歌劇迷,因此當某些陽光燦爛的午後,從社區遙遠的一角傳來男中音練唱威爾第的聲音時,她總是會和我相視一笑,然後壓低聲音跟著哼著:
普羅旺斯的海洋與大地
誰將它從你心中抹去
誰將它從你心中抹去
有時候陽光依舊燦爛,但是男中音出國表演去了,女孩就會自己在唱盤中放進蘇莎蘭和帕華洛帝領銜、波寧吉指揮的版本,然後邊哼唱著邊將切成圈狀的花枝倒入滋滋作響的平底鍋中,用木鏟來回拌炒一會兒,然後倒入夏多內葡萄釀成的餐桌白酒,一倒就是半瓶,將爐子的火力開到最大,興奮地看著白酒沸騰、飄香、濃縮。
總是在同一個時間點,她會用筷子挑出幾個大小適中、香味四溢的花枝圈,放在一個小盤子上,彎下腰放到我面前的地板上。然後在我不顧弄髒鬍子埋首大啖時,她則把煮得彈牙的麵條倒入平底鍋拌炒,撒上一把迅速切碎的平葉荷蘭芹後裝盤。
有一次她捉弄著也撒了一些荷蘭芹到我盤裡,我氣得兩天不理她。
但在這樣一切如常的陽光燦爛的午後中,通常不會有太多意外,用完餐後她
總是會迅速地將碗盤清洗乾淨,煮上一壺咖啡,然後在窗前坐下來,打開<<在少女的身旁>>,翻到折了角的那一頁,靜靜地往下讀。
我則一如往常趴在她的大腿上,在午後的陽光中打盹。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巴黎公寓物語:諾弗勒 短篇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34 |
小說 |
$ 31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巴黎公寓物語:諾弗勒 短篇集
匯淬了諾弗勒十年來的九個短篇作品,不管是時間感或空間感都有著很大的跨幅。如在新竹科學園區工作時用冷眼旁觀的語氣寫下的「請以分手為前提與我交往」與「絕對清醒」、在陽光傻逼地燦爛的矽谷蘊釀出的「我是這樣地愛上了那個愛上你(妳)的自己」與「如果一個人抓到穿過麥田的人」、在光之都巴黎鋪陳出的「巴黎公寓物語」與「在瑪黑」。
「白開水」與「番茄系義大利麵」雖風格迥異,卻意外生成前後篇的有機連結。 「線性人生與巴黎女孩」以諾弗勒典型的尖銳論理筆鋒開始,卻掂著腳尖旋轉幾圈後,舞出最出人意料的結局。
諾弗勒的短篇遊走於虛實之間,讀者不免好奇:有多少情節是作者真實的體驗,而又有多少是文人自戀的幻想。然而正是這忽遠忽近、亦疏亦親的微妙距離感,以及盡在不言中的想像留白,讓這九篇作品與讀者建立起的對話從紙面活了過來。
「這個理工科的怪咖竟然橘逾淮為枳地將憤世譏誚化作了人生幽默,從筆下漫漫湧出法式詼諧,而終於在寫作上醞釀出混種巴黎人風采。我在新作裡讀到了他的巴黎公寓、他的巴黎「豔遇」——肯定不是寫出的那樣少——他的巴黎同事、他的巴黎咖啡館⋯⋯而忍不住想起了巴黎。」— 陳彧馨
作者簡介:
高雄人,典型舒適區恐懼症患者,在台灣和矽谷工作十餘載後,輾轉落腳於巴黎,現從事創投工作。擅長以系統駕馭跨領域的理論和知識,對美的事物無可救藥地著迷,熱愛文學、音樂、哲學、語言、建築、藝術、歷史、總經、金融和政治,嗜好包含寫作、攝影、散步和啃大部頭的文字書。曾任《音樂時代》雜誌主筆,著有《諾弗勒在北義》。
章節試閱
巴黎公寓物語
「就算脫衣服的方式有魅力的女孩子很多,但穿衣服的方式有魅力的女孩子卻不是那麼多。」我喃喃地對自己複述著村上講過的真理,女孩坐在床角略顯吃力地正在把雙腿塞入煙管褲中。
她終於站起了身,穿上米色小羊皮外套,轉身走過來在我額頭上吻了一下,然後走出房間。不規則的金屬撞擊聲傳來,是在門口那只大碗裡撈鑰匙的每天例行公事,然後是開門和關門聲,高跟鞋逐漸遠去的下樓聲。
我伸了伸懶腰,從床上爬起,信步來到窗前低頭眺望,女孩正一手壓著敞開的公寓大門,對微微顫顫地進門的老太太說了聲日安,那是...
「就算脫衣服的方式有魅力的女孩子很多,但穿衣服的方式有魅力的女孩子卻不是那麼多。」我喃喃地對自己複述著村上講過的真理,女孩坐在床角略顯吃力地正在把雙腿塞入煙管褲中。
她終於站起了身,穿上米色小羊皮外套,轉身走過來在我額頭上吻了一下,然後走出房間。不規則的金屬撞擊聲傳來,是在門口那只大碗裡撈鑰匙的每天例行公事,然後是開門和關門聲,高跟鞋逐漸遠去的下樓聲。
我伸了伸懶腰,從床上爬起,信步來到窗前低頭眺望,女孩正一手壓著敞開的公寓大門,對微微顫顫地進門的老太太說了聲日安,那是...
»看全部
作者序
後記
會開始寫短篇其實是場意外。
有一陣子我寫作遇到很大的瓶頸,總覺得不管什麼主題,寫出來的東西都像潑婦罵街。雖然我從不避諱說自己寫作的目的是要達到西方文學中那種「偷偷背後插讀者一刀、讀者還連聲道謝」的嘲諷境界,但字正腔圓地罵人,就算只是在紙面上,罵久了自己也會懷疑起這裡面意義何在。
有一天我發現自己正在寫的本來是隨筆文章,竟然無端自動長出虛構的劇情來,然後隨著劇情發展越寫越順手,欲罷不能,最後停筆時,眼前是一篇饒富趣味的半隨筆半故事的文章,而且創作的核心動機比原本用隨筆角度下筆時更...
會開始寫短篇其實是場意外。
有一陣子我寫作遇到很大的瓶頸,總覺得不管什麼主題,寫出來的東西都像潑婦罵街。雖然我從不避諱說自己寫作的目的是要達到西方文學中那種「偷偷背後插讀者一刀、讀者還連聲道謝」的嘲諷境界,但字正腔圓地罵人,就算只是在紙面上,罵久了自己也會懷疑起這裡面意義何在。
有一天我發現自己正在寫的本來是隨筆文章,竟然無端自動長出虛構的劇情來,然後隨著劇情發展越寫越順手,欲罷不能,最後停筆時,眼前是一篇饒富趣味的半隨筆半故事的文章,而且創作的核心動機比原本用隨筆角度下筆時更...
»看全部
目錄
巴黎公寓物語
在瑪黑
線性人生與巴黎女孩
我是這樣地愛上了那個愛上你(妳)的自己
白開水
番茄系義大利麵
如果一個人抓到穿過麥田的人
絕對清醒
請以分手為前提跟我交往
後記
在瑪黑
線性人生與巴黎女孩
我是這樣地愛上了那個愛上你(妳)的自己
白開水
番茄系義大利麵
如果一個人抓到穿過麥田的人
絕對清醒
請以分手為前提跟我交往
後記
商品資料
- 作者: 諾弗勒
- 出版社: 美好事物 出版日期:2015-02-08 ISBN/ISSN:978986877854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6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