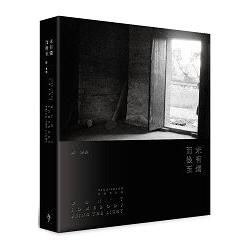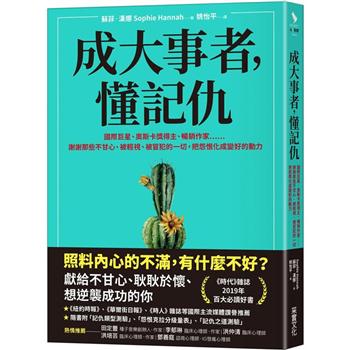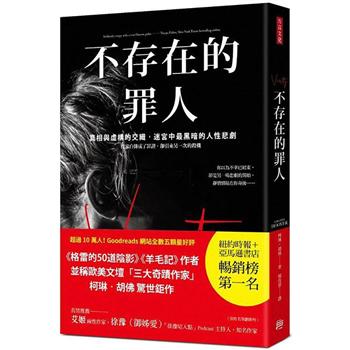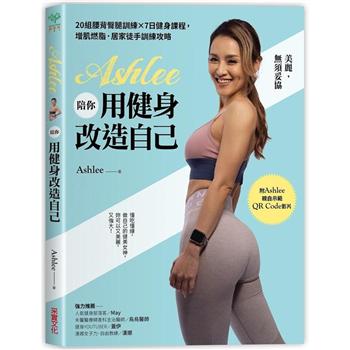★ 華人圈唯一跨足攝影、電影、語言學、哲學領域,身兼理論、評論、創作者的陳傳興,首部個人攝影集。
★ 陳傳興個人精神史第一部,繁中與英文對照,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攝影展同步推出。
★ 與雅昌藝術集團合作,使用雅映四色黑白專利印刷技術。
《未有燭而後至》書名出自《禮記》的〈少儀〉:「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意為「身在暗處,先至者告訴後來者以暗處之情形。」
本攝影集包含119張1970至1980年代間臺灣日常影像,意不在強調攝影者的美學或玩弄光影的技術,亦非談論攝影作為溝通語言或工具,更無關微觀個人或宏觀社會的回憶,而是在銀鹽凝結的40年後,從多所遺失損毀的底片中,抽取出其中119次觀望。
年少時期的陳傳興,前往蘆洲、林家花園、蘭嶼、臺北車站、羅東等地,拍攝了一場葬禮、忙碌的正午火車站、戲曲的觀眾與演員等日常影像,這不是一場場少年的壯游冒險,少年陳傳興看見的是無數互相隔離與連通的世界,以及如絲般存在於人類、亡魂、世代、場所之間的空間通道、時間通道、語言/非語言通道。在「日常」這個場景舞臺上,有著面孔與內在世界的無限組合,人生的角色與戲曲的角色上戲下戲,攝影/鏡頭/底片只是恰巧捕捉了這個舞臺上的燈光(光與影)。
手持傳統相機的少年陳傳興,觀看著現實世界這個永恆進行中的劇場,等待著按下快門,與旅人進行移動之間的等待互相對照。而當他按下快門的那一刻,他從等待者轉為祈請者,祈請作為這一切的發生者與終結者。暫態,流動的現實世界被銀鹽定格。
當我們觀看這系列作品,表示少年陳傳興眼中所見的世界被觀看著,只不過少年陳傳興的世界是透過相機鏡頭──正好也是一具觀看的機械──在被觀看。這是雙重的觀看,交迭的複數世界。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未有燭而後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00 |
攝影 |
$ 2000 |
攝影 |
$ 2000 |
攝影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未有燭而後至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傳興
學者、導演
1952年出生於臺北
法蘭西藝術與文學勳位軍官勳章受勳人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
行人出版社創辦人
陳傳興先生長期耕耘美學、哲學、精神分析與影像論述等領域,同時有學者、作家、攝影者、藝術評論者與電影創作者等多重角色,也是一位勇於面對公民運動做出反應的思想家。他以哲學基礎來詮釋臺灣的現代面向,在他身上隱然看得到法國重要哲學和知識傳統的影響與特有風範。其出版著作包括《銀鹽熱》、《木與夜孰長》、《憂鬱文件》、《攝影美學七問》、《道德不能罷免》等。影像和技術哲學思辨的論文如《螢幕》、《鏡夜》等,其特出觀點及論述每每引起學者熱烈迴響。
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十年間,陳傳興先生留學法國,先後鑽研文學、攝影、電影、戲劇、藝術、符號學與精神分析理論等不同領域,師承法國電影理論大師克利斯蒂安.梅玄 (Christian Metz),並獲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法國學成歸國後,于1998年創立行人出版社,致力引介法國當代文化思想,包括主持翻譯以佛洛伊德思想為軸心的法國精神分析經典《精神分析詞彙》,以及布賀東的《娜嘉》、傅柯的《外邊思維》、布朗.修的《黑暗托馬》、蕭沆的《解體概要》、亞祖.貝彤的《HOME》、與LOUIS VUITTON合作《路易威登:傳奇旅行箱100》、題材前衛的《革命將至》、李維-史陀的《月的另一面》、《我們都是食人族》,以及法國史重量著作《記憶所系之處》等書籍。十多年來透過行人的出版,使得兩岸學界及年輕學子得以親炙法國思想界諸多經典作品。
陳傳興先生以紀錄片創作為基礎所開展的社會文獻和檔案深挖的實踐,集文化研究和影像創作為一體,先後拍攝如《移民》、《阿坤》、《鄭在東》、《姚一葦口述史》等紀錄片。2009年以來,推動系列紀錄電影專案「他們在島嶼寫作」,執導其中兩部《化城再來時》、《如霧起時》。該專案現已開展兩期,在海峽兩岸的觀眾和文化界引起深度反響。
陳傳興
學者、導演
1952年出生於臺北
法蘭西藝術與文學勳位軍官勳章受勳人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
行人出版社創辦人
陳傳興先生長期耕耘美學、哲學、精神分析與影像論述等領域,同時有學者、作家、攝影者、藝術評論者與電影創作者等多重角色,也是一位勇於面對公民運動做出反應的思想家。他以哲學基礎來詮釋臺灣的現代面向,在他身上隱然看得到法國重要哲學和知識傳統的影響與特有風範。其出版著作包括《銀鹽熱》、《木與夜孰長》、《憂鬱文件》、《攝影美學七問》、《道德不能罷免》等。影像和技術哲學思辨的論文如《螢幕》、《鏡夜》等,其特出觀點及論述每每引起學者熱烈迴響。
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十年間,陳傳興先生留學法國,先後鑽研文學、攝影、電影、戲劇、藝術、符號學與精神分析理論等不同領域,師承法國電影理論大師克利斯蒂安.梅玄 (Christian Metz),並獲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語言學博士。法國學成歸國後,于1998年創立行人出版社,致力引介法國當代文化思想,包括主持翻譯以佛洛伊德思想為軸心的法國精神分析經典《精神分析詞彙》,以及布賀東的《娜嘉》、傅柯的《外邊思維》、布朗.修的《黑暗托馬》、蕭沆的《解體概要》、亞祖.貝彤的《HOME》、與LOUIS VUITTON合作《路易威登:傳奇旅行箱100》、題材前衛的《革命將至》、李維-史陀的《月的另一面》、《我們都是食人族》,以及法國史重量著作《記憶所系之處》等書籍。十多年來透過行人的出版,使得兩岸學界及年輕學子得以親炙法國思想界諸多經典作品。
陳傳興先生以紀錄片創作為基礎所開展的社會文獻和檔案深挖的實踐,集文化研究和影像創作為一體,先後拍攝如《移民》、《阿坤》、《鄭在東》、《姚一葦口述史》等紀錄片。2009年以來,推動系列紀錄電影專案「他們在島嶼寫作」,執導其中兩部《化城再來時》、《如霧起時》。該專案現已開展兩期,在海峽兩岸的觀眾和文化界引起深度反響。
目錄
推薦序 以「延遲」的方式與死亡對決──觀陳傳興攝影有感(顧錚)
自序
I
1-1 蘆洲
1-2 荒場:林家花園
1-3 悼亡
1-4 艋舺
1-5 花蓮輪
1-6 蘭嶼:交通輪
1-7 蘭嶼
1-8 淡水
1-9 臺北車站
II
2-1 子弟戲
2-2 戲班
2-3 坤旦
2-4 午後流浪藝人
2-5 複像
圖版索引
作者年表
自序
I
1-1 蘆洲
1-2 荒場:林家花園
1-3 悼亡
1-4 艋舺
1-5 花蓮輪
1-6 蘭嶼:交通輪
1-7 蘭嶼
1-8 淡水
1-9 臺北車站
II
2-1 子弟戲
2-2 戲班
2-3 坤旦
2-4 午後流浪藝人
2-5 複像
圖版索引
作者年表
序
自序
陳傳興
白日熾熱曠野,漸行漸遠消逝在遠方無盡路途,陌生旅人家族,奠祭亡者,一條分隔冥界與人間的曲折山路和白茫茫蒸發逸散的荒草野墳。留不住的人和世界風景回映不在的另一世界。沒有透視黑洞,蔓衍如草的黑線,未斷的冥界臍帶聯結此在和無限。你在那裡?未盡的暗影,等待奧菲斯引路與拯救,卻被不期然的回望溶蝕,允諾與責任全被不完全的愛戀欲望所摧毀,你在那裡?她是否在重墜回永夜的片刻,瞬間,哭泣,失聲或微微細語,有人聽見?他聽見否?他在一個希臘雅典夜宴裡被人嘲諷,未充足愛戀者怎麼可能贖回冥界裡的愛人,他的罪,不願留在冥界長伴逝者,用自己的生命換回逝去的愛戀與戀人。最終他只能帶回眼中暗影,永恆暗影和悔疚。命運用撕裂的暴力死亡懲罰對愛戀作出懷疑的他。為什麼在冥界與人間的分界處,即將走出永夜,他卻不能等待,急切回望,就是懷疑愛戀,而愛戀需憑藉肉體方才為真?還是,等待與觀看的不足時間?等待誰?誰在等待?等待觀看?觀看等待?等待倫理發生?小鎮照相館,玻璃倒影重迭反復,覆掩住相機鏡頭,指向對街醫院,疾病和新生,小鎮的隱喻。灰朴樸靜靜滯立在窗裡,只有等待,被隔離的等待透明流動無人街景,沒有事件,也沒任何言說。不屬於任何人的不知是否在觀看的觀看機械,世界在彼方他處。它靜默,給予靜默。背後庭燎明煌閃爍,少年執燭立於暗夜長路等待未知陌生賓客,遲至赴宴者,夜未央露其冷。前導引路,指明位置,但不能指名,誰是誰。帶路少年不是神曲裡的維吉爾,他沒有言說的權力,他不是教諭者而是正要被啟蒙教導的少年。夜宴的主人向遲到的賓客介紹已在座者,少年默然傾聽等待賓客入座後,重複等待和引路;此即「少儀」,少年成長儀式,禮與倫理關係的學習和實踐。未有燭而後至者,是遲到者,也是少年。舉燭照明暗路他者,借此少年反身自照于靜默,于語言生成之前的陌生遲到賓客顏面之前,他尚未是迎納賓客的主人,他只是延遲的倫理關係見證者。
他舉燭引路,等待暗夜中遲至的陌生賓客贈與光照,展開倫理道路。少年沒有語言,不能直面陌生來者。立足內與外的邊隙位置,聯絡明與暗。他即等待。「少儀」一套儀軌,倫理儀式交滲美的發生。儀,禮的理性秩序和美的偶然。「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燭火光照的倫理位置在於其應然責任,出現在言語和詩的取消,美的雙重否定,明明暗暗閃爍不定的燭火。語言和詩的虛無禮贊。
等待,等待光,事件和現象。讓光進入暗室,煉金魔法囚禁波動不止的光,碎裂成千萬微粒,光的遺址,光的殘骸,鍍金描銀如聖像等待重返世界,顯露於光照之中另個囚所居停。等待流轉,放逐游離諸種觀望,再度沉入永夜,哀悼遺忘,記憶不在,重複再制無歌無言的孤獨黑夜長照。無盡在無限。學習等待在鏡及閘之間的時間縫隙,迎納陌生魅影群聚夜宴。等待先于回憶,先於觀看欲望,欲望觀看。等待,時間的重量,時間的罪和羞恥,闇然滲入鏡前他者,顏面、世界與事物。執燭者肅穆沉默立于白日長夜,抑止了任何情感可能,取消了語言權力和能力,不能吟唱者如何有詩?夏夜農舍曬穀場上,謝神獻祭,沒有酒神狂歡,秋收學戲念唱扮作重走人神之間無形祈禱之路,遠越任何可計數的時間,朝向等待。諸神降臨,時間季節和大地的對話,等待。卑微與悲憫的等待。一如喪禮中悲送亡的家人,哀泣伴隨亡者,一場又一場的哀悼儀式劇場,重溯千年永別的無時間死亡秩序,像是為了召喚死亡而非對亡者的追懷記憶,記憶只是生者自我的語言和欲望,在死亡的片刻場景,悼亡場景中那是對亡者的不敬和羞辱,亡者已非他者,他是黑夜等待死亡見證,真實化之。死亡不屬於任何人,即使曾有人說動物沒有死亡,但死亡不可能被擁有。死亡不可見,那這些種種影像,叩問闇默,等待反諷?
將只是某種飄散空中煙霧,不會凝聚,也不屬於任何人,消失不見為其終極命運。荒蕪廢墟,驛站和海船旅人,漂泊在城市夜街,稻田村野的流浪者,放逐荒島罪犯和被忽略族人。偶然讓我交錯,面向無名的陌生人,也許有些名稱斑駁殘留,那所謂曾經的方鑒齋、開軒一笑亭等等都只是空洞的時間痕跡,如同蘭嶼、艋舺地理標記占住地圖方位一丁點而已。我能否再度召喚他們,從黑暗,從閃爍如星辰銀鹽海中,從永眠長夢中,離開長夜進入觀看世界,放棄遺忘的幸福,碰撞再記憶的羞辱,變異,和批判?我有權力,還是我有責任去承擔,而不是去存取再造它們?漫長等待我自己至今都尚未能理解的謎,它們在那裡,在那裡?嘲諷還是必然,此刻,我祈請它們再現,回應我的無盡疑問時候,卻是它們的銀塑囚所崩解的終極時刻。不再有星辰銀粒,震顫噴灑微點取而代之。不可見的數列,至上規定一切的驚懼顫抖,微微銀粒星辰的黑夜禮贊不再,只有不安,恐懼的愉悅。它們會在那裡?等待再度的偶然自由?
陳傳興
白日熾熱曠野,漸行漸遠消逝在遠方無盡路途,陌生旅人家族,奠祭亡者,一條分隔冥界與人間的曲折山路和白茫茫蒸發逸散的荒草野墳。留不住的人和世界風景回映不在的另一世界。沒有透視黑洞,蔓衍如草的黑線,未斷的冥界臍帶聯結此在和無限。你在那裡?未盡的暗影,等待奧菲斯引路與拯救,卻被不期然的回望溶蝕,允諾與責任全被不完全的愛戀欲望所摧毀,你在那裡?她是否在重墜回永夜的片刻,瞬間,哭泣,失聲或微微細語,有人聽見?他聽見否?他在一個希臘雅典夜宴裡被人嘲諷,未充足愛戀者怎麼可能贖回冥界裡的愛人,他的罪,不願留在冥界長伴逝者,用自己的生命換回逝去的愛戀與戀人。最終他只能帶回眼中暗影,永恆暗影和悔疚。命運用撕裂的暴力死亡懲罰對愛戀作出懷疑的他。為什麼在冥界與人間的分界處,即將走出永夜,他卻不能等待,急切回望,就是懷疑愛戀,而愛戀需憑藉肉體方才為真?還是,等待與觀看的不足時間?等待誰?誰在等待?等待觀看?觀看等待?等待倫理發生?小鎮照相館,玻璃倒影重迭反復,覆掩住相機鏡頭,指向對街醫院,疾病和新生,小鎮的隱喻。灰朴樸靜靜滯立在窗裡,只有等待,被隔離的等待透明流動無人街景,沒有事件,也沒任何言說。不屬於任何人的不知是否在觀看的觀看機械,世界在彼方他處。它靜默,給予靜默。背後庭燎明煌閃爍,少年執燭立於暗夜長路等待未知陌生賓客,遲至赴宴者,夜未央露其冷。前導引路,指明位置,但不能指名,誰是誰。帶路少年不是神曲裡的維吉爾,他沒有言說的權力,他不是教諭者而是正要被啟蒙教導的少年。夜宴的主人向遲到的賓客介紹已在座者,少年默然傾聽等待賓客入座後,重複等待和引路;此即「少儀」,少年成長儀式,禮與倫理關係的學習和實踐。未有燭而後至者,是遲到者,也是少年。舉燭照明暗路他者,借此少年反身自照于靜默,于語言生成之前的陌生遲到賓客顏面之前,他尚未是迎納賓客的主人,他只是延遲的倫理關係見證者。
他舉燭引路,等待暗夜中遲至的陌生賓客贈與光照,展開倫理道路。少年沒有語言,不能直面陌生來者。立足內與外的邊隙位置,聯絡明與暗。他即等待。「少儀」一套儀軌,倫理儀式交滲美的發生。儀,禮的理性秩序和美的偶然。「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燭火光照的倫理位置在於其應然責任,出現在言語和詩的取消,美的雙重否定,明明暗暗閃爍不定的燭火。語言和詩的虛無禮贊。
等待,等待光,事件和現象。讓光進入暗室,煉金魔法囚禁波動不止的光,碎裂成千萬微粒,光的遺址,光的殘骸,鍍金描銀如聖像等待重返世界,顯露於光照之中另個囚所居停。等待流轉,放逐游離諸種觀望,再度沉入永夜,哀悼遺忘,記憶不在,重複再制無歌無言的孤獨黑夜長照。無盡在無限。學習等待在鏡及閘之間的時間縫隙,迎納陌生魅影群聚夜宴。等待先于回憶,先於觀看欲望,欲望觀看。等待,時間的重量,時間的罪和羞恥,闇然滲入鏡前他者,顏面、世界與事物。執燭者肅穆沉默立于白日長夜,抑止了任何情感可能,取消了語言權力和能力,不能吟唱者如何有詩?夏夜農舍曬穀場上,謝神獻祭,沒有酒神狂歡,秋收學戲念唱扮作重走人神之間無形祈禱之路,遠越任何可計數的時間,朝向等待。諸神降臨,時間季節和大地的對話,等待。卑微與悲憫的等待。一如喪禮中悲送亡的家人,哀泣伴隨亡者,一場又一場的哀悼儀式劇場,重溯千年永別的無時間死亡秩序,像是為了召喚死亡而非對亡者的追懷記憶,記憶只是生者自我的語言和欲望,在死亡的片刻場景,悼亡場景中那是對亡者的不敬和羞辱,亡者已非他者,他是黑夜等待死亡見證,真實化之。死亡不屬於任何人,即使曾有人說動物沒有死亡,但死亡不可能被擁有。死亡不可見,那這些種種影像,叩問闇默,等待反諷?
將只是某種飄散空中煙霧,不會凝聚,也不屬於任何人,消失不見為其終極命運。荒蕪廢墟,驛站和海船旅人,漂泊在城市夜街,稻田村野的流浪者,放逐荒島罪犯和被忽略族人。偶然讓我交錯,面向無名的陌生人,也許有些名稱斑駁殘留,那所謂曾經的方鑒齋、開軒一笑亭等等都只是空洞的時間痕跡,如同蘭嶼、艋舺地理標記占住地圖方位一丁點而已。我能否再度召喚他們,從黑暗,從閃爍如星辰銀鹽海中,從永眠長夢中,離開長夜進入觀看世界,放棄遺忘的幸福,碰撞再記憶的羞辱,變異,和批判?我有權力,還是我有責任去承擔,而不是去存取再造它們?漫長等待我自己至今都尚未能理解的謎,它們在那裡,在那裡?嘲諷還是必然,此刻,我祈請它們再現,回應我的無盡疑問時候,卻是它們的銀塑囚所崩解的終極時刻。不再有星辰銀粒,震顫噴灑微點取而代之。不可見的數列,至上規定一切的驚懼顫抖,微微銀粒星辰的黑夜禮贊不再,只有不安,恐懼的愉悅。它們會在那裡?等待再度的偶然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