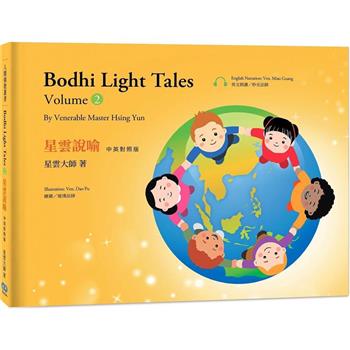思考、觀察臺灣自然書寫必然通過的一條路徑……..
生態批評顯然不只是文學研究,它同時需要科學研究、價值體系的支持,但它卻也不是鹵莽的道德判斷。
吳明益從第一次純為自然所眩迷的經驗開始,十多年來縱身投入學術研究,儘管,論述讓其思考環境各個層面的議題時都充滿痛苦,但這種痛苦在某些時刻,回過頭去提醒著領略生態之美的迷人與快樂。
本書透過拋出生態批評的議題思維,邀請你一同以思考凝聚行動力,參與解放自然的實踐運動。
◎關於《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3》
1983年,韓韓與馬以工共同出版了《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可說是臺灣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的濫觴。之後的20餘年,其開始蓬勃發展,如同飲食文學、旅遊文學、同志文學等一般,成為臺灣文學譜系中的重要分支,但對於自然書寫,大家仍存有一個模糊的定論和想像。因此臺灣文學史上,第一套完整論述臺灣自然書寫的經典著作於焉而生。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論述,2012年1月三冊同時登場,可依讀者興趣閱讀和蒐藏。BOOK 3《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是一部「不只是論述」的論述專書,讀者閱讀的將不只是靜態的論述評論而已,更可感受到的是一股認真、浪漫與熱切的行動力量。
誠如作者於修訂版總序所言:「論述讓我思考環境各個層面的議題時都充滿痛苦,這種痛苦在某些時刻,回過頭去提醒我感受生態之美的迷人與快樂。這麼多年來,我仍在書本與野地受著自然的教育,這系列的寫作,不只是為了學院裡的讀者,也為學院外的讀者。因此,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只要活著,我會繼續痛苦並快樂著地思維下去。」
◎自然書寫重要論述文集
自《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待自然書寫的探索》(2004)出版後,吳明益於近年來亦發表過許多關於自然書寫的論述,《自然之心──從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即收錄相關文章共九篇,內容從生態發展、環境倫理、自然書寫到生態批評,為跨入第二階段的研究。這本書為初步的研究成果,吳明益同時參與一些生態團體,持續保持固定的野外踏查習慣,參與部分環境運動,本書為其參與環境行動過程中,重新回頭自我檢視,重新展開論述的一枚基石。
作者簡介:
吳明益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有時候寫作、畫圖、攝影、旅行、談論文學,副業是文學研究。
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長篇小說《複眼人》、《睡眠的航線》,論文《以書寫解放自然》。另編有《臺灣自然寫作選》,並與吳晟共同主編《濕地‧石化‧島嶼想像》。近期作品為短篇小說集《天橋上的魔術師》。
曾三度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金石堂年度最有影響力的書、誠品年度推薦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聯合報小說大獎等等。
章節試閱
荒原?試論台灣自然書寫中的「濕地」
一、自然書寫中的水意識與水倫理
接續上一篇文章進一步思考,自然地景事實上不是獨立存在的小生態系,而是聯構為一個地球生態系的「生境」。舉例而言,河流生態系不可能獨立存在,它與山岳的生態系、濕地生態系、海洋生態系都有密切關聯。
我曾在2004至2007年間,也曾踏查東部海岸、溪流,而寫了一本名為《家離水邊那麼近》(2007)的散文集。發現河流與海洋銜接的生態區,往往是變動最劇的區域,河流會影響近海的海灘(包括沙灘的形成),乃至於有機物質的分布與沉澱,成為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現今學者多半將其獨立出來,稱為「濕地」(wetland)。濕地是整體生態系統中碳匯服務(carbon sink) 最高的一種生態系,但往往因為看似荒原而被遺忘。
在文學研究中,海洋文學在台灣相較之下一直都是最受關注的「自然地景」書寫,或重要的象徵景觀,特別是近年的海洋文學研究相對蓬勃。過去台灣的海洋文學研究,多半採取較寬鬆的海洋文學定義(即含括虛構與非虛構文學,應說是包含了海洋文學與海洋書寫。詳細論述請見下節),但其實有時亦會納入海岸相關書寫,因而就會把書寫濕地生態的文本一併含括進去了。而討論描寫河流的文本時,有時也會將河岸濕地的作品一併納入談論。
濕地在科學上獨立為一個被研究的生態體系,雖是晚近的事,但卻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水文生態系統。相對之下,文學研究是否有可能將這個生態區位的書寫獨立出來討論,以便能更細膩地解析出其中的意義?並且與河流、海洋書寫比照,呈現出作家敏銳的觀察與反省?這即是本文的基源提問,而我也認為這是處理台灣文學中「水意識」的一個重要關鍵。
書寫濕地的作品為何值得獨立出來討論?我想從自然科學研究的理由談起。
二、在科學與文學視野中消失的濕地
在生態學相關研究發展的漫長時間裡,直到上個世紀中,濕地仍常被視為荒蕪之地,因此成為棄置垃圾、開發為工業區、築路築堤的處所。非止是文學研究不會將此地景視為重點,自然科學研究也往往忽視。
直到1971年,聯合國在伊朗拉姆薩召開了濕地會議,與會學者廣泛交換了濕地對生態系的貢獻,才引起世人的重視。當時所簽定的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也因此成為現今定義濕地的重要文獻。
濕地在中文中過去以「坔」來表現,意即有水有土之地。若依據現今國際上較被接受的拉姆薩公約,對濕地的定義是「草澤、泥沼地、泥煤地或水域;不管其為天然或人為、永久或暫時、死水或活流、淡水或海水,或兩者混合、海水淹沒地區,水深低潮時不超過六公尺者。」(For the purpose of this Convention wetlands are areas of marsh, fen, peatland or water, whether natural or artificial, permanent or temporary, with water that is static or flowing, fresh, brackish or salt, including areas of marine water the depth of which at low tide does not exceed six meters.)
根據這樣的定義,公約又再分這些濕地為「海洋/海岸濕地」(Marine/Coastal Wetlands)、「內陸濕地」(Inland Wetlands)與「人工濕地」(Human-made Wetlands),並又進一步區分出42種類型。而這42種濕地,國內學者通常再歸納為「海岸濕地」(Marine Wetlands)、「河口濕地」(Estuarine Wetland)、「河岸濕地」(Riverine Wetlands)、「湖泊濕地」(Lacustrine Wetlands)四種主要類型。
台灣的濕地保育發展很晚,直至2006年10月才由內政部成立「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2007年4月9日的「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第二次會議」,才決議未來將國家重要濕地分為「國際級」、「國家級」、「地方級」、「未定」等數種位階。
1972年美國通過Clean Water Act,這個行動公約制訂了一個非常高標準的方案,那就是希望所有地表水都回復到原始的潔淨狀態,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濕地監測標準。 自此世界各國紛紛開始注意濕地的生態系功能,學者不再認為濕地是一堆一下子有水,一下子沒水的爛泥巴,生長一堆讓人過敏、蚊蟲聚集的無用植物而已。過去濕地被認為是無用之處,但事實上濕地雖僅占全球表面積的百分之十八,但生產力卻占了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九十的漁獲都是從濕地生態系獲取的。濕地同時具有淨化水質、過濾污染物、製造氧氣、調節氣候、保護海岸等功能,更是陸生生物、水生生物的避難所。
而根據學者的分析,濕地的生態系統服務項目,其中與人類相關的有下列幾項:Defeo et al. (2009)彙整了海岸濕地廣泛的生態系統服務項目,其中有許多是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包括: (1) 沉積物的儲存與輸送,(2) 波浪的消散以及極端事件(颱風暴潮與海嘯)的緩衝功能,(3) 能即時但有限度地反應海平面上升,(4) 分解有機物與汙染物,(5) 過濾與淨化水質,(6) 營養礦化與循環,(7) 水的儲存與地下水的釋出,(8) 生物多樣性的維持與基因庫的儲存,(9) 稚魚的孵育場,(10) 水鳥與海龜的築巢地以及鰭足類的群棲處,(11) 鳥類與陸棲野生動物的食餌來源地,(12) 景觀遊憩,(13) 人類食物來源以及(14) 陸域與海域環境的連接處。海岸濕地每年所提供的服務價值達一千七百兆美元之多,佔全球各型生態系所提供經濟總值之53%。 由此可知濕地在整體生態系上的重要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濕地生態系由於其地理位置的關係,和海洋、河流、湖泊等生態系密切相關,難以切分,且同屬於水文地景,因此在科學上當然有時也會被合併討論。同樣的情形,濕地相關書寫既然過去也未被特別提舉出來,文本也就常被收納至其它較常討論的文學議題中。海洋文學與海洋書寫的量最為大宗,在最廣義的定義下,它往往吸納了海岸濕地與河口濕地的描寫作品。其次便是僅有筆者撰述過的河流書寫/文學,它吸納了描寫河岸濕地與部分河口濕地的作品。至於湖泊書寫/文學,雖然數量不多,但亦確實存在著不少專以寫湖的篇章。
我認為不論是自然科學或文學研究,在特定定義某種「類型」之時,目的一方面是要突顯此一類型的重要性與特異性,一面又是為了說明此特異性與重要性,其實是與其整體其它部分環環相扣、密切相關的。因此,若能透過整理與分析,說明台灣描寫濕地作品的獨特意義,將有助於釐清創作者為何面對不同地景時會有不同的想像:諸如大海總是象徵無盡與廣闊,作者往往在其中寄寓傷痛,或放逐心靈;河流則分隔兩岸,溯流往往存在著尋根的象徵;而濕地看似荒原,卻在自然作家筆下,反而刻意著重荒涼中的「盎然生機」……。這些想像是從地景的哪部分特色衍生出來的?其間是否暗示了人類面對不同地景時,人與環境互動的關係?這是我一系列探討「水意識」的文章,極具關鍵性的探討。
由於一篇文章能呈現的討論焦點有限,河流書寫/文學仍有待清理,湖泊書寫/文學仍有待清理,而「海洋文學」向來是台灣文學中極被關注的議題。在海洋文學/書寫中,由於只有鮮少作者有「離岸航行」的豐富經驗,因此相關的討論向來存在著盡可能廣義處理相關題材的方式進行,部分學者甚且認為應該納入海岸的書寫,以豐富海洋文學/書寫的意涵。
我個人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因此,濕地的描寫,恰好提供了我一個探索、思考的「交匯區」。
三、海洋的邊緣與河水的盡頭是濕地
台灣的海洋文學成為文學研究中的顯學,一方面相關的編選不輟,幾乎是次文類文選裡頭僅次於旅行與飲食書寫的類型。《大海洋詩刊》與林燿德編選的《中國海洋文學選》等相關文獻,已重被文學研究者重視 ,2011年則甫由郭強生編出一本《作家與海》,所選以詩與散文為主,而散文則含括了一般學者認定的自然書寫者(如劉克襄、廖鴻基、杜虹、吳明益等)與非自然書寫者(如楊牧、陳黎、林文義、林清玄等)的作品。近年海洋文學的研究聚焦在廖鴻基與夏曼•藍波安兩位具有豐富航海經驗的海洋作家身上,因此,這本選集有再把視野再拉廣的意味。
但事實上,把海岸,或寫作者描述海岸濕地,或將「岸上觀看者」所書寫的作品納入海洋文學,早在林燿德編選相關選集時已是如此,也是過去論述海洋文學的常態。楊政源〈尋找海洋文學─試析「海洋文學」的內涵〉一文,試著將海洋文學定義為「是以自然海洋、海岸(濱海陸地)的環境及在其上所生成的人文活動為主題,並有明確海洋意識的文學作品。」 這樣的定義可以看出來是較寬鬆的,並不一定要求寫作者具有航海經驗,連濱海陸地上的「人文活動」都含括在內了。而其重點乃在於「海洋意識」。
不過這個「海洋意識」也相當難以捉摸,畢竟海洋意識一詞無分「正面的海洋意識」或「負面意義的海洋意識」,因此也很可能變得相當籠統。不過這樣的定義,恰好可以看一九八○年後,才漸次發展的「現代自然書寫」中,論及海洋文學或海洋書寫時,較嚴格指涉作者需有非虛構經驗的定義,有了對照性的意義。楊政源很清楚這一點,他在文中比對了陳思和、林燿德、黃騰德、張瑞芬、李奭學、東年、黃聲威等人和我的說法,至少條理分明地將文學論述中「海洋文學」一詞清楚析流。他認為所謂自然書寫指涉的是較嚴格的非虛構寫作,海洋文學自可另外拓展向虛構文本,乃至於非虛構寫作裡,雖非具有自然知識,但具有海洋意識的相關作品。
相較之下,同年後出的吳旻旻〈「海/岸」觀點:論台灣海洋散文的發展性與特質〉,則出現相異的論述,我認為其間有幾個問題值得商榷:一、作者認為台灣海洋文學僅夏曼•藍波安、廖鴻基外,極少人投入耕耘。作者認為:「假如描寫海洋生態或海上生活才算海洋文學,那麼這個文學類型勢必難以興繁茂盛,因為從事航海、捕魚或海洋生態考察同時又能執筆創作的人畢竟少之又少。」 這段話第一個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台灣作為一個海島,就「一定」得有相對應繁多的海洋文學?更令人不解的是,研究者為了要「納入」更多作品到海洋文學的論述中,而認為其定義應該擴大,將沒有實際經驗的作品也一併討論。當然定義不是確定的,可以在合理的論述下改易並沒有問題。比方說作者可以宣稱在蒐羅文本後,發現有大量具海洋意識的作品因此被排除在論述之外,因此試著調整定義,或者也可以試圖比較有實際航海經驗的文本與沒有實際離岸經驗文本的差異。但宣稱一種次文類因定義過狹,因此少人耕耘,我認為這是倒果為因的推論。即便是自然書寫的定義較嚴格,而不把某些虛構作品視為「海洋書寫」(特意用「海洋書寫」一詞,是因為本文一開始即已宣稱以「書寫」來指涉非虛構作品,「文學」指涉虛構作品),顯然也不是對這些作品的貶抑,只是不同寫作形式的作品,不宜放在一起用同一標準評價而已。吳旻旻當然可比持和他人不同的定義,卻不能說他人較嚴格的定義,是造成「台灣海洋文學難以興繁茂盛」的理由。
二、作者說:「自然寫作者或是生態學者往往對『文學性』持保留態度」、「多數生態學者、自然寫作者對『文學性』的認知有些偏頗」 。事實上,該文參考書目列舉了我的《以書寫解放自然》,而這本書第二章「感性的自然地誌」,明確地說明了文學在自然書寫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以文學促使自然書寫成為一種負載自然地誌的軟性載具,甚至以實例說明了自然書寫的幾種文學表現形式。 其實應該說幾乎沒有研究台灣自然寫作者不重視這類書寫的文學性表現才對。吳旻旻的文章缺乏指證。
而該論文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否應將「濱海而觀者(立足岸上)所描繪、闡述海洋的作品」 納入海洋文學的討論?其實與楊政源的說法無異,楊政源已解釋了這屬於「傳統派的海洋文學定義」。而由於吳旻旻的閱讀重點放在「站在海濱觀海」這樣的角度上,因此文中僅提及楊牧、林文義、周芬伶等,及張堂錡、楊照的軍旅散文中,描寫到海洋的段落,顯示出吳的定義雖然寬鬆了,相關閱讀卻未周延,特別是遺漏了自然書寫者描述海岸濕地的段落。
從楊政源、吳旻旻的文章,雖然從文學的論述角度提出了海洋文學的特質,卻也讓我想起人文學者在思考自然書寫相關議題時,因相對缺乏自然科學常識,而容易忽略了一些問題點。
楊牧等人的作品,固然從文學的角度上來看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對海洋文化的想像性作品,但另有一些人同樣是「濱海而觀者」,卻能夠帶我們同時觀看生物如何利用這塊濱海之地,乃至於反省人類因私利而對環境造成如何的傷害的文學作品。這類作品在兩相對照之下,雖同屬「海濱」之作,視野卻大不相同。而我認為這些站在海的邊緣、河的盡頭的濕地書寫,或許可以讓我們看出這類寫作者的特殊觀察與特殊視野,而成為獨具意義的一系列作品。
(未完)
荒原?試論台灣自然書寫中的「濕地」一、自然書寫中的水意識與水倫理接續上一篇文章進一步思考,自然地景事實上不是獨立存在的小生態系,而是聯構為一個地球生態系的「生境」。舉例而言,河流生態系不可能獨立存在,它與山岳的生態系、濕地生態系、海洋生態系都有密切關聯。我曾在2004至2007年間,也曾踏查東部海岸、溪流,而寫了一本名為《家離水邊那麼近》(2007)的散文集。發現河流與海洋銜接的生態區,往往是變動最劇的區域,河流會影響近海的海灘(包括沙灘的形成),乃至於有機物質的分布與沉澱,成為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現今學者...
作者序
痛苦並快樂著/吳明益
住到紅樹林以後我偶爾朝淡水河流往大海的相反方向慢跑。多數時候我帶著相機,想像數年後說不定可以寫出一系列的「慢跑觀察筆記」。有一回我沒帶著相機,空中遠遠地飛來大約超過五十隻的鳥群,高度並不高,飛行速度穩定,那隊伍的陣式像是隱涵了什麼意味似地前進。我不知不覺地停下腳步,抬頭仰望。
彼時我肯定感受到一種美。可是就在那一刻的下一個瞬間,我辨識出那是臺灣的外來鳥種埃及聖(睘鳥)。埃及聖(睘鳥)是體型巨大的涉禽,近年開始有鳥友和政府單位注意牠可能對此地鳥種造成的生態排擠效應,因此正在對牠們進行族群抑制的計畫,比方說在牠們的鳥蛋上噴油以降低孵化率。也就是說,在此地整體的生態觀上,有些生態學家認為埃及聖(睘鳥)或者是一種需要排除、或是抑制的生物之一。
但彼時我肯定感受到一種美。可是那是外來種呢,從理性上來看,我該恨牠們的,不是嗎?
我試著往心裡頭尋找所謂的「理性」,它就像在人的掌中故意蜷縮軀體,掉入草叢中的一隻瓢蟲,印象雖在,卻又如此模糊。我對自己的意識與思維的流動掌握度是那麼低,低到無法確認自己信仰什麼。就拿埃及聖䴉來說,難道我對牠們的美的感受只是像性慾一般的直覺,而恨竟爾來自理性?
其實大多數的時候,我並沒有感受到美的感動與科學之間的衝突。就像遇到一個白鷺鷥林,做為一個解說員,我們可以說:「鷺科(Ardeidea)鳥類全世界共有六十二種,牠們共同的特徵與習性是:腳比其他一般鳥類為長,以便於涉水,嘴也比較長,可能對於捕捉蛙類、魚類、昆蟲等有幫助。翅膀長而寬略成圓形;飛行時拍翅較慢,頸部彎曲往後收縮。主要棲息於沼澤、河口、 沙洲、水田、池塘及溪流等水域地帶。台灣的鷺科鳥類目前紀錄有二十種,其中八種在台灣繁殖。」也可以像李奧波(Aldo Leopold)說:「在每個轉彎處,我們看到白鷺站在前方的水池中,一尊尊白色的雕像都有一個白色的倒影⋯⋯當一群白鷺在遠處一棵綠柳樹上棲息時,牠們看起來就像一陣太早到來的暴風雪。」這兩者都是人類對鳥的禮讚:理解與想像。這樣的解說員或許因此話說多了些,但給點時間,兩者還是可以並行陳述的。
但有些東西有著更深的觸動,就像文學所帶給我們的震顫之感。比方「聲音生態學家」高登‧ 漢普頓(Gordon Hempton)說:「草原狼對著夜空長嚎的月光之歌,是一種寂靜,而牠們伴侶的回應,也是一種寂靜。」這種「寂靜」同時也是草原上代表掠食者的「最高音」,那既是一種美學修辭,其實也是一種科學認識。我相信許多文學教授會認為這個句子是「美」的,但他們卻不必然理解漢普頓在陳述的不只是一種美感經驗,還是一種理性經驗。掠食者常是一個地區「聲音的最高音」,這是為了宣示獵食領域,是一種寂靜的張揚。聲音與氣味,都可以象徵領域。
部分美學家認為美來自於「直覺」,但直覺卻有很多種。就像我們若獨自在草原上聽到草原狼的長嚎,肯定會產生令一種懼怖到寒毛直豎的直覺。那種直覺,難道也是一種美嗎?
在自然科學中,直覺是一種生存的本能,甚至可以被理性研究,追根探源,或許這便是直覺可以和理性連結的主因。即便這個直覺被解剖了、解釋了,仍然不能否定那瞬間傳遞的美。我肯定數十隻埃及聖(睘鳥)飛越我的天空,那是一種美。但這種美不會強大到讓我忘記思考,比方說,埃及聖(睘鳥)是否已然危及本地生態的問題。思維的樂趣不在進行道德判斷(埃及聖䴉就是為自己而存活著,牠們哪管道德不道德),而在從中尋求解釋/解謎之道。而這種追尋,偏偏又有時讓思考者陷入謎困之中。
《以書寫解放自然》是我到花蓮任教後一年出版的論文集(2004),大約兩三年後,我陸陸續續收到來信問哪裡可以再買到這本書。於是我將原本收在書房的五十本書再交給出版社販售,但隨即後悔不已。有段時間,我真心希望這本書就像一個逝去的演化時代,它在整體的過程中確有意義,卻不宜停留再現。
但有幾個理由,我決定在夏日重新出版這部書的修訂版。
首先是這些年來,這部書成為學界討論臺灣自然書寫的著作之一,因此時有學者挑戰書中的觀點。比方說有的學者認為我詮釋的自然書寫偏向「無人荒野」,或認為太過強調非虛構經驗,或認為我根本忽略原住民文學。我認為這些問題幾乎百分之九十出在質疑的學者沒有真正讀完整部書的關係。我私下猜測,也許是這本書不易買到吧。我不忍心相信,我們學院訓練出來的學者,會連整部書都沒有讀完就自以為是地下結論。
其次,我仍在走在這條思維的路上。在這十年研究自然導向文學的時光裡,有時被美牽引而憎恨論述,有時沉迷於科學的解釋,而遺忘了時時重返野地的必要性。一晃眼當初出版《以書寫解放自然》的我,已變成如此不同的「另一個人」。但就像馬是從始祖馬演化而來的一樣,那蹄子的痕跡還在。我於是有了個想像,日後不論我在哪一家出版社出版關於自然導向文學的論著,書名或許可以都一律稱為《以書寫解放自然》。就從BOOK 1、BOOK 2、BOOK 3、BOOK 4……這樣接續寫下去,直到我放棄書寫為止。這樣的想法或許也多少還帶點年輕時的浪漫感,讓我忘了羞赧,或許這些論述根本不值得被閱讀也不一定。
思維是痛苦並快樂著的事情。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是個實證主義的哲學家,據說五歲的時候人家對他說地球是圓的,他不相信,拿了圓鍬就想挖到澳大利亞去。但羅素同時知道人的知識受限於所見。古埃及人判斷地球是圓的,偏偏古希臘人卻以為世界是平的。羅素認為這不是因為埃及人聰明而希臘人笨,而是因為埃及地勢空曠,容易發現地平線並非直線的事實;濱海的希臘卻多山、多地震,因此想像鯨魚撐住平板的大地,時時晃動。從想像力來說,埃及人跟希臘人都說得很迷人不是嗎?
我以為學術研究這個行當不只是要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有時候也要為自己製造問題,最好還能了解自己不懂哪些問題。當我跑步時,或許我和旁邊的跑者不一樣,因為我是認識埃及聖環,也已經努力建構過腦中對埃及聖(睘鳥)的資訊。於是當牠們飛掠的那一瞬間,我可能同時在腦中體現了美感經驗、搜尋了關於牠們的生態訊息、進行了倫理上的反省,甚至可能告訴自己,這種鳥在埃及可是一種犧帶著文化意涵飛行的鳥,它被認為是(睘鳥)首人身的托特(Thoth)的化身,托特是智慧之神,也是月亮、數學以及醫藥之神。
然而這一切描述,都不得不指向一個嚴竣的提問:人類是否有權利屠殺因為人類才遷徙到此處的一種生物?為什麼我們懲罰的不是當初的始作俑者,而是努力在異鄉求生的生命群體?這樣的提問不亞於部分論者談死刑存廢時,所用的「艱難的殺戮」。
從人類的歷史上,常看到某個時期總有些人種認為另一個人種是需要排除的,即使在生物學上證明,人其實只有一「種」,種族主義者其實不是生物學上的「種間」主義者,他們只是在殘殺同種生物而已。只不過殺戮者通常也能想出一大堆理由,甚且找到科學數據支持那個理由,來繼續殺戮。
或許透過埃及聖(睘鳥)的例子,我可以說明自己所理解的「生態批評」,以及自己為什麼除了創作以外,也試著維繫這系列的研究。生態批評顯然不只是文學研究,它同時需要科學研究、價值體系的支持,但它卻也不是鹵莽的道德判斷。好的自然導向文學都不是以道德教訓為出發點的,相反地,它可能只提出了一種對抗性的主張,凝聚另一種意識。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一生做為一個不合作的公民,威爾森(E. O. Wilson)甘冒眾諱以生物觀察為基礎大談人性,乃至於卡森女士(Rachel Louise Carson)的反化學藥劑⋯⋯誰會怪她沒有發明一種無毒的殺蟲劑呢?而這種對抗性的主張,通常可以在典型的自然作家身上看到,因為生態批評對抗的正是掌權機制或掌權的思維,面對諸如國光石化、阿朗壹古道、美麗灣事件這類環境議題時宣稱是為了大多數人好,而做的「不帶痛苦的決定」。
論述讓我思考環境各個層面的議題時都充滿痛苦,這種痛苦在某些時刻,回過頭去提醒我感受生態之美的迷人與快樂。
在這一系列的《以書寫解放自然》中,我先把2003 年的版本分成BOOK 1、BOOK 2出版,因為這是我進入這個痛苦並快樂著的思維領域的開始。這麼多年來,我仍在書本與野地受著自然的教育,這系列的寫作,不只是為了學院裡的讀者,也為學院外的讀者。因此,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只要活著,我會繼續痛苦並快樂著地思維下去。
痛苦並快樂著/吳明益
住到紅樹林以後我偶爾朝淡水河流往大海的相反方向慢跑。多數時候我帶著相機,想像數年後說不定可以寫出一系列的「慢跑觀察筆記」。有一回我沒帶著相機,空中遠遠地飛來大約超過五十隻的鳥群,高度並不高,飛行速度穩定,那隊伍的陣式像是隱涵了什麼意味似地前進。我不知不覺地停下腳步,抬頭仰望。
彼時我肯定感受到一種美。可是就在那一刻的下一個瞬間,我辨識出那是臺灣的外來鳥種埃及聖(睘鳥)。埃及聖(睘鳥)是體型巨大的涉禽,近年開始有鳥友和政府單位注意牠可能對此地鳥種造成的生態排擠效應,因此正在對牠們進...
目錄
新版總序 痛苦並快樂著
初版序 往前走去,然後回頭
Chapter 1 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 臺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再思考
兩個仍具意義的觀察座標
越界是為了再發現
戀土、覺醒、追尋與棲居
環境對書寫的挑戰
Chapter 2 天真智慧,抑或理性禁忌? 關於原住民族漢語文學中所呈現環境倫理觀的初步思考
在自然書寫研究中刻意被忽視的原住民文學?
是文化回歸,也是文化抵抗
「這裡」就是我們生活的場域
生存環境、維生訓練與禁忌的「理性內涵」
Yggdrasil:在地生態智慧與全球生態知識的聯結
Chapter 3 一種「照管」土地的態度 《笠山農場》中人與其所墾殖土地的關係
小說家只是效法大自然罷了
如何「照管」笠山?
Chapter 4 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 重詮宋澤萊《打牛湳村》到《廢墟臺灣》呈現的環境倫理觀
宋澤萊生態嗎?
存活於文字中的「詩情居所」:那些記憶中美麗的農村
臺灣鄉土的「環境傾圮史」
美的廢棄與心的死亡:一則反烏托邦的預言書
結語:喲呵,福爾摩沙
Chapter 5 文字中的蠻荒 《 大河盡頭》中的禽鳥野獸及自然意識
溯河與記憶
存活於文字中的蠻荒
移動的象徵──禽鳥野獸
隱涵著生的契機:崩解的溯河隊伍與崩解的雨林
Chapter 6 傳遞知識是為了討論價值 臺灣科學/科普書寫中的幾個議題
「文學中心主義」的遺憾?
現代自然書寫的礎石、盟友、同義詞:科學,還是科普書寫?
那些文學研究者略過的書:臺灣近年日漸篷勃的幾種科普類型
真相本身已經很迷人?
結語:科學已經變得太重要了,不能讓科學家決定
Chapter 7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 形構臺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文化構築於自然?一個地理參與文化決定論者提供的可能性
河流書寫與河流文學:書寫者以文字建構河流的心靈圖象
臺灣是「山島」、「海島」、還是「河島」?──形構臺灣河流書寫的地理環境與文化環境
地母的乳汁與眼淚:解讀文學家書寫臺灣河流的一種途徑試演
結語:河流會帶來深山裡的東西
Chapter 8 荒原? 試論臺灣自然書寫中的「濕地」
自然書寫中的水意識與水倫理
在科學與文學視野中消失的濕地
海洋的邊緣與河水的盡頭是濕地
濕地在自然書寫者筆下呈現出的書寫模式特異性
結語:一個水意識的開端─多元的行動主義者
Chapter 9 造心景,抑或安天命? 論劉大任《園林內外》中的園林觀與書寫特質
兩種「造化」:關於劉大任的「園林書寫」
園藝、園意、園憶
人擇的園林,人造的天堂?
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園林的野性
結語:既造心景,又安天命
跋
新版總序 痛苦並快樂著
初版序 往前走去,然後回頭
Chapter 1 戀土、覺醒、追尋,而後棲居 臺灣生態批評與自然導向文學發展再思考
兩個仍具意義的觀察座標
越界是為了再發現
戀土、覺醒、追尋與棲居
環境對書寫的挑戰
Chapter 2 天真智慧,抑或理性禁忌? 關於原住民族漢語文學中所呈現環境倫理觀的初步思考
在自然書寫研究中刻意被忽視的原住民文學?
是文化回歸,也是文化抵抗
「這裡」就是我們生活的場域
生存環境、維生訓練與禁忌的「理性內涵」
Yggdrasil:在地生態智慧與全球生態知識的聯結
Chapter 3 一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