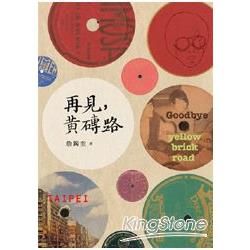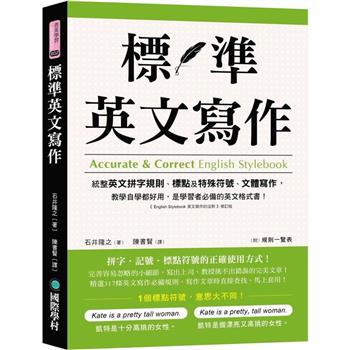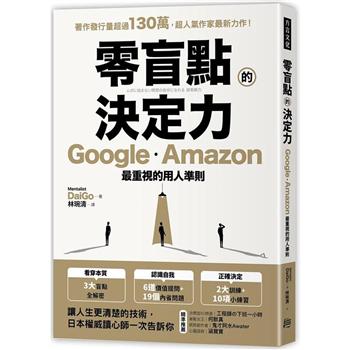民歌手喬也輕輕地撥動琴弦,那些再熟悉不過的西洋歌曲,Elton John、Bob Dylon、Judy Collings……,從他口中幽幽流淌出來。
年輕人浸泡在崇洋氛圍之中,迷幻藥,混雜英文的語言,夜夜留連於搖滾pub狂歡,任憑樂音和幻覺淹沒意識。
喬也哀傷地想,去除美國文化,去除癲狂的沉迷,究竟同代人還剩下什麼。
他試探性地踏出微小的一步,彷彿是Don Mclean的Vincent,那孤獨的先行者: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失落的愛情不知去向。明天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夏天就快要結束了,青春也是。喬也只想有一天,能唱自己的歌。
作者簡介:
詹錫奎
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自由時報》副刊主編,並在自立報系任職,亦曾擔任本土文化公司《新臺灣新聞周刊》發行人兼社長。其創作以小說、散文為主。早期一系列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小說甚受重視,被視為年輕的小說怪傑。1981年出版長篇小說《再見,黃磚路》,描寫七○年代青年徬徨的成長過程,極富震撼力。作家陳映真曾撰文讚嘆:「啊!終於出現這樣的小說了。」後來筆鋒一轉,改以「老包」為筆名撰寫政論文章,對台灣的關切躍然紙上。喜歡音樂,能以吉他自彈自唱,這也是寫出《再見,黃磚路》這本以歌手為人物的小說之原因。
章節試閱
歌唱完,他側過頭,Mikko 一手支頭看他,隱約可以感受到她那清澈靈慧眼光的侵襲。回頭注視著黑鍵白鍵,手指漫不在意的彈著一些樂音。習慣上是這樣,沒有找到次一首歌的情緒前,他就在零落的樂音中尋求。忽然他記起昨天寫的一首歌,翻開本子彈了起來。
我想我應該戴一頂草帽的
街道像一首翻版的老歌
一捲花色冰淇淋
流向黃的白的斑馬線
唱了一段,覺得很難繼續下去,思緒零亂,而且懷疑這些人是否能夠接受這個中文唱出的情歌,他們喜歡嗎?自己實在沒有演唱它的信心。因此在間奏的時候,顯得漫長而不經意。這時不知從哪裡走出一個絡腮鬍的老外,扶著唱臺外圍的半圓桌,大聲問他:Chinese song?(中國歌?)
喬也聞聲抬起頭,他又問了一次,喬也點點頭,那老外隨即翹起大拇指說:Go Ahead(唱啊!)旁邊的人都不知所以的看著他,他卻大搖大擺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喬也受到鼓勵,情緒漸高昂。Mikko 端著酒杯向前走來,細挑的身影,牛仔短褲,寬鬆的運動罩衫。纖纖玉手橫在腰際,嫻靜的面對她。她身上泛發的青春氣息深深感染了他時而低沉時而溫和的心情,這正是他已失去而且缺乏的原始動力。好似她百般了解他情懷的變變,適時的給他激揚的力量。他按在琴上修長的手指不覺百般靈活起來,原先創作這個歌的情緒也明亮鮮麗。他從頭再唱起:
我想我應戴一頂草帽……
那大鬍子旁若無人的大鼓其掌,喬也微點頭。
我又迷信著下午的風
它們像你輕紗長裙的走過來
說要告訴我一個短短的故事
說你就要走了
松山機場有一扇殘酷的門
抑制著自己不能太激動。麥克風傳出的樂音溫軟而動人心弦。他告訴自己要像講一個平凡的故事般的唱出,這兩天小野的影子若隱若現,造成很大的心理威脅。
呵,我是應該戴一頂寬邊的草帽
遮住波音要飛過的天空
我多傷心的臉
傷心的臉
呵,再走一段陸橋也好
我想我只是一個跑江湖的歌手……
街道像一首翻版的老歌
一捲你喜愛的花色冰淇淋
流向黃的白的斑馬線……
歌唱完,他側過頭,Mikko 一手支頭看他,隱約可以感受到她那清澈靈慧眼光的侵襲。回頭注視著黑鍵白鍵,手指漫不在意的彈著一些樂音。習慣上是這樣,沒有找到次一首歌的情緒前,他就在零落的樂音中尋求。忽然他記起昨天寫的一首歌,翻開本子彈了起來。我想我應該戴一頂草帽的街道像一首翻版的老歌一捲花色冰淇淋流向黃的白的斑馬線唱了一段,覺得很難繼續下去,思緒零亂,而且懷疑這些人是否能夠接受這個中文唱出的情歌,他們喜歡嗎?自己實在沒有演唱它的信心。因此在間奏的時候,顯得漫長而不經意。這時不知從哪裡走出一個絡腮鬍的老外,...
推薦序
搖滾、台灣與敘事──重讀〈再見.黃磚路〉
詹偉雄
「青年歲月」、「死亡」、「西洋音樂」,共同出現在1977年發表的小說〈再見.黃磚路〉中,從時間角度而言是偶然,但就歷史向度來看,則是必然──當然,在35年後作這樣的論斷,應是靠了三、兩分的後見之明。
小說主人翁是一位自彈自唱、走闖駐唱餐廳的民謠歌手,他周旋在一群人生不知所從的同輩朋友以及對移民女友的思念之間,過著一種掙扎與焦灼的人生。
像極了台灣在那個年代的主要通俗小說(譬如瓊瑤所寫的《我是一片雲》、《月朦朧鳥朦朧》、《一顆紅豆》),故事中的主角與配角們雖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卻與外在的政治、社會、經濟世界毫無聯繫,他們抽洋菸、說英文、泡咖啡館與酒吧,「真空」似地與世隔絕般地過日子,談(若即若離般的)戀愛以及某種對生活的烏托邦想像,才是他(她)們的核心關切,而與通俗小說稍有不同的是:主角的奮鬥有著一個比較鮮明的救贖目標:成為一位「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的「artist」(而不只是一個「singer」)。
小說敘事進行的緊張點來自兩處:除了主角的理想不斷遭受(社會的)奚落與忽視之外,還來自女主角「美子」(Mikko)的出現,她是一個雙親離異、染上迷幻藥癮、氣味與神情都酷似主角前女友的中日混血兒,這使得主角陷入了另一段迷離的戀曲。故事最終以時間與空間的分離作結:「美子」因毒品受逮準備受刑入獄,主角則搭上南下的火車入伍服役。而在讀者今日看到的小說結尾,則以新聞敘事交待著另一個結局:「美子」被判刑入獄,出獄後的當年(1981)自殺去世,骨灰供奉北投善光寺。
先不論此一實虛並陳的結局,對小說的敘事造成何種戲劇性的影響──「死亡」意味著生命敘事的永恆終止,它總是有「特權」邀請讀者進行一種靜謐、長時間、逆溯的「反思」(當然,它也必定促成了敘事緊張點的消解)──我們更關切的是:〈再見.黃磚路〉在當年台灣社會中,所訴求的一種特殊的「音樂閱讀策略」。在小說中,故事的推演沒有帶來大了悟也沒有大洞察,它所召喚的,反而是川流於整篇小說中的各個西洋音樂文本,化整為零後所建構出的一種「自我追尋」式樣的浪漫情調。
譬如定為小說篇名的〈再見.黃磚路〉(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來自英國樂手Elton John 1973年冠軍唱片的主打歌,「黃磚路」的隱喻來自童話《綠野仙蹤》中女主角Dorothy前往奧茲(OZ)王國的起點,原意代表現代人對美好生活的期望,但整首歌描繪的卻是鄉巴佬對現代社會禁錮自由的反抗,Elton John同志搭檔作詞家Bernie Taupin在副歌中如此寫的一段歌詞:「Back to the howling old owl in the woods(回到森林找夜啼的老貓頭鷹)/ Hunting the horny back toad(捕捉背脊嶙峋的蟾蜍)/ Oh I've finally decided my future lies(我已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 Beyond the yellow brick road(在那黃磚路之外)(翻譯取自網友安德森網頁)」,詩意地描寫出一個叛逆青年的身影。也譬如民謠詩人Don McLean謳歌荷蘭畫家梵谷的〈文森〉(Vincent)、鄉村歌手Cat Stevens(七○年代警廣午夜節目《平安夜》,總以他唱的〈破曉〉(Morning Has Broken)作十二點整點報時曲)同樣描寫破碎現代生活的〈野蠻世界〉(Wild World)、執意虛無反抗調調的門戶合唱團(The Doors)的〈點火吧〉(Light My Fire)……等等──是這些星羅棋布的呢喃音符,隱隱約約地組織了一種莫名的小說主旨。
英國音樂社會學家Simon Frith在他那篇著名的論文〈探索一種流行音樂的美學〉(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opular Music)中指出,音樂有四種常見的社會功能:1.人們透過音樂,來確定認同(identity);我們透過流行歌為自身創造一個特殊的「自我定義」,為自己在社會中創建一個獨特的「位子」,告訴他人「我們是誰」與「我們不是誰」;2. 透過音樂,我們得以將「私密自我」用創意的方式,公開表達出來,譬如「愛情」,如果用言語表達,只能是千篇一律、味同嚼蠟的「我愛你」三個字,但如果透過流行歌,那就有千萬首動人不已的「情歌」來百轉千迴;3.音樂是我們組織「時間感」(sense of time)的最重要媒材,音樂塑造了人們的記憶,因而當一首少年時聽的音樂忽然響起,彼時生活時空中的器物細節往往便接著紛杳而至,這使得音樂成為每個人最重要的文化資本;4. 也是因為有前述三種機制,所以音樂與聆聽者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擁有」(possession)關係,Frith以他親身經驗指出:當你批評一位樂手明星時,他的粉思會以為你在批評他們,因為「樂迷擁有樂手」(「我們的『少女時代』」?),他們已經分不開了。
從Frith的視角來閱讀〈再見.黃磚路〉,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新鮮的收穫:
70年代,是台灣透過「OEM代工」擺脫貧窮,於世界經濟地圖中底定「世界工廠」分工位置的關鍵時刻,其確切指標為1976年台灣外匯收支帳首度由負轉正,台灣一下子從「恐懼」外匯入超的國家,正式成為「自信」的積累外匯存底國家。確定了「出口替代」政策有效之後,台灣社會發展出綿密的「集體化」支援系統(從教育、出口專區、媒體、意識型態、「客廳即工廠」),來協助工廠製造業的效率化。這也意味著,每個人開始被整編進一個生產線般的「大我」系統,而「小我」則應被控管、排除、隔離或壓抑。
面對著這些新鮮的「壓迫」,人們迫切地尋找工具要來捕捉這些「受創經驗」,重新組織自己的認同,並且在社會中「坎」進一個新的位子,隨著外銷貨輪回航的西方搖滾樂(尤其是Bob Dylan、Joan Baez、Don McLean的自彈自唱民謠),便成了當時台灣社會年輕人建構「意義青年」(meaningful youth)自我的論述、技藝與藍圖範本。西洋音樂使台灣青年的自我認同連上Dylan的英美反抗傳統,幫助他們對抗著例行化、乏味的日常生活;音樂也表達出他們內心難以言喻的虛無、挫敗、傷痛;音樂更組織了他們在生命時間流逝中的難受或暢快經驗,使他們過著「有感覺的人生」,最終,音樂使他們共同擁有一些事物,不再覺得孤獨無依;只是,就命題的合理性而言,Dylan的信仰者必定也要揮別Dylan(Frith說,這就是「本真性」(authenticity)在搖滾樂中的重要性:忠於自己的感覺,而非複製他人的感受),〈再見.黃磚路〉的主角一心要作個「中國民歌手」,呼應了這個命題,但讀者們究竟是在他的作品裡獲得感動,還是在小說的各個不同音樂文本中,自顧自地成就自我的浪漫化、英雄化想像?
今日的心理學家指出:「自我」不是什麼本質性的玩意兒,而是一組自己關於自身時間經驗的敘事,由每個人的「過去」、「現在」與「可欲的未來」所組合,個人能過著穩當的生活,端賴他(她)有個穩定的自我(過去-現在-未來之間,被一道你覺得「有意義」的鎖鏈串連著),小說中,民歌手男主角相對穩定的生命狀態,便來自他的「過去-現在-未來」敘事被穩定地延續而且實踐著,但「美子」卻是「脫鏈」的,未來不可嚮往(極權社會)、過去不可回憶(父母離異破裂家庭),只好活在激情的當下,據此,「死亡」似乎也是一個無可逃逸的宿命了。
對於東方社會來說,六、七○年代都是一個「死亡」陰影籠罩的年代,在那個壓迫與叛逆並行的時代轉折中,「自我」敘事的延續變成一種高度困難的志業。日本資深記者川本三郎在半自傳體散文集《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裡,回憶在日本學生運動的高潮中,結識了一位《週刊朝日》封面女郎保倉幸惠,在他與她共處的極少時光中,這位女優意外地成為叛逆記者的他的知音,兩人常一起去看電影,她永遠記得他所忽略的男主角哭泣畫面,「我喜歡敢盡情哭的男人,」她說。1975年,22歲的幸惠清晨五點離開家門,不久,她從天橋上跳下橫須賀線往東京的電車,死亡時年22歲。
在年輕人的死亡中,都有搖滾樂──〈再見.黃磚路〉重印了,也再現了全球化現代性裡──那個異常孤獨的時代。
搖滾、台灣與敘事──重讀〈再見.黃磚路〉
詹偉雄
「青年歲月」、「死亡」、「西洋音樂」,共同出現在1977年發表的小說〈再見.黃磚路〉中,從時間角度而言是偶然,但就歷史向度來看,則是必然──當然,在35年後作這樣的論斷,應是靠了三、兩分的後見之明。
小說主人翁是一位自彈自唱、走闖駐唱餐廳的民謠歌手,他周旋在一群人生不知所從的同輩朋友以及對移民女友的思念之間,過著一種掙扎與焦灼的人生。
像極了台灣在那個年代的主要通俗小說(譬如瓊瑤所寫的《我是一片雲》、《月朦朧鳥朦朧》、《一顆紅豆》),故事中的主角與配角...
作者序
搭上時光機器──「再見,黃磚路」自序
詹錫奎
三十多年後,為了新版的最後校對,又仔細閱讀了「再見,黃磚路」;這一次,竟然情不自禁,幾度熱淚盈眶。
我在一邊閱讀時,一邊從youtube點播書中所提,那個年代令人著迷的歌曲音樂。文字加上音樂,當巧妙的配方完成時,一部不可思議的時光機器就這麼啟動飛翔穿越了。在科幻電影中,我們時常看到從時光隧道回到早年的場景,且能就近觀看年輕時「自己」的一舉一動;但那個「自己」在幻化的五度空間中,並不是百分百的自己,正因如此,你反而更能清楚的意識到那個環境、那些事務。
我就是在這種繁複的情境中,閱讀完「再見,黃磚路」的。這個時候,我已經能充分體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陳映真先生在討論此小說時,所說的「……全篇貫穿著一股青年的孤獨和悲哀,讀後,令我這個已隔一代的人,也有油然的憐惜、心疼之感」,某種不同世代的心靈相互衝擊。在二、三十年前,我總是刻意和自己的作品,保持一定的距離,避免直接涉入去充分談論;因為在我的觀念中,作品本身「自己會說話」,當作者盡力保持沉默時,旁人在評論或詮釋中,反而較有空間去想像與發揮。
但是三十年後,當我是乘坐時光機器去探索那個年代時,這樣的忌諱又似乎可以拋開了。重建「再見,黃磚路」的場景──一九七五年夏天的台灣,到底是什麼樣的環境、氛圍?為什麼我們的青年在那個時代,會是如此的寂寞與容易感傷呢?
原來當時台灣和美國是有正式邦交的(一九七九年才斷交),透過這一層關係(駐台美軍為一大特色),被政治力緊緊封閉的台灣社會(報禁、黨禁、思想檢查、人人心中有一個警總……),卻在高處開了一方形氣窗,踮高腳尖的話,可以窺見已然自由奔放、文化多元、進步思潮洶湧、正在和保守自私的人類劣根性拔河的,令人瞠目結舌的美國文化。這樣說也許還是不夠深刻,我換個角度解釋好了──除了大家時常談論的貓王、披頭四、瑪麗蓮夢露,一九六九年人類首次登陸月球!隔不到一個月的一九六九年八月,史上第一場超大型的搖滾音樂祭,在Woodstock舉行(四十萬人參加,嬉皮文化的大舞台)!一九七一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一九七二年美總統尼克森打破冷戰僵局,首度訪中(季辛吉前一年去舖路,這對主張「漢賊不兩立」又很依賴美國的台灣很傷)!一九七五年老蔣去世(小蔣繼任)……。
簡單的說,一邊是炫人耳目的美國文化,等著讓吸水海綿般的台灣青年去吸收,另一邊卻是風雨飄搖的台灣政經處境;人類都已經登陸月球了,同一時間彭明敏等人卻只因發表台灣自救宣言就被捕軟禁(一九七○年逃離台灣),而蔣介石去世時,被政治力塑造的舉國同悲氣氛,則是今日我們所見到北韓的戲碼翻版。因此,一九七○年代的台灣青年,心靈擺盪於極權和自由之間,其痛苦煎熬是可以想見的。他們想要振翅高飛,但現實的地心引力,卻總是把他們拉扯向下。相當多的青年就是選擇逃離這塊土地──我們別忘了,所謂「去去去,去美國」的口號,就是那個年代的特殊寫照;而當時的「去美國」,所意謂的也就是一去不回頭,「能不回來就別回來」,那樣的一個時代背景。
「再見,黃磚路」的主角喬也,試圖去對抗這樣的風潮,孤獨與寂寞就這樣產生了。這一部分我想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談:在中文世界,從來不太重視文學的隱喻(Metaphor)元素,舉例來說,「西遊記」裡面的孫悟空,或是「封神榜」裡面的三太子李哪吒,這兩個角色很明顯是作者在那個極權時代(明朝的恐怖統治,竟讓偉大小說的作者也只好選擇匿名),創造出來「隱喻」對抗威權的重要手法,是兩部小說中的精彩靈魂人物,但這樣的隱喻卻很少被人談論到。「再見,黃磚路」裡面也有隱喻元素:主角喬也和前女友小野的分手,「如同雙胞胎被強迫割離的痛楚」,乃隱喻奔向美國(小野新定居美國)或留下來為這塊土地奉獻的天人交戰;而與此同時,我們一定不要忘了,當時的台灣,正是厲行思想控制的年代,對一個已浸淫西方自由思潮的青年來說,面對那樣的抉擇(與割捨),也實在很殘酷(主角喬也選擇留下來)。
總之,「再見,黃磚路」是在一個激烈衝突的思潮下,屬於青年痛若掙扎下的產物。那個衝擊的程度,或許可以用某個高山瀑布最下方,水流粉身碎骨那樣的能量,來加以形容;當然,我們也可以嘗試這樣感覺一下:田徑健將紀政如果活在一個女性必須被迫纏足的社會,那是什麼樣的情境?我在一九七五年見到很多把詠唱西洋歌曲,當做第二生命的跑場民歌手,但那一年四月五日蔣介石去世,所有餐廳(演唱場所)皆被禁止歌唱,長達兩、三個月。我們就是這樣跌跌撞撞,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我還很清楚記得,那時我們呼吸西方自由思潮空氣的管道,是現代人很難想像的:包括美軍電台(AFNT)、中華路販售翻版唱片的那一排唱片行、晴光市場那些舶來品店(產品設計概念的背後,也可以解讀出西方進步思潮)、洋文書店,以及很重要的,每個月,我一個家中開書攤的同學好友,他固定會捎來一本全新的「花花公子」(PLAYBOY,屬禁書,多數為委託結束度假、入境台灣的美軍所攜帶),書中對於進步思潮的引介,以及名家藝術、文學作品的發表,常令人嘆為觀止(曾看過海明威小說)……。我們是這麼辛苦的在「踮高腳尖」、透過通往自由奔放思潮的「氣窗」在眺望,但樂此不疲(「再見,黃磚路」後來也拍成電影,李烈主演Mikko,但整部電影被電檢處剪得不堪入目,很失敗)。
當然,最重要的隱喻,就是書的主題,以及書名了──「再見,黃磚路」乃來自Elton John的歌名「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而在那個年代,英文歌曲有所隱喻,正是該時代的一大特色。歌曲Yellow Brick Road的典故是出自童話故事「綠野仙蹤」,意指去追尋夢想的奇妙王國,必走之路;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是追尋生命答案的路。我在創作「再見,黃磚路」時,基本上也相當掌握文字的節奏,整篇小說讀起來很近似一首Don McLean的「American Pie」,富有相當的音樂性,因此小野那一部分的故事發展及隱喻,也就只能點到為止;但「American Pie」也有隱喻,Pie應該指的是多重文化的衝擊揉和,這當然也是「再見,黃磚路」所要表現的。此外小說中當然也有其他更重要的隱喻,這就有勞讀者自己去感受與解讀了。
不管如何,我很感謝東村出版提供了這一次機會,讓我搭上了時光機器,回到三十多年前的場景──雖然在那裡我看到了昔日的自己,那個孤獨的身影,在時代的破繭而出及蛻變中,所承受的掙扎與痛苦,因而幾度熱淚盈眶。但我仍然忍不住要為他們鼓掌:所有曾出現在小說中的,那些我曾經碰過的每個生命、每個角色,感謝他們,讓我以及我所處的社會,不但增加了生命的厚度,也增加了生命的縱深。謝謝你們。
搭上時光機器──「再見,黃磚路」自序
詹錫奎
三十多年後,為了新版的最後校對,又仔細閱讀了「再見,黃磚路」;這一次,竟然情不自禁,幾度熱淚盈眶。
我在一邊閱讀時,一邊從youtube點播書中所提,那個年代令人著迷的歌曲音樂。文字加上音樂,當巧妙的配方完成時,一部不可思議的時光機器就這麼啟動飛翔穿越了。在科幻電影中,我們時常看到從時光隧道回到早年的場景,且能就近觀看年輕時「自己」的一舉一動;但那個「自己」在幻化的五度空間中,並不是百分百的自己,正因如此,你反而更能清楚的意識到那個環境、那些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