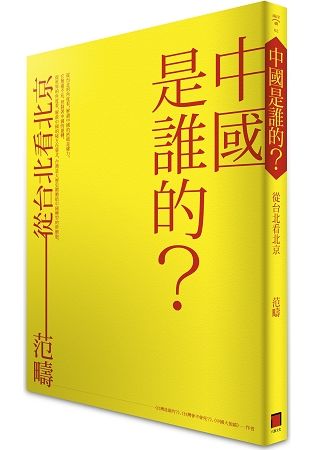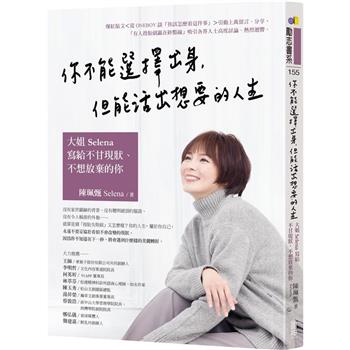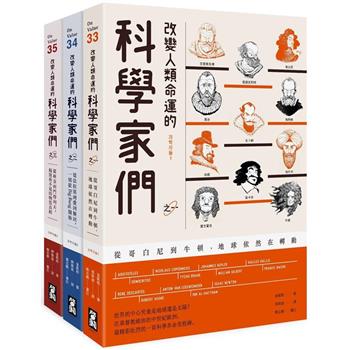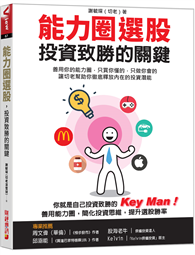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中國是誰的?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10 |
中國史地 |
電子書 |
$ 210 |
社會科學 |
$ 237 |
政治/法律/軍事 |
$ 237 |
政治 |
$ 237 |
社會哲思 |
$ 255 |
社會人文 |
$ 264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從台北看北京,作者看到的不是撤除對台飛彈的假問題、不是亮麗的北上廣等樣本城市、作者也不會概念化的批評中共強權、更不會樂觀的認為對岸市場商機無限。他,透過權力塞車解讀中國政治、藉由權本主義分析中國經濟,從權力控制窺看中國社會。如果中國是一頭大象或巨獸,作者則提供了台灣讀者熟悉或不熟悉的若干切片:揭示出其內在運作的潛規則和權力邏輯。如,從看病吃藥等小事體會到台灣讀者無法想像的權力密碼,從小三和二奶的流行看到中國新世代的進階無門,從五星級酒店的地下停車場的粗陋看到北京背負的沉重權力包袱,從山寨和網路世代思考中國式民主的變形記。顯然,這只能是一個旅居中國幾十年的台灣人才看得到的中國,所以才跳出台灣人常見的獵奇、浮泛的觀察誤區,也不會簡單的把中國議題化。
× × ×
從台北看北京,意味著台北是個絕對的俯視高點嗎?顯然,在國際政治上台北只能仰視北京。然而在世界品牌的比賽場上,台北比北京具有某種顯而易見的優勢。因此,作者不僅僅是從台北看北京,更從世界文明的趨勢看兩岸,揭示出台灣經驗中存在許多權力中國的傳統病灶,尚未洗盡清除,正在阻礙台灣進一步文明化,如官有經濟。他更點出兩岸跳脫出政治正確性的未來可能——主權之外,地球上有一個更大的文明空間,有待兩岸共同定位與開發。中共如果看不見這個空間,其執政將不可延續;台灣如果繼續漠視這個空間,其創造力將消失殆盡。
台灣是中國文明的探路者;是未來中華文化的2.0版;是歷史饋贈給中國轉型的幹細胞。在新的時空背景下,作者建構出全新的中國論述。如果中國將改變世界命運,那麼,台灣可改變中國命運嗎?
作者簡介
范疇
連續創業者,企業及機構顧問。三人行必有我師、自然萬物皆有可觀的信奉者。工作生活於東南亞、北美、台灣、中國大陸數十載,當下遊走於台北京一日生活圈之間。著有《台灣是誰的?你的?我的?他的?世界的?》。 E-mail: 2020bluese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