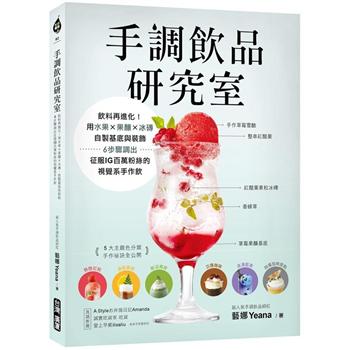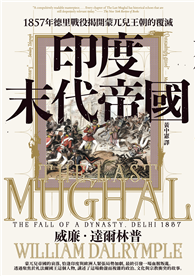代序
有心的人,不發瘋是很難的
今晚,決定不要麻醉自己
作為蛋頭學者,有關於政治制度設計,今天的討論是徹底失敗的,很令人失望。我問到底是駕駛的技術不好、車子有問題、天候不佳、還是路況很差?收到的答案是太抽象。其實,我有一個問題鯁在喉裡沒有說出口:到底你想要去哪裡?
社會科學的基本課題,就是先看問題在哪裡,接著作病理分析,最後才開藥方。哪有先決定要開刀,只不過直覺很危急、必須採取行動,那是急病亂投醫。
我認為,這裡至少有三個場域,包括學者之間的研究跟論述、學者與政治人物的對話、以及政治人物如何說服百姓。都不是簡單工作,必須用相當大的心力。
就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政治學界有相當的鑽研,可惜,國內還停留在初級。再來,如果政治人物不肯傾聽,又如何消化?最後,又如何讓選民覺得有改弦更張的必要?花了一千萬買豪華進口跑車,結果只是當上下班用,沒有必要吧!
包裝、品牌、直銷都很重要,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品質。可惜,沒有幾個人有興趣作信用的。急功、近利,這是台灣人的缺點,「好管不好教」,這是日本人的評價。
表面上說是要給消費者選擇,即使是百貨公司,逛了一圈、買了不少東西,終究,還是浪費。看到型錄甚麼都有,買空賣空、騙來騙去,這就是台灣的民主。
社會的進步,應該是專業分工。學者的責任就是提供生產,不可能要求去作銷售,更不可能要求去動員臨時演員來捧場,又不是作老鼠會的、或吃飽沒事幹。
是的,「學生可以去佔領立法院,為何你們學者沒有能力?」問得好,蛋頭學者,即使鞠躬盡瘁,不知如何回答,也只能這樣接受羞辱了。
良知是不能出賣的
二十年前,我參加的一個團體(台灣教授協會)要我作國會觀察,重點是兩岸條例的過程以及立場稍微納悶。法律的會員很多,為何找上我?不過,既然在美國唸書時,跟指導教授做過國會議員在外交委員投票行為會的研究,所以,也就當仁不讓了。
這個計畫很辛苦,沒有電子檔,沒有網際網路、或是資料庫,因此,是立法院的記錄一本一本地翻,影印回來作內容分析,這是國內極少數作的國會觀察研究。
千辛萬苦,把報告交出去了。年底(1992)剛好是立委選舉,會長(林逢慶)說要把立委的表現跟選民交代,打算開記者會,要我準備。時間、地點都敲定了,在最後一刻卻取消了。到目前,沒有人跟我說明為甚麼,可想而知,是政治不正確,擔心影響選情。
把這份報告整理出一篇論文〈國會議員的政治立場與其立法參與-以兩岸條例為例〉,登在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上的《法政學報》(1994.07,2期,頁145-65),並收在1999年出版的論文集《台灣政治建構》(台北,前衛)的最後一章,雖是沒有能力對抗,也有交代了。
當然,從此被同路人打壓,那是沒有想到的慘烈。
二十年來,台灣的民主政治似乎進步不多。
卑微地苟活著
這一年半來,與其說是肢體的不便,倒不如說是想不透:「難道學者一定要從政,中了狀元一般,才叫出人頭地嗎?」因此,儘管生氣,卻只能頭低低的、卑微地苟活著。
回國以來,由於能力有限,只能忙著運動需要的理念及知識,雖是寂寞,倒也心安理得。當然,我們也知道,有些東西是不讓我們碰的(指國科會、研討會、公聽會),還好,運動圈的朋友看得起,不時會分配沒有人要做的。反正,能溜回台灣已經是謝天謝地,也就沒有必要說什麼先齊身、才能治國平天下;說穿了,就是比較會算,先佔個好位置、寫幾篇有I的國內外論文,升等以後,就可以學而優則仕。
然而,去年,有人強烈質疑,為何你們教授不帶頭衝鐵絲網?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就好像好久以前,有人說,你們為什麼不學學鄭南榕?我想,自己的能力、膽量,就只有這樣了,能做多少算多少。最後,只能自我解嘲說,不好意思啦,天主教徒不能自殺,否則會下地獄,不像佛教徒有地藏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
社會的進步,端賴分工,不像在原始的社會,一個人什麼都要做,既沒有效率、又很難進步,宛如魯賓孫一樣。說真的,我已經很努力「不務正業」了,至少就精神上而言,迄今,已經比很多人多活了一倍以上,所以,自我調侃是米蟲,卻是很認真的米蟲,至少沒有對不起自己的良心。然而,就知識的產業而言,既要我生產沒有人要做的,又要包裝改寫通俗,還要當街叫賣演講,甚至於必須動員,就只差沒有要求直銷給親友。(話又說回來,朋友沒有走避,看到年輕人捨我其誰,很高興)
熱炒一百跟五柳枝
以下是半睡半醒中、會議結束前,被點名發言後的胡言亂語:
一、由於習慣穿短褲,只能穿涼鞋,所以,要給我穿小鞋沒有用。
二、越是想封殺我,越難達到目的。
三、這是一個很廉價的社會(指對於知識而言,特別是政治學)。
報告完畢。
朋友問:「怎麼啦?」
也沒什麼,只是想說熱炒一百跟五柳枝(紅燒魚)的差別:前者多半不過是蔥薑蒜,卻往往比較受歡迎,至少就按讚而言;後者稍微比較麻煩,未必受青睞。
話又說回來,付費打電話去電視節目、甚至於扣應進去,未必代表母體的看法。真正重要的,要看是否有知識性的影響,即使只有一個人看懂,畢竟要看是否有緣人。
正如學生的評鑑本來的用意是好的,卻可能被拿來當作鬥爭的工具,點閱、或是按讚的人數,當然也可以被拿來大做文章。在文化霸權下,我們就是想盡辦法掙脫制約,講好一聽一點,就是看有沒有緣分作交陪。
所以,政治人物儘管可以訕笑,你們辦的研討會沒有人要去、媒體不會報導,有什麼用?你們出的書有誰要看?對於這種勢利眼、投機者的看法,不值一哂,畢竟,我們還有很多同心的人,默默地相互打氣、扶持,為了一個相同的目標在努力,沒有那麼寂寞。
人類大腦的形狀像青蛙
昨天聽到國民黨一名政治人物(當年的國大)說,1997年修憲,民進黨主張法國雙首長制;這種似是而非,現場沒有來賓指正,反正不會有人記得,也不會有人負責。今天,也有學者有類似的說法,應該是選擇性的記憶、或是道聽塗說。
比較正確的說法是,當年的黨主席許信良崇拜戴高樂,而李登輝為了抗拒國民黨保守派的掣肘,拿掉國會的閣揆同意權,未必是真的青睞雙首長制。
然而,此後對這一段歷史,大家有不同的解讀。特別是在2000年,連戰輸掉總統選舉、國民黨仍掌有國會優勢,因此堅持以法國的所謂「自動換軌」,要求陳水扁交出組閣權,那當然是強人所難。連戰如果贏了總統選舉,當然會自行組閣;輸了大選,卻也要求組閣,選來選去都是他在玩,未免欺騙社會。
有回去八德路上電視當砲灰,眾人除了痛罵李登輝,把砲火指向我,彷彿我是民進黨的御用學者。其實,當時代表民進黨去草山談判修憲的是陳文西,而台教會的朋友主張總統制,水火不容,不要把帳算在我身上。下了節目,在電梯中,這位花中畢業的名嘴說,不好意思,他的角色就是這樣。所以,讀到所謂「民進黨策士」,覺得應該具體一點,不該張冠李戴,以免讓人產生全稱式想像。
小時候,父親告誡我們,如果怕忘記,就用一條繩子綁在手指上。可惜,大家的記憶不太好,可能是因為人類大腦的形狀像青蛙(雙關語brain fog與frog brain)。
不要拿鴿子來跟斑鳩交配,不要把張俊雄當作張俊宏
一個學生問我,高中公民老師說,「我們的憲政體制是雙首長制,因為同時有總統、又有行政院長」。我反問:德國跟以色列都有總統跟總理,豈不也是雙首長制?當然不是,他們的憲政體制是如假包換的內閣制。
所謂的雙首長制,就是有一個民選的首長,同時又有一個由國會產生的總理。所以,不管是政客還是媒體,還在舉憲法文本說,我們目前是雙首長制,應該是忘了1997年的修憲,老早已經把國會的閣揆同意權拿掉了。同樣地,如果拿大法官會議釋憲喋喋不休,那是1997年以前的事了。
看到學者接受訪問,舉法國跟芬蘭的作法,要我們依樣畫葫蘆,就有點硬是要拿鴿子來跟斑鳩交配。退一百步,即使台灣目前是雙首長制,光譜上也有三大類,為何一定要依據法國的慣例?
最好笑的是,政客名嘴竟然把挪威(內閣制)當作芬蘭,就好像把張俊雄當作張俊宏。同樣地,青瞑牛不罵死,看到記者寫到,「多數黨組閣在國際上有許多國家的經驗可以參考」,也是道聽塗說:如果是內閣制,那是原本就是這樣的,如果是總統制,就是朝小野大;如果是雙首長制,要看國情。很多東西都可以討論,然而,裝神弄鬼、道貌岸然,好像很有學問的樣子,很討厭。
阿倫•沃茨
英國哲學家阿倫•沃茨(Alan Watts, 1915-73)說:「傻子的立場是所有的社會制度都是遊戲,他看這個世界是在玩遊戲。這也是為什麼當人們煞有介事地在完遊戲之際,傻子只會在一旁傻笑,畢竟,這一切也不過是一場遊戲。」獻給昨晚在凱道原轉教室、以及沒有機會前來的朋友們。
有關政治制度運作的一些錯誤認知
一般而言,影響民主的因素大致上可以歸納為文化、結構、及制度。人民及政治人物的民主文化素養需要時間培養,並非一蹴可及,尤其是彼此是否願意相互傾聽說服的傳統;至於經濟結構(譬如階級)、或是社會結構(譬如族群),也是短期恐難改變,只能企盼舒緩之道、或是不要惡化既有的分歧;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中央政府體制、中央與地方關係)、選舉制度、及政黨體系,彼此環環相扣,卻是相對上比較能立竿見影,關鍵在於變革的動力。
政治改革猶如醫療,必須先有正確的問診,經過合理的病理分析,最後才可能提出有效的藥方。暫且不提修憲vs. 制憲的糾結、或是國家的統獨定位,至少就當下政治運作順暢與否,坊間提出來的病痾主要集中在所謂的「權責不符」,也就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另外,老百姓對於藍綠兩黨長期對立漸感不煩。至於解決之道,議者所開出來的藥方是否能對症下藥、宛如OK繃、或是頭痛醫頭、甚至於頭痛醫腳,還是必須有通盤的理解。
我們打個比方,假設我們一群人想要從台北到墾丁國家公園出遊,感覺上不是那麼順暢,究竟是天候不佳(中國威脅)、路況不順(國民黨黨產)、車子將就(憲法借殼)、公司信譽(政黨輪替)、車型選擇(政治制度)、自排手排(憲政體制)、駕駛技術(國家領導)、司機vs. 導遊(閣揆vs. 總統)、還是乘客素質(文化)或齟齬(社會經濟結構)?
事實上,老爺車只要保養好,通勤應該不是問題;話又說回來,儘管平日勤於保養,忽然拿來上山下海,甚至於想要台灣走透透、全島歡樂遊,遲早要拋錨的。相對地,買新車子還是要看用途,超跑、雙B雖然拉風,在市區未必比銅管仔車好開,至於開家庭房車上下班,光是停車就頭疼,自找麻煩。如果有人只是希望有Ubike可以騎就好,卻是大談是否自排,那是撈過界。
就政治制度設計來看,因果關係最清楚的是選舉制度會影響政黨體系,具體而言,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有利於兩黨制的發展、政黨比例代表制則傾向於多黨制;至於混合制,還要看單一選區與政黨比例席次的相對比率,一般是不希望後者不要超過半數,以免國會過於零碎化、法案不好整合。目前不分區立委34席,佔國會總數113席的三分之一,尚難說小黨沒有生存的空間。
憲政體制也會左右政黨體系的發展,基本上,在總統制(或偏向總統制的雙首長制)下,相對多數有利於兩黨制(譬如美國),絕對多數則有利於兩大陣營(譬如法國)。換句話說,憲政體制會中介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的關係,也就是強化單一選區收斂有效政黨數目、弱化比例代表制的國會零碎化傾向。其實,政治學者的「臨床」實證,發現比例代表制與總統制不太相容,亦即法案整合在相對上比較困難。台灣有三黨不過半、朝小野大、及全面執政的經驗,孰優孰劣?
其實,即使是在內閣制之下,究竟全國性政黨體系是兩黨制(譬如英國)、還是多黨制(譬如荷蘭、以色列、德國)比較好,各有千秋。多黨制並非天生不好,只是萬一碰到政黨相互傾軋,聯合內閣的組成曠日廢時,政府又很可能老是面對不信任案倒閣而必須改選,譬如戰後法國第四共和國,甚至於是醞釀威權主義的溫床,譬如戰前的德國威瑪共和國,殷鑑不遠。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盧比孔河畔的沈思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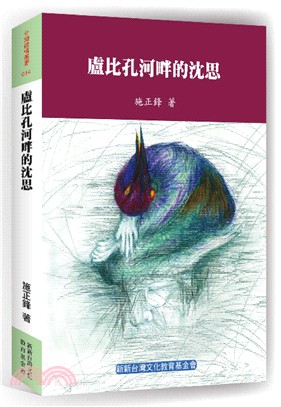 |
盧比孔河畔的沈思 作者:施正鋒 出版社: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翰蘆) 出版日期:2020-04-17 規格:21cm*15cm*2.2cm (高/寬/厚) / 平裝 / 464頁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04 |
社會人文 |
$ 504 |
政治 |
$ 504 |
社會人文 |
$ 532 |
中文書 |
$ 532 |
政治評論 |
$ 532 |
政治 |
$ 560 |
台灣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盧比孔河畔的沈思
本書涵蓋2013年九月政爭、到2020年大選前的政治發展,主題包括九月政爭的政治制度思考、台灣政黨政治的前景、民主轉型的回顧及深化的期待、總統直選與台灣政治發展、九合一選舉的觀察、蔡英文第一任政府的觀察、民進黨的總統初選、國會改革觀察、台灣憲政改造的觀察、以及台獨學者從政百日。基本上,這是當代政治的忠實紀錄,有觀察、有分析、也有針砭、更有建議,換句話說,這不止是照妖鏡,也是作為知識份子的自我期待。問題是,不管是無知、無良、還是無膽,儘管看到病徵、知道病理,掌有權力的人未必願意服藥。經過六年半的沈思,已經沒有其他選擇,求人不如求己,必須直接參與,破釜沈舟、義無反顧,只能當過河卒子了。
作者簡介:
施正鋒
現職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學歷
.Ohio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博士
.Iowa St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碩士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學士
經歷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任
服務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長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總編輯
.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台北市台中一中校友會文教基金會董事
.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喜樂島聯盟副主席兼發言人
專長
比較外交政策、國際政治經濟、族群政治
研究
和平研究、民族主義、政黨政治、選舉制度、經濟發展
推薦序
代序
有心的人,不發瘋是很難的
今晚,決定不要麻醉自己
作為蛋頭學者,有關於政治制度設計,今天的討論是徹底失敗的,很令人失望。我問到底是駕駛的技術不好、車子有問題、天候不佳、還是路況很差?收到的答案是太抽象。其實,我有一個問題鯁在喉裡沒有說出口:到底你想要去哪裡?
社會科學的基本課題,就是先看問題在哪裡,接著作病理分析,最後才開藥方。哪有先決定要開刀,只不過直覺很危急、必須採取行動,那是急病亂投醫。
我認為,這裡至少有三個場域,包括學者之間的研究跟論述、學者與政治人物的對話、以及政治人物如何說服...
有心的人,不發瘋是很難的
今晚,決定不要麻醉自己
作為蛋頭學者,有關於政治制度設計,今天的討論是徹底失敗的,很令人失望。我問到底是駕駛的技術不好、車子有問題、天候不佳、還是路況很差?收到的答案是太抽象。其實,我有一個問題鯁在喉裡沒有說出口:到底你想要去哪裡?
社會科學的基本課題,就是先看問題在哪裡,接著作病理分析,最後才開藥方。哪有先決定要開刀,只不過直覺很危急、必須採取行動,那是急病亂投醫。
我認為,這裡至少有三個場域,包括學者之間的研究跟論述、學者與政治人物的對話、以及政治人物如何說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代序-有心的人,不發瘋是很難的
今晚,決定不要麻醉自己
良知是不能出賣的
卑微地苟活著
熱炒一百跟五柳枝
人類大腦的形狀像青蛙
不要拿鴿子來跟斑鳩交配,不要把張俊雄當作張俊宏
阿倫•沃茨
有關政治制度運作的一些錯誤認知
九月政爭的政治制度思考-不要當赤腳醫生,不管是學者、媒體、還是國會觀察者
壹、行政協定的審查
貳、憲法中的政黨:私人俱樂部、還是公共個體?
參、國會議長的定位:不偏不倚、還是沒有政黨立場?
肆、結語
台灣政黨政治的前景
壹、台灣的政黨板塊是否凍結了
貳、當前政黨體系發展的觀察...
今晚,決定不要麻醉自己
良知是不能出賣的
卑微地苟活著
熱炒一百跟五柳枝
人類大腦的形狀像青蛙
不要拿鴿子來跟斑鳩交配,不要把張俊雄當作張俊宏
阿倫•沃茨
有關政治制度運作的一些錯誤認知
九月政爭的政治制度思考-不要當赤腳醫生,不管是學者、媒體、還是國會觀察者
壹、行政協定的審查
貳、憲法中的政黨:私人俱樂部、還是公共個體?
參、國會議長的定位:不偏不倚、還是沒有政黨立場?
肆、結語
台灣政黨政治的前景
壹、台灣的政黨板塊是否凍結了
貳、當前政黨體系發展的觀察...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