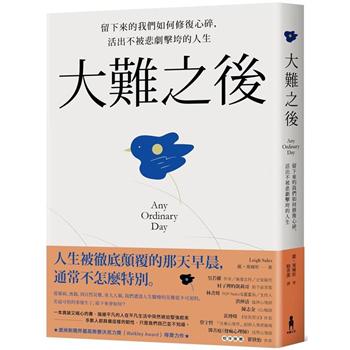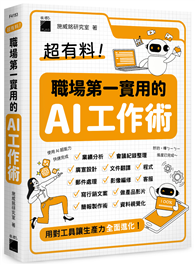前言
有點裝,但很真實,歡迎來到唐納薇的世界
一
在我不甚正常的和寫字有關的歲月裡,總試圖用小說的格式來思辨,用公式的套路去講音樂,又或者,用詩歌的方法來談原理,用定量的企圖去描述感覺。總之,總想很努力地把理性和感性糅合到一起,不管是否有吃力不討好之嫌。
倘若被問之,為何總是熱衷於此等混搭,唔,那的確是一個有點長的故事。
從頭開始講吧,大約在十年前,我所待的聚合物實驗室,每天都要煮一鍋以甲基丙烯酸甲酯為主料、各種烯酸酯為輔料的乳液。所謂乳液,是因為在那個透明的玻璃反應容器內盛滿了水,而微小的油性有機分子以水包油形式存在。當它們逐漸以鏈接的方式形成為高聚合度的大分子之後,整個瓶子,就會透出微藍的柔美的乳光來。
每天下午,坐在實驗台對面的書桌上,透過層疊的儀器,面前擺著一本記錄本,不時地探頭看幾眼反應器,每間隔一段時間就要起身,用一支滴管從中取出約0.5ml的樣液,滴在表面皿上,稱量,用最快的速度烘乾,繼續稱量,然後大致估算出一個叫做聚合度的數值來。
而在那等待乳光到來的漫長卻又碎片式的時間段裡,我花了大量的力氣去思考這樣一些問題: 到底,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我是誰?我會成為誰?我將去追尋什麼?
終於有一天,我決定放棄那抹微藍。
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有些疼痛的成長階段。說疼痛是因為許多變化發生得實在太快了——放棄科研轉而靠寫樂評和文字報道為生。那期間,許多場景恍如一夢:有一陣子我的工作就是晚十點之後打車出門,來到一家喧囂的夜店,觀察台上的DJ如何打碟,構想著怎麼用文字把這一切記錄下來。也許這樣的生活值得很多年後去細細品味……
如果說,通過這些事,我終於把自己歸結為一個以「寫字」為重要屬性之一的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智人種個體,但在「寫字」兩個字前,仍顯得十分空曠,我不認為對感覺對表象的描述就是自己的終點,雖然它感動了我,卻並沒有抓住我。就好像當年做的某種聚合物端基還在等著去設計……那麼,該用什麼詞彙去填補呢?
我在等。
轉機或說契機的出現,是在慎重選擇了一家科學媒體之後,我開始涉及「科學寫作」,名正言順成為了一個「科學工作者」。生命於某個階段都會出現一種回歸,如此選擇,也許最適合作為逃兵一枚卻又怎麼也放不下那不可捉摸的理性邏輯美的自己。雖說世間萬象並不是非此即彼,但我願意選擇從脈絡和機理的層面去看清,而不僅僅停留於感覺。
二
從2009年夏天開始,受前同事項斯微姑娘之邀,每隔一周在《上海壹周》上更新「科學家閨蜜」的專欄。最初,我被限定不可以寫問答,不可以太學術,不可以沒有科學含量,最最要緊的,不可以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大概思忖了一晚,我構想了專欄的基本風格。其實也很簡單——這些年看過不下百本亦舒小說,各種橋段的講述、運用了然在心,何不嘗試虛構一名主體人物,輔佐三五配角來講故事,而在故事的間隙插進科學現象進行分析呢?
「唐納薇」因此而誕生,沒錯,她是個人物,具有如下屬性: 出生於中國一二線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姿色中等偏上,IQ有個130吧,月薪不低於2萬。這是一個有著我和身邊許多同類人影子的設定,她堅強得有點裝,但又絕對真實。
為了塑造唐納薇和她的朋友們,我把聽來的各個故事揉碎、拼接、雜化、移植……隔周的星期二晚上就要抱著筆記本在被窩裡憋出一篇,不得不說這是個快樂的創作過程,也不得不感謝項斯微近兩年來的威逼利誘,否則這些文字不可能從無到有。這本書中寫到的許多情事、人事,或案例,都有著某種程度的非虛構性,書中的特別之處在於,會被植入若干用來分析原因的道理——它們或是一些來自進化生物學或生理學的理論假說,或是一些博弈論或決策研究的議題。
毫無疑問,以上做法沒有遵循在正式科學寫作中的一套標準,並不足夠嚴格,有「預設」或「附就」的嫌疑。而非常清晰的一點是: 讓唐納薇代言我,更多是為了表達一種「我們是這樣來思考問題」的態度,而非堅定地要告訴人們什麼大道理。即便是一個從業多年的研究者,也不會聲稱人類的愛、性、情感、關係「就是那個樣子了」。每個針對具體問題的探討,給出的僅僅只能作為階段性結論,是有條件和邊界的——無論如何,絕對化的表述在科學嚴謹的世界裡絕對不會受到認可。我也力求在描述中呈現確切出處、樣本大小、相關數據等基本的實驗方法,也許看起來稍嫌繁複,使得行文趣味性下降,但卻必須如此。
三
還是回過來說愛。
愛,的的確確,可以有多浮泛就可以有多深刻,可以有多狹隘就可以有多寬廣,可以有多現實就可以有多飄渺。年輕一些的人們,對這個字的感受多來自於那些美麗的文字、影視。而當漸漸不年輕,對這個字就無法再做過多旖旎、不合實際的想像。
比如,關於「來電」,科學會告訴你,這其實是一種性喚起,如果用儀器測量的話,在狂熱狀態中人的某部分腦區活動變得特別頻繁,從身體上來說,不過是因為去甲腎上腺素的大量湧出而造成了興奮和心跳加快。關於永恆的愛,科學會告訴你,那種隨著生物體的消亡才消亡的愛是個例,因為愛是對人身體的消耗,如果一直很瘋狂地愛人,必須具備很強的體質,迸髮式的巔峰狀態只出現在很短暫的瞬間,基本上所有人都無法勝任這種事物,「永恆」只存在於傳說裡。
唐納薇,擔負著使命而出現,一邊觀察一邊講述,理據無非都是諸如上述那些。她做著看似聰明卻不討好的事,很辛苦地釐清著作為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一個女人渴望知道的那些道理,而那些辛苦,說白了,皆因本星球有著另一種叫做「男人」的生物。
我在六十多個篇目裡,寫的每個故事,均來自於這種對立而生的疑惑。寫了它們的我和身在其中的每個角色一樣,不曾穿越過這個困境,卻也因為講述帶來的釋懷而能夠自在嬉笑。
讓.波德裡亞隨筆集《冷記憶》裡面寫過一段非常有趣的描述,會被我在不同的場合下反覆提起,因為無論用它來表達困境或提出解決方法都可說太絕妙。原文大致是說,男女相悅在雙方的理解上難以調和: 對於男人而言,他希望直入主題、省卻那個過程;而對女人而言,她希望那個過程無限長、被反覆玩味。那麼化解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 女人在去往男人房間的途中,從踏上第一層樓梯就開始脫衣服,一路脫,於是她佔有了那個過程,當男人打開房門時,看到的是一個赤身裸體的對象,於是他直抵了那個結果。
在能力範圍內,我無法提出比波德裡亞更無懈可擊的設定,但卻會據此想到著名動物學家、人類行為學家德斯蒙德‧莫裡斯的一個說法,他在暢銷書《親密行為》中把兩性交往設定為12個階段: 眼對身階段、眼對眼階段、話對話階段、手對手階段、臂搭肩階段、臂挽腰階段、嘴對嘴階段、手對頭階段、手對身階段、嘴對乳房階段、手對生殖器階段、生殖器對生殖器階段。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兩性經歷那些中間環節,為的是到達最後的階段。其中的某個具體環節,可以很長也可能很短,一些情況下甚至可能停留在某個階段就無法深入了。
不知道人們會不會和我一樣,覺得這當中有一種美妙的對應,這種對應甚至掩蓋了我們進入真實的一番掙扎後所必然直面的破碎和美感的消弭。
四
你相信倘若有一天,科學足夠發展,人類可以預測或者控制愛情嗎?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場合下被問到過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是的,我相信」。提問者不約而同地追問一句:「你不覺得那很無趣嗎?」我也會繼續回答:「不會,要相信我們到時候已經發展出了反預測和反控制技術。」
唐納薇和她的女朋友們
唐納薇31歲,本書主角,名牌大學生物學碩士,門戶網站高管,好理性談風月,閒時會在所謂時尚雜誌的犄角旮旯裡展示其思想的火花。
M33歲,海歸經濟學博士,工作於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是四人中最tough的一位,女人中的邏輯辯論極品,宴會上常見其分析全球政經形勢。
莫扉28歲,藝術專業出身,先後在廣告行業、公關行業和媒體行業混跡,現為一名獨立作家,最愛標榜自由,實則以此為名交結各國男友。
戴安29歲,語言學專業出身,明星經紀人,前女文青特質在摸爬滾打中屢屢遭受重創,且於現實激流中保留著傳統保守的內在。
她們的故事,或許你也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