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命運可以是這樣,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結局……
★攻佔《紐約時報》排行榜,橫掃西班牙書市,蟬聯三年暢銷No.1
★全球銷售突破2,500,000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極力推崇的文學新高峰
★烽火迷情如《亂世佳人》、秘密諜報媲美《色戒》、異國剪影更勝《北非諜影》
在烽火離亂、愛情財富地位都朝不保夕的二戰前夕,
她唯一能對抗時間淹沒人生的方式,就是不斷地縫下去……
即使不能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也要證明自己曾真實地活過。
一個把針線作為武器的女子,一段熱烈、激情、戰慄且神秘的地中海傳奇──
天真爛漫的少女希拉,在結婚前夕,和未婚夫走向一家打字機專賣店,推開門,她的命運瞬間徹底改變。
1936年,西班牙烽火連天,希拉帶著裁縫師和秘密情報員的雙重身份,遊走三個國家、五個城市,潛入黑幫走私,投身桃色交易……這一路上,她失去珍愛她的、不得不放棄她所愛的,甚至無數次被自己的選擇背叛。隨著故事一頁頁展開,整個地中海都成為她的舞台,而政治、諜戰、陰謀、冒險竟也與她難分難解……
暗伏在時代的軌跡下,以小說織出歷史的真面目──
《時間裁縫師》整個故事橫跨十餘年,作者對西班牙、摩洛哥整個地中海沿岸深刻且細膩的描繪,讓人彷彿親臨直布羅陀海峽兩岸截然不同的年代時景──西班牙在內戰的炮火下滿目瘡痍,摩洛哥卻豐富迷人,充滿激情、炙熱和肉慾蠢蠢欲動的異國風情;而二十世紀初那段狂躁的歐洲歷史,更隱身在希拉的腳印之下,形成本書暗伏的重要準軸。希拉以高級服裝師偽裝下的秘密情報員身份,揭露西班牙將軍佛朗哥、二戰同盟國和軸心國等所有時代暗潮下高潮起伏、虛實相交的秘事。許多情景皆來自史料記載,書中角色則好似歷史上沒有被記錄下來的人物,雖然被淹沒於記載中,卻在小說裡和真實人物一起參與重大歷史事件,帶給我們栩栩如生的感覺──明知是虛構的,卻彷彿真的發生過。讓人不僅為書中角色動情,也被那些歷史人物所感動;而作者從歷史的細節捕捉靈感,也使這部小說成為不朽的時間檔案。
透過作者和書中角色的一針一線、一步一印,彷彿填補了戰爭殘缺的面貌,彰顯那個年代女性在亂世下的掙扎、犧牲與努力,就像在隱約告訴我們:生命中有這麼多缺口,正是我們縫補發揮的最好時機;就如希拉,用每一次的決心,即使是一個錯判,去車過這些裂縫,也終能車出一生漫天烽火下的絕世美景。
作者簡介
瑪麗亞.杜埃尼亞斯 Maria Duenas
1964年出生,英語語言學博士,曾在北美大學執教,現任穆爾西亞大學教授,目前居住在西班牙卡塔赫納。《時間裁縫師》是她的第一部小說,在沒有任何行銷宣傳的情況下,這部新人處女作憑著小說自身的魅力,受到讀者熱情追捧,僅在西班牙的銷量就超過250萬冊,並已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全球發行。
譯者簡介
羅秀
本名黃曄華,北大西語系畢業,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現任人民網西文版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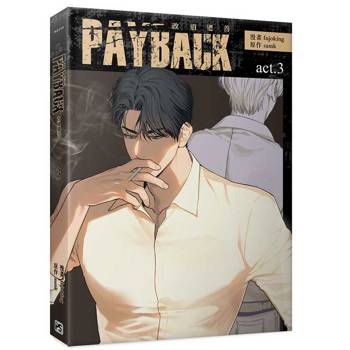


故事描述窮苦單親家庭出身的女孩的一生,有身世之謎(其生父是西班牙巨富)、有年少不顧一切的初戀、有失去一切砍掉重來憑藉勇氣與裁縫技術重生、有異鄉異國的風情和浪跡天涯的風情(主角的故事遍及馬德里到北非、葡萄牙.....)、驚險刺激的生涯(如與游擊隊周旋以及後來成為英國情報員和納粹份子鬥智.....) 只是如果想要就純粹娛樂的目的來讀,本書故事的起承轉合太過於「平」,主角每次轉換身份或切換場景,鋪陳起來相當硬。第二、整本書的故事沒有中心意識思想,這類接近大河歷史著作的大部頭小說到底是想要呈現什麼東西?是女人奮鬥出頭天?還是西班牙與殖民地之間的悲歡離合?還是二戰中西班牙的微妙角色?還是對極權法西斯的控訴?....本書並沒有強烈且明顯的思想主軸。 最後長達將近兩百頁的情報員篇幅更是全書的敗筆,故事鋪陳的幼稚與不合理不合邏輯的程度簡直直逼張愛玲的《色戒》,為什麼我說本書與《色戒》都是荒謬的芭樂諜報小說呢?因為他們都沒有對情報或間諜工作作過深入研究,只憑文學家的想像和筆觸就去虛構一個自以為是現實場景,破綻百出且太過於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