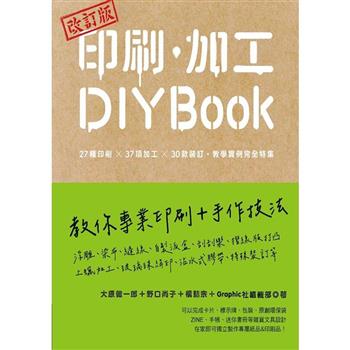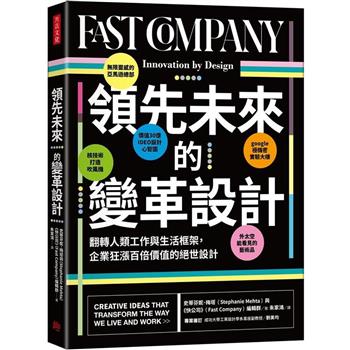圖書名稱:八尺門
「人們為了生存而不懈奮鬥,不是為鏡頭與筆墨而生活。」
在《八尺門報告》發表同時期,為了維護和保障自己的權益,台灣原住民掀起了一波波自覺性的社會運動,並於1984年成立了「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爭取原住民的自主地位。這個以原住民知識青年為中監分子的「原權會」,不僅提倡「部落主義」,並跨越族群、城鄉,爭取原住民的身分地位、自我認同、國家族群與文化政策等訴求。
然而將近三十年過去了,原住民社會運動發展至今,成果有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成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憲法增修條款、原住民電視台成立等,以及各原住民族正名、身分、母語、就業、經濟立法保障等,但原住民在台灣社會的極端弱勢與困境真的有獲得改善?關曉榮決定重回八尺門,希望透過紀錄在時間容顏裡所顯示的意義,看見都會原住民的變遷與困境,讓社會大眾正視、關注都會原住民生存及生活空間等議題,進而從原住民政策、土地、經濟、社會、文化與教育等根本的社會構造,去思索並尋求解決問題之有效途徑。本書收錄大量攝影圖像以及當時作者紀錄文字,包括一九九六和二○一一年重返八尺門之心得與後記。
作者簡介
關曉榮
報導攝影與文學工作者,致力於當代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與現實的社會調查報告。關曉榮曾在1984年赴基隆八尺門記錄當地阿美族島內移工的生活,後寫成〈2%的希望與掙扎〉於1985年人間雜誌創刊號發表,並在美國文化中心開辦攝影展。之後於1987~1988年赴蘭嶼進行達悟族社會調查報告工作,並於《人間雜誌》分篇發表〈蘭嶼報告〉,頗獲攝影界重視。曾任《天下》專職攝影、《時報雜誌》採訪記者、自立報系專題採訪記者、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記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教授(2012退休),著有《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1987》、《八尺門手札》、《女兒的胞衣》等書,以及《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國境邊陲:1997島嶼上的人類》等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