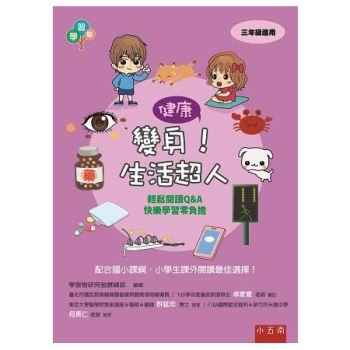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上海已經下了半個多月的雨,我的心情卻是充滿陽光,因為這本書終於要出版啦。
文革,是什麼?
是不是一種皮革(皮草)啦?
知青,又是什麼?
應該是一種蘋果,就像蛇果、青蘋、嘎啦、紅富士一樣……
這不是說笑,真的有人這樣以為啦。
其實,不要說臺灣的讀者,就連大陸的讀者,對那個特殊年代的事情,或渾然不知,或一知半解,或漸漸淡忘。在政府刻意的淡化下,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終將塵封。就像重慶沙坪壩的那座紅衛兵墓園,早已成為一段歷史,那些被埋葬的死難者,他們的親人都漸漸老去,來祭奠的人來越少,再過若干年,這裡終將成為一片荒墳野塚。
可我還是想把這個故事寫下來,哪怕多位出版界的友人明確告訴我,這本書在大陸很難出版,只因題材受限制。這就意味著,能讀到它的人少而又少。
沒關係,哪怕只有一百名讀者,不,哪怕只有十名讀者,我也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把這個發生在並不遙遠的四十多年前的、充斥了荒誕與黑色幽默但又血淚交織的故事寫下來。
先講個笑話,輕鬆一下。
二〇〇八年,我參加作家協會組織的一次踏青活動,記得是去陽澄湖吃大閘蟹,在旅遊巴士上,聽到一則笑話,說當年有一個知青,想吃肉,日思夜想,口水咽下去又湧上來,真的快想瘋了。其實別人也想,每天晚上饑腸轆轆地躺下去,眼睛一閉,身體就飄乎乎地來到一張餐桌前,桌上擺著紅燒肉、黃豆豬腳湯、大蔥炒豬肝、茄子大腸煲,還有一碗堆得像金字塔一樣高的雪白大米飯,就在夢裡抄起筷子,開動啦!
別人只是意淫,可這位老兄,真的付諸行動了。
他從生產隊的豬圈裡偷走一頭豬,獨自完成從趕豬、屠宰、切割、醃製到藏匿的一系列高難動作,然後獨享口福。在那個食物匱乏的年代,他簡直成了紫禁城裡的皇上,周圍一群性無能的太監,而他獨擁三千嬪妃,嗨翻了。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我忽然意識到,這個素材不錯哎。
我有個表兄,當年也是知青,在上海崇明島的農場插隊落戶。他告訴我一件真事,在他們農場裡,有一個警察,遭受政治迫害,被迫脫下警服,下放到這裡。農場領導慧眼識珠,將其“廢物利用”,派他去抓賊。農場人多手雜,經常發生財物失竊,由此他獲得了一點小小的特權,日子過得比那些知青要滋潤,有沒有肉吃我不曉得,但肯定不會餓肚子。
從這兩個素材開始,我開始了漫長的構思。
十月懷胎?拜託,我都有十年了好吧!只要有空暇,我就構思這個故事,我的大腦就是子宮,慢慢來孕育它。二〇一八年瓜熟蒂落,開始撰寫第一章,當時腦子裡還是“有一頭豬不翼而飛……”,可寫著寫著卻愈發懷疑這個笑話的真實性——知青多是群居,要完成這樣一個任務,難度實在太大,他必須有獨居的環境,類似養蜂人楊家業,還要有屠夫的手藝……所以權衡下來,我把一整頭豬改成一顆豬頭。
文革結束後,崇明島那個農場裡那個不穿警服的警察,被“平反”,恢復原職,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單位——公安局,還領到了補發的數年薪水,類似於現在的“國家賠償”。
不得不說,他是幸運的,更多像姚傳經那樣的人,把生命留在了農場裡,埋在那片土地下,再也沒能回到自己的故土。這樣的人,不是數以百計、千計,而是多達數十萬,如果加上死於文革中的那些冤魂,就是數以百萬計。
謹以此書獻給這些人,想對他們說,即使你們已經被國家、被這個時代所遺忘,但我沒有忘。期待有一天,我們能像以色列猶太人對納粹大屠殺那樣,建立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紀念館,把這段歷史詳盡地寫進學校的教材,人們可以公開講、大聲講、哭著講、笑著講……我堅信這樣一天終會到來。
在這裡特別鳴謝友人阿聯、Ada和明智周,他們為我牽線搭橋、付梓出版。然跟那些暢銷書比起來,這只是一本很小眾的懸疑小說,但我已心滿意足。後面如有機會,還想寫一個姚茶生的探案故事,當然不再是文革年代啦。
清明過後,就是春光明媚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一九七四戴手銬的警察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4 |
中文書 |
$ 332 |
推理/驚悚小說 |
$ 332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70 |
小說 |
$ 37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一九七四戴手銬的警察
茅捷大幅增補改寫,2021年重磅推出完整版24萬字血淚鉅作。
讓讀者聲歷其境,體驗無奈歷史經驗之際,依稀看見人性光明與未來之希望。
民國63年,貴州,一個貧瘠的國營茶場,接連發生了幾樁荒唐事:食堂失竊了一顆豬頭;一個犯人被派去破案,只因為他當過警察……這個倒楣的警察,既要找豬頭,又要找配槍,還要偵查兇手,萬萬沒想到,自己竟淪為殺人嫌犯⋯⋯
作者簡介:
著(作)者簡介
茅捷。上海人,祖父開有錢莊,民國41年永隆錢莊成為公私合營銀行,相當於被人民銀行兼併,全家淪為赤貧。民國37年12月5日,祖父茅潤泉搭乘中央航空公司從寧波飛上海,因天氣惡劣,在江灣美軍臨時機場迫降未果,機身斷裂,大多數乘客震盪昏迷,生還者寥寥。文革中,家人因當年說過一句“美軍地勤大兵積極救人,國人卻趁機劫掠乘客財物”,遭受猛烈批判⋯⋯凡此種種,讓作者對民國年的老上海及文革題材,心心念念,情有獨鍾。曾出版《來自陰間的51號油畫》、《無頭鬼子兵》、《穿黃雨衣的死神》、《外灘裡十八號》、《招財貓和流浪貓》等小說。作者郵箱maojie25@hotmail.com,歡迎讀者多多指正。
矢板明夫(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時事評論家)誠摯推薦:
翻閱本書,是你了解現代中國,掌握中國人思考的第一步。
作者序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上海已經下了半個多月的雨,我的心情卻是充滿陽光,因為這本書終於要出版啦。
文革,是什麼?
是不是一種皮革(皮草)啦?
知青,又是什麼?
應該是一種蘋果,就像蛇果、青蘋、嘎啦、紅富士一樣……
這不是說笑,真的有人這樣以為啦。
其實,不要說臺灣的讀者,就連大陸的讀者,對那個特殊年代的事情,或渾然不知,或一知半解,或漸漸淡忘。在政府刻意的淡化下,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終將塵封。就像重慶沙坪壩的那座紅衛兵墓園,早已成為一段歷史,那些被埋葬的死難者,他們的親人都漸漸老去,來祭...
文革,是什麼?
是不是一種皮革(皮草)啦?
知青,又是什麼?
應該是一種蘋果,就像蛇果、青蘋、嘎啦、紅富士一樣……
這不是說笑,真的有人這樣以為啦。
其實,不要說臺灣的讀者,就連大陸的讀者,對那個特殊年代的事情,或渾然不知,或一知半解,或漸漸淡忘。在政府刻意的淡化下,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終將塵封。就像重慶沙坪壩的那座紅衛兵墓園,早已成為一段歷史,那些被埋葬的死難者,他們的親人都漸漸老去,來祭...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楔子 3
第一章:豬頭 11
第二章:手槍 63
第三章:象鼻神 99
第四章:面具 139
第五章:五六式步槍 193
第六章:三件寶貝 249
第七章:熟客 307
第八章:上吊 349
第九章:雞蛋 395
第十章:白色物體 439
《 後記 》 459
第一章:豬頭 11
第二章:手槍 63
第三章:象鼻神 99
第四章:面具 139
第五章:五六式步槍 193
第六章:三件寶貝 249
第七章:熟客 307
第八章:上吊 349
第九章:雞蛋 395
第十章:白色物體 439
《 後記 》 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