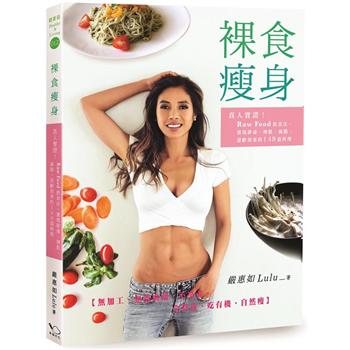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鎮痛的圖書 |
 |
鎮痛 作者:宋尚緯 出版社:啟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3-0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87 |
小說/文學 |
電子書 |
$ 190 |
詩 |
$ 30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42 |
中文書 |
$ 342 |
文學作品 |
$ 342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詩人宋尚緯敏銳地捕捉到生活中每個傷痛的片段,輕輕拾起檢視再大口吞落疼痛,用時間緩慢地將抽象的痛感修煉成詩句,集結成一本關於悲傷與沉默的圖鑑,點燃一盞又一盞的燈火,照亮自身的缺口,同時照亮他人的傷心,所以自癒,所以癒人。
《鎮痛》以99首詩作表現疾病、苦厄與療癒的人生課題,從自身自心,及於社會家國,層層推進,各篇作品既獨立、又聯結,相互呼應,展示作者處於當代台灣的苦悶、憂思、抵抗與反省。在結構上,首章以序詩之『如是我聞』起,終於末章末篇的『夢幻泡影』,隱喻作者對人生與家國亂象的沉痛指涉,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有機形式,儼然史詩之宏偉架構。而其語言,能善用日常之語,巧構詩意的語言世界,既能承載並彰顯『震痛』(疾病與療癒)的書寫主旨,又能以極具內在音樂性的節奏,傳達作者面對內心與外在世界的傷痛情境。
——向陽對楊牧詩獎得獎作品《鎮痛》的評語;詩人於出版前有再剔除、挑選詩作,最後詩集由61首詩組成
作者簡介
宋尚緯
一九八九年生,東華大學華文文學所創作組碩士,創世紀詩社同仁,著有詩集《輪迴手札》、《共生》及《鎮痛》。作品入選2014臺灣詩選、2013年度臺灣詩選、2011中國詩歌年鑑、乾坤詩刊15週年詩選。
得獎紀錄:
《鎮痛》第二屆楊牧詩獎
中興湖文學獎首獎
全國學生文學獎
〈日光旅行〉:2010全國巡迴文藝營創作獎新詩佳作
〈輪迴手札〉:2009年文創副刊年度最佳作品獎
〈我們這些毫無關聯的細節〉:98年度好詩大家寫收錄
〈找房間〉:大學校園文學詩獎作品巡迴詩展暨第二屆國民詩展
〈駱駝〉:第四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新詩優勝
〈日夜的界線與瀕臨死亡的城〉:X19全球華文詩獎
我常常將詩當作禱詞來寫,將看見的所有哀傷都一一刻在裡面,希望一切都會朝著更好的方向前進,但也常因此感受到自己的無能為力,於是一切都只能成為令自己也令他人沉默的句子。我在每一首詩中都輕輕地攤平自己,用力地將自己劃開,再仔細地將自己湊齊,也希望每一首詩都能給予和我有類似經驗的人一點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