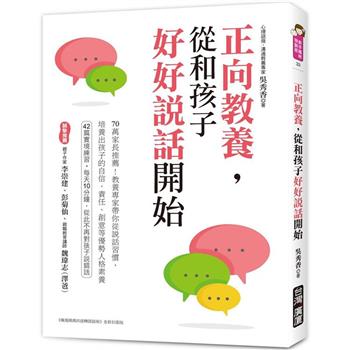私繪畫
譚軍
我一直覺得畫畫是件很私人、私密的事情,甚至連對繪畫的思考過程也是很私人的。我可不喜歡有人在一旁看著我畫畫。在那樣情況下我畫畫只能是遊戲,或者繪畫知識的展示,與我自己的繪畫是沒有關系的。我的畫只想反映我自己的生存狀態,我看什麽聽什麽關注什麽思考什麽,這些直接反映在我的畫裏。我執著于把自己對自我、個體、人、人和這個世界的關系等這些問題的感受與思考真誠、真實地呈現出來。實際上,我,我的生活,決定了我的繪畫,決定了我繪畫的私人化。正像其他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創作一樣。如果每個人都能真誠地展現著自己,那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非要對這種個人化生存和創作的人進行歸納、定義出某個具體的概念,對于作爲創作者的我來說是很沒有必要的。
當然,我也不會把“私人化”、“個人化”當作什麽了不起的標准來衡量繪畫,畢竟“個人”只是一個很中性,甚至是有些可疑的狀況。“人人都是藝術家”就像宗教裏說“人人都能成佛”一樣,只是一種可能性,並不是現實的狀況,既然不可能實現,我覺得也就不必在意了。呈現個人,真實、真誠地呈現個人,在此也就變得可疑了,鬼知道呈現出來的會是什麽。可能是真的個人,也可能只是個人的局部或者願意呈現的部分,還可能只是假象,甚至是策略和謊言,但不管怎麽呈現總是會倒映出那個幕後者。就像俗話裏說的“畫如其人”、“相由心生”之類的“谶語”。這讓我常常陷入到一種矛盾的境地中,不願意面對或感受別人的作品,因爲我只會坦誠以對,難免會被別人的作品惡心了自己。但我同時又不得不去面對以便了解這個世界,而且也很想去面對別人的作品來感受那些作品裏可能存在的美好的東西。我面對“人”時也是同樣矛盾的景況,既渴望從別人那感受到身爲人的美好,又害怕被那些“人”特有的汙穢惡心了自己。根據我對“人”的了解“惡心了自己”的可能性遠遠大過從他人身上感受到的美好。我也因此變得少語和遠離人群。
爲了防止被自己惡心到,我不得不對自己格外警惕和苛刻。曾有一位長者在與我短暫的相識後給了我一個“潔癖”的歸納。我知道這當然不是指我對清潔衛生程度上的苛求,而是指我藝術完美的追求和對自己的約束自律。在他看來幾乎成了“潔癖”還是讓我有些吃驚的。或許這種自我約束和自律,正是我在對“人”的思考和認識後的下意識行爲,我不想變成我自己討厭的那類人,自己惡心到自己、自己厭惡自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要做到不被自己惡心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俗了說,簡直是逆水行舟,尤其是在接受多年順流而下和順水推舟的教育後。沒有所謂的頓悟,我是在經曆了艱難緩慢的自覺後才意識到自己的目標在水流的反方向,能否“自救”得了,就全憑個人的意志力和真的知識了。
雖說人是個時間的概念,人總活在自己的年齡裏,但我每回想到自己在力比多旺盛的歲月裏傻逼閃閃地混日子還是想找個緣由來歸咎一下。畢竟接受了十幾年的教育後一個渾身冒著傻氣的自己出爐了,這實在有點讓人難以接受,也太對不起爹娘了。因爲所受的教育,我的成長不但來得太遲,而且夾雜了太多錯誤和謊言,等我意識到自己的路和方向時,差不多三十年已經過去了,按作家石康的理解,某些美國人已經用這三十年做完了中國人一百年才可能做完的事情。我常聽到或看到有一種說法,說任何經曆都是財富,我是不是可以假裝自己已經是個闊佬了,接著活下去就是了,百年之後自然財富等身。
不,我才不要這樣的結果。
Better late than never.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游離:譚軍作品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游離:譚軍作品
書籍重點
無力是藝術家在這個世界上的有力。
藝術就是用來向這個世界示弱、示敏感的。
當代中國青年水墨畫家-譚軍,第一本個人作品集。
精美冊頁型畫冊設計,收錄30餘幅動人作品。
譚軍的作品,像是帶我們穿越奇異的時間,像是走在星空裡,或是緩緩路過古怪的人與動物。
人說,古代的中國被留在了日本,但譚軍又像是從日本這塊文化的縱合體中,切出一片片景觀,
它們帶著一些殘酷、一些冷漠,既是日本物語繪卷的當代段片,也是中國水墨的新「私繪畫」。
作者簡介:
譚 軍,當代水墨藝術家,1973年生於湖南湘潭,2005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獲碩士學位。現居北京。
2008年於上海美術館舉辦大型個展「異語者」,並曾於北京今日美術館,以及香港、北京等地畫廊舉辦聯展。本書《游離 譚軍作品》為2013年4月譚軍於北京亦安畫廊舉辦同名個展之畫冊。
章節試閱
私繪畫
譚軍
我一直覺得畫畫是件很私人、私密的事情,甚至連對繪畫的思考過程也是很私人的。我可不喜歡有人在一旁看著我畫畫。在那樣情況下我畫畫只能是遊戲,或者繪畫知識的展示,與我自己的繪畫是沒有關系的。我的畫只想反映我自己的生存狀態,我看什麽聽什麽關注什麽思考什麽,這些直接反映在我的畫裏。我執著于把自己對自我、個體、人、人和這個世界的關系等這些問題的感受與思考真誠、真實地呈現出來。實際上,我,我的生活,決定了我的繪畫,決定了我繪畫的私人化。正像其他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創作一樣。如果每個人都能真誠地展現著...
譚軍
我一直覺得畫畫是件很私人、私密的事情,甚至連對繪畫的思考過程也是很私人的。我可不喜歡有人在一旁看著我畫畫。在那樣情況下我畫畫只能是遊戲,或者繪畫知識的展示,與我自己的繪畫是沒有關系的。我的畫只想反映我自己的生存狀態,我看什麽聽什麽關注什麽思考什麽,這些直接反映在我的畫裏。我執著于把自己對自我、個體、人、人和這個世界的關系等這些問題的感受與思考真誠、真實地呈現出來。實際上,我,我的生活,決定了我的繪畫,決定了我繪畫的私人化。正像其他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創作一樣。如果每個人都能真誠地展現著...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譚軍
- 出版社: 亦安工作室 出版日期:2013-05-10 ISBN/ISSN:978986885734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0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美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