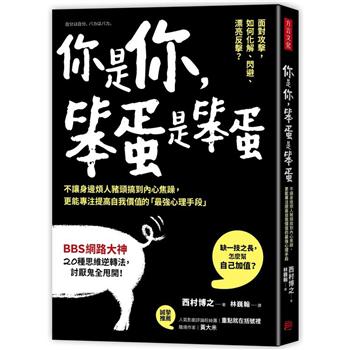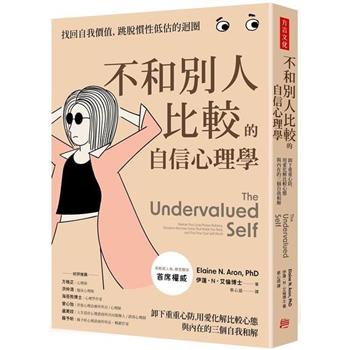媒體推薦:
《血色童話》的作者倫德維斯特被譽為瑞典的史蒂芬.金,以不負眾望的妙筆勾勒出兩個可怕的少女合力報復這個世界。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精彩絕倫……絕對會成為恐怖經典之作,約翰.傑維德.倫德維斯特也藉此奠定不容小覷的文壇地位。
──MTV.com
史蒂芬.金和倫德維斯特筆下的人物色彩鮮明,令人難忘,第一時間就擄獲讀者的目光……倫德維斯特的作品驚嚇指數破表,劇情難以預料,峰迴百折,如同生命本身。就算只是洩漏一點點劇情,你都會覺得自己破壞了作者精心安排的詭異甜蜜時刻。
──BloodyDisgusting.com
倫德維斯特大膽躍進,一連串的突破創新造就出這本令人驚豔,不按牌理出牌的巨著……起碼堪稱為妄為激進之作。結尾虛無殘酷,卻又富饒詭異的詩意。
──《書單》雜誌(Booklist)
劇情或許驚悚,還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但書中對於天生vs.教養的反思,以及對於音樂、心理疾病與電視選秀節目之現象的探討犀利無比,銳利如碎玻璃的鋒緣,足以劃開你的肌膚。作者倫德維斯特不落俗套,以誇張的手法來勾勒這群多愁善感的少女,教人不知該同情她們或者該懼怕她們……閱讀此書時,開燈為宜,並請遠離黑髮女孩。
──《坎納瑞碼頭報》(The Wharf)
嶄露頭角的精彩作品。
──《城市生活》雜誌(Time Out)
相較於多數同儕,倫德維斯特的作品更發人深省,也更驚世駭俗。
──《現代科幻》雜誌(Sci-Fi Now)
精彩絕倫。血腥驚悚。讓人愛不釋手。人物刻畫精心,劇情懸疑曲折,引人入勝,讀來不禁沉浸其中。將專演恐怖戲的巴黎大木偶劇場的場景與音樂產業相結合,來譏諷後者……完美佳作。
──科幻驚悚類的影視專刊《SFX》
作者倫德維斯特筆耕不輟,創作出一部部犀利精心的恐怖大作……全書瀰漫著驚悚氛圍,但又帶著脫俗出塵卻詭異的感覺……讓人讚歎激賞。作者對於少女心態的描繪不落俗套,栩栩如生,以慧黠筆觸不著痕跡地點出校園霸凌與社會霸凌的關係……藉由書中人物的疏離感,具體歷歷傳達出恐怖感,而啟示錄式的結尾更讓他躋身為傑出恐怖小說家之列。
──愛爾蘭《週日獨立報》(Independent on Sunday)
一開始是尋常的驚悚小說,但隨即成了驚世駭俗之作,這位瑞典作家再次證明他是北歐的史蒂芬.金。事實上,他的成就已超越了史蒂芬.金。
──《每日鏡報》(Daily Mirror)
倫德維斯特這本作品具有黑色幽默的肌理,尤其是他集中火力,勾勒流行文化產業的剝削本質……《小星星》層次分明,發人深省。
──《捷運地鐵報》(Metro)
《小星星》的劇情在一場音樂會上達到最高潮。這種安排跟史蒂芬.金的《魔女嘉莉》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對於女孩變成狼的背景刻畫同樣入微,而且結局都帶有天啟的意味……倫德維斯特精準地傳達出他要的效果。
──《坎培拉時報》(Canberra Times)
經常被拿來跟史蒂芬.金相提並論的倫德維斯特在《小星星》中同樣描繪了一個瘋狂社會,並精心刻畫出這個社會的心理層面,提供犀利的警世預言……倫德維斯特以瑞典流行音樂圈為背景,劇情在血液噴濺的音樂會達到高潮,以全新的角度來重新詮釋女孩的力量。
──《澳洲人》(The Australian)
《小星星》是一部怪異卻讓人著迷的小說:血腥、偶帶趣味,意有所指地嘲諷音樂產業、電視和社交媒體。
──《聆聽者》(Listener)
揉合了希臘神話伊底帕斯、十九世紀身世成謎的德國神祕人物賈斯伯.荷西(Kasper Hauser)、創造出科學怪人的法蘭肯斯坦博士(Dr. Frankenstein),以及阿巴樂團等元素,交織出力道十足的冰冷敘述,訴說出一個殘酷但美麗的生物,如何在扉頁之間踉蹌展開她的故事。
──《墨爾本評論》(Melbourne Review)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為什麼恐怖故事中常出現孩童?
我想,原因有很多,最簡單的理由:如果你想嚇人,想營造毛骨悚然的氣氛,那麼,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讀者或觀眾能感同身受被驚嚇者的感覺,所謂的被驚嚇者,就是遇上可怕怪物或生物的主角。如果被驚嚇者是成人演員,我很難對其所扮演的角色產生共鳴,因為他們有特定的說話方式和服裝,這些都會妨礙我感同身受。不管我多想當布萊德.彼特,終究不會是他。另一方面,是因為螢幕或文本裡的孩子通常命運多舛,加上成人比較容易進入孩子的心裡。以孩童為主角,讓我更能跟自己的童年連結在一起。所以,對我來說這麼做比較容易,我也喜歡這麼做。
此外,還有其他顯而易見的理由。孩童會讓人想照顧、保護,照理說他們不該經歷可怕的事物,所以,若他們面臨可怖情境,就會讓人難以忍受,畢竟,在恐怖故事的世界中還是有些禁忌。然而,這幾年來,凌虐式的色情片扭曲了這些禁忌,比如巴斯卡.勞吉哈(Pascal Laugier)所導演的《極限:殘殺煉獄》(Martyrs)之類的電影。這種電影結合了孩童與凌虐兩個元素,在我看來總覺得太超過。感謝老天爺,我真的不認為這種作法可行。
不過,這種事情真的會讓人產生共鳴。沒有什麼比孩童更能讓人感同身受。媒體在報導十七、八歲的青少年問題時,採取的態度完全迥異於報導失蹤兒或孩童被殺害的事件。身處惡劣環境的脆弱孩童會讓人更加不安,即使那個孩子是加害者,這點最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就我的記憶所及,最恐怖的電影場景是二○○四年查克.史奈德(Zack Snyder)重拍的《活人生吃》(Dawn of the Dead)的開場。一開始,有個少女變成殭屍,晚上疾步走入父母的臥房,撲向父親,撕開他的喉嚨。這女孩穿著睡袍,以孩童的移動姿態走向父母房間,看似要尋求雙親的安慰,這種人人眼熟的場景忽然「啪」地迸裂,你赫然發現她不再是你原本以為的那個女孩,而且她的行為產生驚人的變化。這種場景真是嚇人。
這種場景為什麼會讓觀眾產生那麼強烈的情緒震撼?為什麼這種畫面能讓人感同身受?
孩童!原因再明顯不過。孩子需要被保護,被照顧,以免受傷害。如果你有孩子,身為成人的你最主要的職責就是照顧保護他們。
另外,我認為很多恐怖電影或恐怖小說家會深入挖掘自己童年時的黑暗洞穴,以找出最原始的恐懼。這種恐懼難以名之。大人會以理性來分析各種思緒,比如原因是這個,這個會嚇到我,這個不會,但對孩子來說,在黑暗處的某種東西或者床底下的怪聲音可能是任何東西。如果我想構思出什麼可怕的情節或駭人的影像,我就必須回到童年經驗,找到適當的辭彙來描述那種恐懼。我想,很多創作或處理恐怖故事的人都會把這種情緒和恐懼運用在他們的作品上。
理由眾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孩子的心智狀態很特別。五到七歲的孩子很容易把一件成人看起來是垃圾的東西視為全世界最珍貴的寶物。當我們是孩童,會隨心所欲決定各種事物的定義。你會認為這東西好珍貴,或者認為花園那角落好可怕。然而長大成人後,你就不會這麼想,所以,從孩童的觀點來敘述會有可信度,會讓作者創作出來的世界顯得很真實。如果有人嘴裡冒出血,大人會想,「噢,他們一定是在拍電影」,或者那人嘴巴受傷。但孩子會想,「吸血鬼,他是吸血鬼!」一旦他們這麼想,吸血鬼就變成他們認定的現實。正由於他們比成人更願意接受各種現實,所以,恐怖故事才會把孩童當成一扇門,藉由他們通往另一個現實世界。
依您之見,身處險境的孩童比身處險境的大人更能引發觀眾或讀者的情緒反應,原因是什麼?
許多恐怖電影的主要缺點就是讓我無法認同男性主角。有陣子流行一種恐怖電影,裡頭的主角都穿著T恤被殭屍追殺。那些殭屍會撿起花園裡的各種東西,以你所能想像的各種方式殺人,後來這個男主角成了英雄,拯救所有人,但我就是不喜歡這樣的角色。在我看來,他的演技爛透了,壓根兒無法說服我,頂多只能在《飛越比佛利》之類的影集裡當配角,怎麼可能當男主角。我真希望怪物快點把他殺死,這樣一來那個台詞還挺有趣的小書呆子才有機會露臉,面對面槓上拿著鐵鍬的怪物……可惜他就是不死。說真的,這種角色會讓成人很難認同,特別是我原本就對這類角色很有意見,你知道的,就是那種我不喜歡或者難以認同的角色。但孩子不一樣,孩子很難不讓人認同,即使這個孩子的角色是邪惡或可怕,你還是會認同他/她,尤其若他/她的四周全是大人。
你經常將孩子當成劇情驅動力,不管是以何種方式,甚至將他們當成主角,比如在你的作品《港灣》(暫定書名,中文版2013年上市)中,主角安德斯之所以沉淪為人類,正是因為孩童,但他之所以能起而抗敵,也是因為孩子……
我之所以借助孩童來說故事,是因為他們在我的故事類型中能發揮很大效益。孩童對於現實或非現實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但成人有,除了《暮光之城》或《噬血真愛》裡的成人,多數大人都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我喜歡的人是吸血鬼,但我仍然愛他。也不能接受某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事物也是真實的。孩童不會認為某種現象是疾病造成的,或者某人演出來的,或者化妝的效果,他們願意接受另類的世界狀態。所以,在《港灣》這部作品中,沒有什麼比孩童更具有強烈的劇情驅動力。為什麼?對我來說,我要寫的故事必須讓我能在寫的時候覺得很難過。在《港灣》中,我想不出有什麼比失去孩子的劇情更極端。對另一個成人的愛,比如丈夫對妻子的愛,通常得加以說明解釋。這種愛我可以想像,但得花很大的篇幅去描述,才能讓讀者接受這種愛巨大強烈到丈夫會使出極端手段來拯救這段愛。然而孩童不一樣,多數人可以體會這種愛,也能理解這種愛會讓人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保護,就連要鑽入地底也在所不惜。
我總覺得你的書中有很多你的影子。
不會吧……真的嗎?
比如你作品中的單口喜劇表演者、魔術師和魔術,在學校被霸凌的孩子……至少,我個人想把這些角色詮釋成你的化身。《斯德哥爾摩復活人》裡有個角色就是單口喜劇表演者,你在書中寫道,他很擔心表演無法讓觀眾發笑。另外,在《血色童話》中,主角奧斯卡躲在地下室,驚恐地聽著其他男孩逐漸接近……我個人覺得,這些片段比怪物或騰空亂飛的物體更恐怖。這種恐怖是日常生活會遇上的經驗。你是不是透過寫書來驅逐自己的恐懼?
嗯,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這麼做:利用我的恐懼來說故事。或者,可以說我利用它們做為故事的驅動力。我的恐懼多半來自於害怕失去所愛,但我不認為我想解決或揮除這種恐懼。話說回來,我認為我滿快樂的,或許可說是個非常快樂的人,所以,照理說,我的腦海應該不會出現我坐下來寫作時浮現心頭的恐怖影像。然而,當我一坐下,那些影像就自動出現,這點讓我很驚訝,也很驚嚇。有時,我會想,這次我要寫的應該是輕鬆愜意的東西,應該不會有問題……可是複雜的心理糾葛開始啟動後,劇情就愈來愈黑暗。我目前正在創作的故事很黑暗,很兇險,為什麼會寫成這樣,我自己也搞不懂。我想,當我坐下來寫作,原本讓我知足常樂的東西反而會變黑暗,我的心思會變得很漆黑。至於是否試圖解決我自己的恐懼,我不這麼認為,我不覺得我有很多問題待解決。當然,我的故事應用了不少我個人的背景、工作經歷、以及自己本身。比方說我對肉品店或工廠一竅不通,但我清楚單口喜劇表演者和魔術師這兩行是怎麼一回事。我也懂得照顧幼兒,因為我曾在托兒所工作過兩年──這是我唯一做過的「正常」工作,另外我也當過老師。除了這些經歷,其他行業的事情我得去研究才能略知一、二,偏偏我不喜歡這麼做。
身處險境、面臨威脅的孩童能引發我們的同情,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不該受到傷害,但如果角色相反,孩童變成威脅……從很多方面來看,這比一般的殺人兇手或怪物更可怕。是什麼讓你有這種感覺?
我想,在電影和小說中,把孩童當成威脅來源會比將他們當成認同對象更讓人倍感威脅,因為照理說孩童不會危害他人,而且他們應該象徵善良和友善。就連迪士尼裡的人偶也被改裝成寶寶形狀,好讓他們顯得更加無害。所以,當孩童變成威脅,拿起工具,展開攻擊……我在寫的就是這樣的事情……情況會非常嚇人,因為這種事情跨越了某種界限。理論上來說,若描述兔子或松鼠攻擊人類,應該會很恐怖,因為照理說牠們是無害的小動物,但事實上我們不覺得恐怖,反而覺得愚蠢,好像在看搞笑的演出。這種表現法很具突破性,幾乎可說是一種仿謔劇。想像一隻小兔子拿著很小、很小的電鋸跳來跳去,簡直是導演提姆.波頓風格的畫面嘛(笑)。總之,以小動物來表現就是行不通,但主角若換成孩童,感覺就很對,因為這種畫面仍然可被理解,你可以輕易地想像一個孩子忽然變臉,變得很邪惡……
可是將孩童當成邪惡實體也很棘手,因為在這樣的故事中,有很多價值觀得詮釋出來……
是啊,不過重點是,你寧願把這些價值觀應用在孩童身上,而不願意應用在成人身上。邪惡這個概念很有問題,比方說,你若追溯某個囚犯的過往背景,回溯發生在他身上的一連串事件,你很可能會說其實誰都沒有罪。一個嬰孩漸漸長大成人,經歷過很多事,有一天他走進銀行,以手裡的短管獵槍或者現在盛行的某種自動武器射殺了兩個人……一個人清白無罪經常是很多事件所造成,背後也有很多原因。從社會的角度而言,我們必須劃定界限,制定規則,非得如此不可……不曉得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我自己都不確定我問了問題……(兩人哈哈笑)不過,現在倒有個問題要請教你,具威脅性的孩童會引發什麼樣的情緒?
我想,這涉及兩種矛盾的事實──一方面孩子需要被保護,但另一方面他不可愛,不善良,而是具威脅性──這兩個事實結合在一起會很嚇人,因為我們覺得自己必須保護這孩子,不讓邪惡力量侵犯他,否則他就會變得很可怕。有很多電影描述孩童被邪靈或惡魔附身,做出可怕的事情,比如《天魔》(The Omen)之類的。喔,不過在《天魔》中,那個男孩是撒旦的兒子,所以或許不能相提並論,不過還有很多其他例子可以用來說明這種狀況。這種孩童角色所引發的情緒涉及兩個事實:孩童需要被保護,否則惡魔就會入侵他們,讓他們變得邪惡。這類型的故事跟描述戴曲棍球面罩的變態殺手的電影相比,帶有更強烈的罪惡感。你不會對一個成人的變態殺手說,「不,你不是真的邪惡,我們要讓你改邪歸正……」你不會對《十三號星期五》裡的殺人魔傑森說這種話,但我們認為,在孩童的行為變得難以接受之前,我們有機會讓他改邪歸正,所以電影裡的邪惡孩子有很多機會重回人性的溫暖懷抱。
我覺得大家似乎更能包容行徑邪惡的孩童……
你可以看看那個十歲時殺死四歲幼童,十一歲時又殺死另一名三歲幼童的英國女孩瑪麗.貝爾(Mary Bell),或者幾年前殺死三歲的詹姆士.柏格(James Bulger)的兩個小男孩。這兩起事件引發眾怒和恐慌,輿論要法院判這兩個男孩死刑,或者無期徒刑,即使這兩個男孩分別才九歲和十歲。因為這種事情天理不容,孩童不該做出這麼可怕的事情,我們的家人和我們的孩子不可能做出這種事。我們壓根兒不會想到我們的孩子會做出這麼可怕的事,所以,我們必須懲罰或者殺掉那些孩子,因為我們做出了我們無法想像的事。孩童不可能這麼邪惡。
以孩童為主角似乎是一股複雜的潮流。我想到了《血色童話》裡的依萊,他確實殺了人,但身為讀者,我覺得他的殺人行徑也還算好……
依我之見,只要讀到了愛情故事,只要劇情裡有愛情,不管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呈現,大家就會很希望他們能有情人終成眷屬,無論付出多少代價。你知道的,就像依萊──他排除所有阻礙,殺光他們所有人……而奧斯卡──拿了刀,做了某些事……這兩人就是要在一起,但你得安排一些距離和阻礙,這樣一來讀者才會更喜歡他們。
對,我就是這個意思,不過你運用這概念的方式很不同。《斯德哥爾摩復活人》也一樣,在這本書裡,小男孩伊利亞思死後復活,通常我對這種死而復活的生物持負面看法,但我對伊利亞思抱持同情,還能感受到他受的苦。
對,我也沒把他描繪成邪惡的殭屍。
沒有,你絕對沒這麼做,雖然殭屍通常很邪惡,就像吸血鬼是怪物,是一種詭異的存在體。
喔,我要強調的就是這一點,而且這也是我的初衷。我想改變既有觀念。如果你停下來想一想,就會覺得這怎麼可能?殭屍幹麼想吃人腦?我真想不通……你知道嗎?他們在籌拍《斯德哥爾摩復活人》的電影時,有多難搞定這個殭屍孩子的角色。我們來來回回討論了好多次。(《斯德哥爾摩復活人》的改編電影預計2013年在瑞典上映。)
以孩童為主角或反派,你認為這兩種角色,哪一種讓你寫起來比較雀躍?
我通常會把這兩種角色結合在一起,一方面把孩子當成主角,由他/她來推動整個劇情的發展,但同時又讓他/她是個得小心提防的角色。尤其是我正在撰寫的這個故事《小星星》。這本書處理了很多我們聊到的問題,書裡的孩童確實做出了非常駭人的事。
你在描述一個孩子做出可怕的壞事時,有什麼樣的思考過程?感覺起來描寫孩子做可怕的壞事比做好事來得更困難。
我不這麼認為,因為我喜歡以孩子的角度來解釋他們的行為,也因此喜歡這類情節所用到的語言和說話模式。我覺得描寫孩子比描述大人更有趣,因為在描繪成人的行為時,得搬出一堆理性說明,但孩子的行為通常出於某種想像,解釋起來簡單多了。如果是成人,作者就得去應付其他作家的意見和主角的痛苦,而孩童做某些事的理由則顯而易見,而且呈現出來的效果也跟成人不同。比方說,我記得小時候會忽然不喜歡玉米片之類的,於是我就把這種經驗放入小說裡。不過,真要比較的話,老實說,我喜歡把孩童當成正派主角的寫作過程,因為寫起來比較有趣。對我來說,描述邪惡孩子的可怕行徑並不愉快,因為我描述人物時通常會進入這些角色的腦袋裡。
之前我們談到孩子會認為某些地方很危險,比如花園的某個角落很可怕,另外,還提到孩童和成人會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事物。我想,大家都能體會那種老覺得地下室的樓梯底下有什麼可怕東西的固執念頭。我發現你的小說裡有很多這類的主題和元素,所以讀者都能從中體會書中人物的感受。
就是這樣!所以,以孩童當主角才會這麼有效果,因為八、九歲的孩子對世界的規則懵懵懂懂。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下水道有怪物嗎?我的床底下會不會塞了什麼東西?是不是有一些門通往神祕的地方?會不會有些看起來很正常的人類其實是機器人偽裝的?這些都有可能發生。就像小時候,會覺得某些懸崖看起來好深,或者某個水坑大到必須游泳才過得了,但長大之後,那個深不可測的懸崖一眼就能看到底,那個大水坑半步就跨得過去。在孩子的世界裡,故事才能說得精彩。我寫作時喜歡讓自己置身在那樣的世界和意識中。
我沒打算問你會不會怕「GB人」。(GB人是某家冰淇淋公司的小丑圖案,這圖案曾短暫出現在倫德維斯特的小說《港灣》中。)
我不怕,所以你就省省,別問了吧。GB人可說陪著我兒子長大。不過,就像《港灣》裡描述的,他原本怕的是其他東西,但我拿GB人當例子,「這就像害怕GB人……」結果說著說著,他真的怕起GB人來了。
你知道嗎?我們剛剛聊的這些,其實都出現在電影《科學怪人》(1931)裡一幕很精彩的場景。在這幕中,科學怪人跟一個小女孩坐在靜謐的湖畔,小女孩把花丟入湖水裡,科學怪人在一旁看著,覺得小女孩好美,於是也把她扔進河裡。現在說起那一幕,或許覺得好笑,但其實非常精彩,也很可怕,蘊含很多意義。事實上,科學怪人是很脆弱的生物,但另一方面,他絲毫不察他的行為所造成的後果,他只是學習小女孩的舉動。這個例子很棒,足以用來說明事情可能錯得多離譜。光從這一幕裡的許多細節,我就能寫出一篇恐怖故事。
三○年代末期這齣影片在電視上播放時,他們把這一幕拿掉了。據說飾演科學怪人的波里士.嘉洛夫(Boris Karloff)也設法讓這一幕消失在電影裡,因為他認為這幕太可怕。
是啊,對他們來說,那情景確實難以忍受,不過幾年後重映時,這一幕又被放回去。不管怎樣,這兩部電影都很讓人讚歎。
不過,就像你說的,科學怪人害死小女孩的那一小幕就足以道盡我們對於善惡的討論。這可怕的事之所以發生,並非因為他很邪惡。就像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史坦貝克(Steinbeck)的小說《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裡那個智障的藍尼,活活把一隻小老鼠捏死。他不明白,不懂自己做了錯事,因為他只是想對老鼠表示親暱,不料他對老鼠的愛卻勒死了牠。
對,如出一轍。
說到純真的物體變得具威脅性,比如GB人,你認為孩童、小丑、洋娃娃、遊戲場和音樂盒等東西具有什麼樣的象徵意義?
還有皮卡丘的遊戲卡!
對,這些東西是很有效的工具,可以操控我們,為什麼會這樣?
這麼說吧,因為它們代表孩童,它們就像孩童,因此照理說它們會讓人聯想到毛茸茸和可愛的東西。如果你讓這樣的東西變得具威脅性,或者用這種東西來殺人,就會讓人毛骨悚然。把它們運用在恐怖脈絡中,破壞它們的純真屬性,會更讓人不寒而慄。恐怖故事經常使用這些元素,雖然取材各異。想想那些老舊的嬰兒車,我是說有天篷可以摺起來蓋住的那種。總之,它們讓人很不安。嬰兒車裡可以發生很多不對勁的事。
確實如此,以我自己來說,我就發現孩童是很有效的敘述工具,若是把他們放在螢幕外,就更具效果。在螢幕以外的脈絡中,我們無法具體看見他們,但我們的想像力會讓畫面變得比螢幕影像或文字敘述更嚇人。真的很有效。
我在寫作時,會利用影響我最深的事物,也就是我最喜愛的東西,即使在我的故事中,我不會支解它或破壞它。對瑞典的讀者來說,卡通巴姆斯熊(Bamse)最能引起讀者共鳴,所以我在《港灣》中就利用了它。你知道那種想大喊「哇」的感覺嗎?比如巴姆斯熊,以及你還小時,巴姆斯熊所衍生的相關產品,比如巴姆斯娃娃、巴姆斯漫畫等會讓你產生的聯想和感受,這種共鳴的情緒是你長大之後任何東西都無法提供的。我想,對我來說,孩童的物品具有強烈的情緒共鳴,所以我把它們用在我的小說裡。這些事物存在我的心裡,而且具正面意義。或者,如果你好好描述Saltkråkan(六○年代瑞典著名的家庭戲劇,場景發生在列島上),那麼多數瑞典人就會立刻想到小時候很喜歡的溫馨電視畫面,所以,若把這齣影集放入恐怖脈絡,其所製造的威脅感就會更強,而這種心理層面的威脅會傷害到我們無憂無慮的童年回憶。在恐怖故事裡加入這些照理說很安全的事物,比如巴姆斯熊和影集Saltkråkan,會威脅到我們的內在小孩和純真無邪的一面。
確實很有效果。我想到閱讀《血色童話》時,我發現裡頭有很多流行文化的事物,它們能標示出故事所屬的年代,也能傳達出該時代的氛圍。有幾次我坐在房間閱讀時,彷彿回到了年少時光,那些電視影集、收音機傳出來的流行音樂,以及服裝等時光膠囊,具體歷歷地出現在我眼前。
是啊,當我在《血色童話》裡描寫到Kiss樂團時,也有這種懷念美好往昔的感覺,真有趣。
不過,其他書好像沒把這樂團當成時光膠囊。起碼沒像《血色童話》這麼詳細描述他們……
這點我不贊同,我想,從某方面來看,他們還是存在於書裡的。對我來說,提到這些事物並非有意識的決定,而是自然而然這麼做。我想,很多作家都有這種經驗。在描寫某個時代時,你的意識會起作用,你的腦海會開始浮現關於那個時代的一切。氣味、顏色和味道。紙盒包裝的奶油是什麼模樣,放在手裡是什麼感覺。回想這些事物時,我會有一種帶有罪惡感的愉快心情,照理說,這種心情會讓恐怖故事沒那麼具說服力,不過當我事後閱讀《血色童話》的有聲書時,竟發現這本書比我以為得更恐怖,另外,還發現我在裡頭用了太多彼時的流行文化。我想,從某方面來說,我坐下來寫作時是身不由己,被那些感覺和印象帶著走。
是啊,我發現就是這些流行文化的事物讓這本書顯得很獨特,我想,很多人也會有這種感覺。這些事物都是許久之前的時代記錄,是逝去的純真歲月。稍早前你提到巴斯卡.勞吉哈所導演的《極限:殘殺煉獄》。你看過這部影片嗎?
看過!
你覺得如何?
我認為……這麼說吧,有次別人這麼問我時,我回答,「這電影很棒,但不要去看!」我是在倫敦的恐怖影展裡看到這部片,當時《血色童話》也應邀上映。這部影片在情緒氛圍上很像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的作品,但我看過之後久久不能自已。我很希望自己沒看過這部影片,因為它太令人不安,太擾亂我的情緒。奧地利導演麥克.漢內基(Haneke)的《大劊人心》(Funny Games)(1997年上映,2007年時,漢內基再拍攝美國版)也很讓人不安,它們會駐足在你的腦海中,跟著你離開戲院,讓你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它們。我不喜歡這部電影,不過我承認它拍得很成功。依個人之見,我不曉得它是不是好電影,但我想它應該是。拍得好極了,讓我無法將它逐出我的腦袋,所以這一定代表某種意義。
對,幾個星期前我也看過這部影片,看完後它也一直流連在我的腦海中,拍得很成功,而且很駭人……
很折磨人!問題出在這導演太過有天分,他太厲害,拍出這麼棒的電影,非常棒的一部。
他功力超強,能這麼深入黑暗、痛苦、折磨和焦慮的情緒,讓悲觀的結局化成快樂結局,女主角最後終於達到殉道者的狀態,移居到另一個更好的地方……
對,我知道……不過話說回來,或許不能這麼說……(聳肩,嘆氣)總之,我不想再去想這部影片。這影片很震撼。放映後的面對面座談中,導演勞吉哈說,這部影片純粹是他個人沮喪感的呈現。他把他的沮喪感都表現在這部影片中。
《極限:殘殺煉獄》?
對,勞吉哈就是這麼說的,不過拉斯.馮.提爾也這麼說過《撒旦的情與慾》(AntiChrist,2009)這部影片。
我不曉得勞吉哈的情況,不過對於拉斯.馮.提爾,我想,他這麼說是有道理的。這幾年,我在研究恐怖電影的製作,以及為何能觸動人心,尤其之前我們討論到孩童在這類型影片中所占有的角色,以及恐怖電影如何影響我們。雖然佛洛依德的理論有點過時──他的理論強調孩童經驗會反映到成年生活──但這理論確實多少能解讀拉斯.馮.提爾生命中一連串怪異騷亂的事件。我曾在報上讀過一篇文章,拉斯.馮.提爾在裡頭提到,他的母親臨終前告訴他,他的父親不是他的生父。她曾跟某位知名的藝術家發生外遇,生下了他,所以,他才有藝術基因。這事件顯然對他造成影響,讓他陷入沮喪,也因此成就出《撒旦的情與慾》這部作品,也影響了他這個人,使得他成為丹麥有史以來最具天分,最受到認可的藝術家。我的意思是,當他想到母親的「實驗」成功了,他果真具有藝術天分時,他一定被這念頭所深深折磨著。
對,所以你會有這種想法。拉斯.馮.提爾和墨西哥裔導演葛雷摩.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是我最愛的導演,他們兩人實在很棒。我認為拉斯.馮.提爾所拍攝的電視影集《王國》(Riket,1997、1997)是有史以來最棒的影集,反正就是……棒透了。
拉斯.馮.提爾在《王國》和《撒旦的情與慾》裡把孩子當成敘述的工具,從這點來說,葛雷摩.戴.托羅也一樣。
對,葛雷摩.戴.托羅在《羊男的迷宮》(Pan's Labyrinth,2006)中也這麼做。這部電影大概是所有電影類型中我最愛的一部。這些以孩童為敘述工具的電影都很成功,很能引發觀眾的共鳴。我們會想看孩子渡過難關,安安全全地活下來把故事說完。他們會激起人類的重要情感,若運用得當,他們就會成為很有效的工具。
約翰.傑維德.倫德維斯特,這個結論說得真好,非常感謝你撥冗接受我們的訪問。謝謝。
謝謝。


 2015/05/18
2015/05/18 2014/01/18
2014/01/18 2013/12/22
2013/12/22 2013/03/06
2013/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