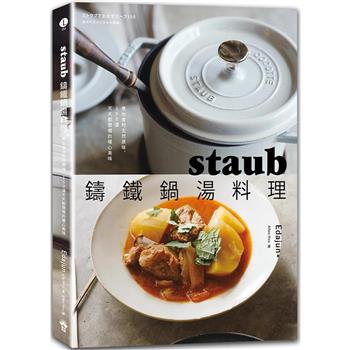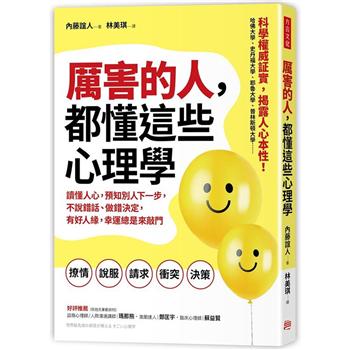經濟長久繁榮的關鍵,竟然是政治!
是要深化民主,或者向威權靠攏?
《槍炮、病菌與鋼鐵》後,最具啟發性與解釋力的經典之作
克拉克獎章得主,經濟學界最耀眼的新生代大師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致推薦
「真正傑出的作品……提出一個簡潔有力的卓越答案。」
──李維特,《蘋果橘子經濟學》作者
「應該列為政治人物以及所有關心經濟發展的人的必讀書目。」
──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
以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解釋人類社會的命運
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為什麼窮國都集中在熱帶或下撒哈拉非洲,富國都在溫帶?帶來繁榮富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富裕的社會能夠一直繁榮下去嗎?一個社會的貧困與富裕,是如同《槍炮、病菌與鋼鐵》所說,受到風土與物種之類地理因素的影響呢?或是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也許是窮國的官員想不到好的政策?
作者的研究顯示,窮國之所以貧窮,不是由於命定的地理因素,也不是因為傳統文化作祟。糟糕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因為執政者愚笨無知,而是他們刻意圖利支持其權力的特權菁英,代價是整體社會的利益。繁榮富裕的關鍵在於這個社會採行何種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
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作者稱為廣納型制度,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作者稱為榨取型制度,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
數千年的全球史也說明,制度可以往更具廣納性的方向移動,也可能會倒退回較具榨取性的狀態,淺層的民主也可能被綁架成為實質的權貴政治。
中世紀的威尼斯因為採行較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而邁向富裕繁盛,反過來又帶動制度朝更加廣納的方向前進,盛極一時而稱霸地中海。但早期的菁英豪族不甘於新人輩出瓜分利益,在當時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下反撲成功,將威尼斯快速拉往封閉的榨取方向,因而導致它逐漸衰落。
作者將備受推崇的多年學術成果,化為架構完整順暢易讀的一般讀物。他們以全球史為素材,運用嚴謹的經濟學分析與政治學洞見,幾乎全面檢視歐美亞非等地的歷史發展,並提出簡潔有力的理論解釋。對於臺灣當前的內外處境,此書恰是幫助我們釐清方向的重要啟示。
* * *
基於十五年的原創研究,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列舉出許多精采的歷史證據,從羅馬帝國、馬雅城邦、中世紀的威尼斯、蘇聯、拉丁美洲、英國、歐洲、美國與非洲,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嶄新理論,非常貼近當前世界關心的重大課題:
♦中國在威權統治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持續狂飆並超越西方國家?
♦美國的好日子是否已經到了盡頭?美國是否正從抵抗既得利益菁英擴大自己權力的良性循環,走向讓一小撮人更富有並掌控更多權力的惡性循環?反觀臺灣呢?
♦要幫助數十億貧困國家的人民脫離貧困,最有效的方式是什麼?西方富國提供更高金額的人道援助?或是從本書作者對於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互動觀察當中找到可行方法?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將會改變你看待世界與理解世界的方式。
作者簡介: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曾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200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專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也是未來最熱門的諾貝爾獎人選。艾塞默魯是全球經濟學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名經濟學者,他的論文產量驚人,是經濟學界最猛悍的新秀。
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
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既是政治學家也是經濟學家。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與拉丁美洲專家,目前在剛果、獅子山共和國、海地與哥倫比亞各國皆主持研究計畫,每年夏季會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學授課。
譯者簡介:
吳國卿
現任國內財經專業報紙資深編譯,負責翻譯本書序言至第八章,譯有《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下一個榮景:當經濟遇上政治》、《碳交易:氣候變遷的市場解決方案》、《趨勢力:改變未來15年的世界樣貌》、《誰劫走了全球經濟》、《衰退危機下的6大價值型投資》、《下一波全球貨幣大戰》等。
鄧伯宸
資深譯者,負責翻譯本書第九章至十五章,譯有《族群:集體認同與政治變遷》、《東方與西方的心靈交會》、《時間等候區》、《生活之道》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專文推薦
吳乃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叡人(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孟奇(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馮勃翰(香港城市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推薦
有三個理由讓你愛上這本書:它是關於現代世界各國的所得差異,這或許是當前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它充滿許多迷人的故事,可以讓你在雞尾酒會上滔滔不絕,例如為什麼非洲的波札那發展迅速而獅子山共和國卻完全沒有。而且它非常好看。就像我一樣,你可能會拚著一次把它讀完,然後回頭一讀再讀。
──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
許久以前一個沒沒無聞的蘇格蘭哲學家寫了一本書,討論國家成功的原因以及國家失敗的原因。《國富論》直到今天還是受到廣泛閱讀。以同等的洞察力及同等的廣闊歷史視野,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為我們這個時代重新處理同一個問題。兩個世紀之後,我們的曾曾…曾子孫同樣也會閱讀《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艾克羅夫(George Akerlof),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為什麼外表相似的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卻有如此大的差異?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對這個論辯主題做了重大貢獻。透過廣泛多樣的歷史例證,他們說明制度發展有時候基於偶然的因素,卻造成影響巨大的結果。社會的開放性及其允許創造性破壞的意願,以及法治,似乎對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亞羅(Kenneth J. Arrow),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作者以很有說服力的方式證明,國家只有在具備適當的經濟制度時才能擺脫貧窮,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財產制與競爭。更具獨創性的是,他們認為當國家擁有開放的多元政治體系,可競爭政治公職、選舉權普及,同時新政治領袖有機會崛起時,才比較可能發展出適宜的制度。他們重大貢獻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緊密關聯性,這種關聯性顯現在他們對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一項重大問題極為有力的研究中。
──貝克(Gary S. Becker),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這是一本重要而有獨到見解的書,以眾多歷史例證證明廣納的政治制度能支援廣納的經濟制度,而這是國家持續繁榮的關鍵。本書檢視一些良性的政權如何創建並經歷良性循環,而惡性政權則經歷惡性循環。這是世人不應忽略的重要分析。
──戴蒙德(Peter Diamond),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對一些認為國家的經濟命途取決於地理或文化的人來說,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帶來的是壞消息。決定國家會變成富國或窮國的主要因素是人所創建的制度,而非取決於地理或我們祖先的信仰。艾塞默魯和羅賓森綜合了從亞當斯密、諾斯(Douglass North)到更晚近的經濟史學者的實證研究,寫出這本引人入勝又順暢好讀的書。
──弗格森(Niall Ferguson),《貨幣崛起》作者
艾塞默魯和羅賓森這兩位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發展專家,揭露了導致國家富裕或貧窮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疾病或文化,而是制度與政治。這本深入淺出的書充滿深刻的洞見,適合專家和一般讀者閱讀。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
一本充滿睿智而且振奮人心的書──同時也敲響了令人深感不安的警鐘。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建立了一套極有說服力的理論,涵蓋幾乎一切與經濟發展有關的事務。當國家設置對成長有利的政治制度時就會興起,當這些體系僵化或無能調整時,國家就會衰敗,而且往往差距極大。所有國家的有權有勢者,永遠會追求完全掌控政府,出於貪婪而阻礙整體社會進步。因此必須以有效的民主節制這些人,否則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國家走向衰敗。
──江森(Simon Johnson),《13個銀行家》作者、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
兩位全世界最傑出、最博學的經濟學家,挑戰一個最難解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貧窮、有些則富裕?本書對經濟學與政治史有著極深刻的認識,很可能是迄今對「制度很重要」的觀點最強而有力的論述。這是一本發人深省、充滿教育性,同時又令人著迷的書。
──莫基爾(Joel Mokyr),西北大學經濟史教授、羅伯史卓茲人文社會與科學教授
兩位當代社會科學的巨人在這本深入淺出的著作中,引領我們輕鬆瀏覽四百年歷史,並帶給我們一個令人鼓舞而重要的訊息:自由讓世界富有。世界各地的暴君要顫抖了!
──莫里斯(Ian Morris),史丹佛大學歷史學及古典學教授,《為什麼西方統治世界至今》作者
想像圍坐在桌邊聽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麥迪遜(James Madison)探討兩千多年的政治史與經濟史。想像他們把自己的思想融入一個前後一致的理論架構,這個架構建立在限制壓榨、鼓勵創造性破壞,和建立權力均享的強大政治制度上,然後你將開始明白這本睿智而引人入勝著作的貢獻。
──佩吉(Scott E. Page),密西根大學及聖塔菲研究所
在這本內容驚人豐富的書中,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問了一個簡單而重要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變富裕,有些國家則依舊貧窮?他們的答案也很簡單──因為政治體發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本書最了不起的是它的文字爽快而明瞭,論述優雅並充滿歷史細節。此刻正當西方各國政府必須喚起政治意志以因應史無前例的債務危機,這是一本非讀不可的書。
──平卡斯(Steven Pincus),耶魯大學歷史與國際及區域研究杜菲教授
「笨蛋,問題在政治!」這就是艾塞默魯和羅賓森簡單但說服力十足的解釋,說明了為什麼許多國家未能繁榮發展的原因。從斯圖亞特王朝到戰前的美國南方、從獅子山到哥倫比亞,這本權威的著作證明菁英如何制訂圖利自己的規則,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作者審慎地尋求悲觀者與樂觀者間的平衡,說明歷史和地理未必決定國家的命途。他們也記述了明智的經濟思想和政策若沒有根本的政治改革輔助,往往成效不大。
──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
這不只是一本迷人而有趣的書,而且是真正重要的書。艾塞默魯和羅賓森高度原創的研究,闡明了經濟力量、政治和政策選擇如何共同演進並互相影響,以及制度如何影響此等演進,而這對瞭解社會與國家的成功與失敗極其重要。這些洞識在本書中以深入淺出、極吸引人的形式呈現。買這本書並開始閱讀的人會發現自己捨不得放下它。
──史賓塞(Michael Spence),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這是一本迷人而且容易閱讀的書,專注於討論政治與經濟制度複雜的共同演進,包括往良性和惡性的方向發展。它巧妙地掌握政治與經濟行為的邏輯,以及或大或小的偶發歷史事件(在關鍵時期)造成的方向轉變之間的平衡。艾塞默魯和羅賓森提供了極其廣泛的歷史例證,說明此等轉變如何促成有利的制度、進步的創新,以及經濟成功,或者惡化成壓榨性的制度並終至崩潰或停滯。這些例子能讓人感到刺激,同時也勾起反思。
──梭羅(Robert Solow),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名人推薦: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專文推薦
吳乃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叡人(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孟奇(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馮勃翰(香港城市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推薦
有三個理由讓你愛上這本書:它是關於現代世界各國的所得差異,這或許是當前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它充滿許多迷人的故事,可以讓你在雞尾酒會上滔滔不絕,例如為什麼非洲的波札那發展迅速而獅子山共和國卻完全沒有。而且它非常好看。就像我一樣,你可能會拚著一次把它讀完,然後回頭一讀再讀。
──賈德.戴蒙,《槍炮、病...
章節試閱
【書摘1】
推薦序:大哉問,大哉答
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交換學者
在戴蒙(Jared Diamond)教授親自主持、依其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製播的影片中,一開頭戴蒙的新幾內亞朋友就問他:「為什麼白人有這麼多好物,而我們新幾內亞人這麼少?」
這個問題乍聽之下平淡無奇,但卻很可能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問題:長期經濟成長與發展的來源到底是什麼?一千年前,世界各地人的生活水準並未有太大的差異,為什麼一千年後,美國人的所得是阿富汗人的五十倍?而非洲大部分國家每人平均國民所得都不超過一千美元?是因為工業革命嗎?那為什麼它發生在英國而不是中國或非洲?國家要如何才能持續的發展?怎樣的國家會走向衰敗?難怪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曾說:「一旦開始思考經濟成長的起源,你就很難再想別的問題了!」
地理環境決定一切?
戴蒙在他的書中,提供了一個簡潔有力的答案:「地理環境決定了一切。」(翻成白話就是:一切都是命!)九千年前,幸運住在肥沃新月的人們,從採集進入了農耕,並且學會了種植與馴化如馬、豬等野生動物,農業生產力增加的結果,讓人類有更多精力發展更複雜的文化、技術與社會結構;而歐亞大陸的橫向連結,有別於美洲或非洲大陸的縱向連結,因不需橫跨不同緯度(因此沒有氣候適應的問題),也讓整個交流(不論是貿易、戰爭、技術或疾病及其抵抗力)與發展相對容易。這個一開始的起點優勢(head start)經過長時期的正向循環(positive feedback loop)不斷累積後,到十五世紀,已經足以支持歐亞以槍炮與病菌殖民美洲與非洲,開展五百年的霸權,而這一切都是一開始的地理環境所造成!
這個理論看來非常吸引人,一些學者如哥倫比亞大學的沙克斯(Sachs)也持相同的看法, 但是有人或許會問:「那為什麼過去五百年來歐洲的發展領先亞洲?而許多地理文化環境幾乎完全相同的地方如南北韓、甚至是美墨邊境上僅一牆之隔的兩個小城鎮,在今天的發展卻如此不同?」
笨蛋!問題在制度!
艾塞默魯和羅賓森以兩人十五年來共同研究的成果,回答了這個問題:不是地理環境,而是制度──是我們如何組織社會來生產並分配資源的制度過程,決定了我們今天是否繁榮昌盛!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也是決定國家走向興盛或衰敗的最大原因。若能在經濟上致力於保護財產權、制訂不因人而異的遊戲規則、鼓勵資源往新科技方向投資;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國家就能持續發展。反之,國家若被只想攫取資源的少數政治菁英把持,則必然走向衰敗。兩人在書中將此二者定義為廣納型(inclusive,或也可譯為涵納)和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作者即以這兩個概念貫穿全書,討論社會科學中最重要也困難的問題之一:什麼原因決定了國家的制度選擇?這個選擇的長期後果又是什麼?
書中列舉出許多歷史實例來反覆闡述這組核心概念。兩人論證「廣納型的經濟制度」會與「民主且重視多元價值的廣納型政治制度」形成良性循環、相互支持。書中以英國光榮革命為例,從以議會為主要政治權力運作場域開始,經過代表社會各個勢力相互制衡的動態政治過程(雖然其中或有你死我活,試圖為自己團體設立掠奪型制度的鬥爭)之後,形成了廣納性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良性循環,也對日後工業革命的誕生及英國的發展,奠下了良好的基礎;反之,「榨取型的政治制度」則會與「榨取型的經濟制度」相互唱和,形成惡性循環,即使短期之內會有經濟成長,但必然無法持續。
另外,這些制度的影響,也往往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影響深遠。書中也引用兩位皆於哈佛大學經濟系任教的新秀努恩(Nathan Nunn)與戴爾(Melissa Dell)的研究來支持此一論點。努恩整理四百年前非洲黑奴買賣運送的資料發現,「當年」輸出越多奴隸的地區,「現在」的經濟發展越差。或許有人會問:「說不定此一相關是因為越貧窮地區輸出越多奴隸的緣故。」但是其實正好相反──奴隸輸出是與該地區跟港口的距離有關(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即是以港口距離作為工具變數)。依照他的估計,如果當年沒有奴隸貿易,非洲現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差距會縮小百分之七十!另外,由於當時黑奴大部分是被親友或他族拐騙強擄,因此時至今日,對他人的信任程度也受到當年奴隸交易的影響!戴爾則是以西班牙殖民祕魯境內時所實行的原住民強迫奴役制度(稱之為米塔﹝mita﹞)為研究對象,發現即使到了今天,在米塔邊界線(此即經濟學家所謂的回歸不連續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兩邊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都仍然有不小的差異!
另外,他們在書中也從許多面向來討論制度是如何形成。其中包括:在國家面臨十字路口時,些微的差異(如十七世紀的英國與西班牙)可能就會導致不同的抉擇。透過蝴蝶效應,數百年後兩國樣貌就會大不相同。而有豐沛自然資源的國家,有時也會受到此一恩賜的詛咒。更重要的是,政治菁英在發展過程中,經常扮演的是阻力而非助力的角色!這些推論過程與歷史事實的連結,在書中俯拾皆是,展現了兩位作者博覽群書、旁徵博引的功力!我想我就不要再爆雷,把這些閱讀的樂趣留給讀者吧!
而這些論點,其實也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與聯合國和其他非營利組織該如何協助貧窮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有些學者如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抱怨:現在有太多的研究能量花在西方能提供協助的小事上──要發放多少蚊帳來防治瘧疾?發放多少保險套來防範愛滋病?發多少免費課本來增加教育程度?但是對於更重要的大問題研究卻相對稀少。我們或許該問:是什麼樣的制度,讓這個國家走到現在這個地步?哪一些制度改革,可以改變該地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如果我們不能從根本改變資源分配的方式,那再多的援助(這也是聯合國目前的標準做法──邀請安潔莉娜裘莉和U2樂團主唱BONO送愛心到非洲)不但無濟於事,也有可能帶來反效果!事實上努恩和耶魯大學的錢楠筠(Nancy Qian)就發現,「糧食援助」反而會使非洲發生內戰的機率增加!
嚴謹學術研究結果支撐的論點
不過,有挑剔習慣或社會科學背景的讀者或許會抱怨,許多例子雖然有趣且引用得宜,但是不免讓人有事後合理化(ex post rationalization)之感:既然廣納是好的,那現在發展好的地方,其制度結構一定就是廣納型的,也一定可以找到一個開始廣納型制度的歷史起始點,反之亦然。會讓人有此感覺是因為這本書主要設定的是一般讀者群,因此將枯燥且複雜的統計結果或數學模型推論直接跳過,但是書中的結論,都是經同儕激烈爭辯、審查後出版的嚴謹學術成果,而這些過程的最重要目的,就是盡可能將作者的循環論證減到最低。我在此就舉兩個例子加以仔細說明。
首先讓我們來細讀兩人在二○○一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的重要文章──「比較發展的殖民緣起:一個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這是他們兩人一開始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這一整支文獻的重要起點。在這篇文章中,他們首先問道:
許多學者都已有共識,重視財產權保護、實施較少效率扭曲的政策,以及有較佳政治制度設計的國家,會藉由將資源更有效率地投注在人力資源、實體資本和基礎建設的改善上,持續的推動經濟發展;而直接觀察世界各國的資料,也的確可以發現「財產權保護指標」與「每人平均國民所得」之間的確是有正相關的。看起來理論與資料相互契合,結論也是我們所樂見的,那到底有什麼好擔心的?
然而任何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都會告訴你:「相關不等於因果」,財產權保護與國民所得的正相關「不代表」改善財產權就會增加經濟成長。《蘋果橘子經濟學》中提到「警察越多的地方犯罪率越高」現象的討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建立並維繫一個好的財產權制度,是需要投入許多資源的(想像法院、警察以及各種典章制度所需的成本),因此制度與國民所得之間的正向關係,有可能只是富裕國家較有資源負擔較佳的制度而已。另外,也有可能是這些國家在其他條件上的不同(比如說人民較為勤奮正直,或天然資源豐富),同時讓制度變好以及所得增加所致。此即是所謂的反向因果關係(reversed causality)與遺漏變數(omitted variable),這兩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那麼上述的觀察就只是虛假相關而已。
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內生性問題」,而解決之道即是找到一個只會透過改變制度來影響國民所得的「工具變數」。讀者可以想像,上帝站在地球儀前面替每個國家擲銅板,正面就給好制度,反面則反之,這樣的隨機實驗就可以保證觀察到的制度與所得的相關,一定是「因果」!現實世界中的確存在這類似上帝之手的工具變數,但是並不好找。兩位作者最大貢獻在於:他們以「歐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為工具變數,成功的解決了內生性的問題。他們發現,在瘧疾與黃熱病越猖獗之處,由於歐洲人越難在該地移民扎根,因此越容易設計一個榨取式的殖民體系,將重心放在如何將殖民地資源提取為母國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較容易將母國較好的財產保護、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過來。即使是在殖民地獨立後,新興起的本地政治菁英也會因為改變制度成本太大,或者是本來在殖民政權下就已經與原來制度發展出一套共生共利的關係,而直接接收原本制度,這種路徑相依的特性,使得當時設立的制度持續存在,對今天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而這裡所謂的「殖民地死亡率」就是一個絕佳的工具變數!這篇文章十年來已經被引用超過六千次,其影響力可見一般。
同時,另一篇「西方為何讓更多民眾可以投票」(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則是從政治菁英和民眾間的策略性互動,來研究投票權(民主)如何產生,以及其後果為何。這雖然是一篇相對複雜的數學模型論文,但是結論卻是相對直覺:政治菁英之所以願意開啟政治改革釋放權力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愛護人民,而是因為害怕社會不滿情緒蔓延,造成動盪甚至革命,進而損及他們利益的緣故。那為什麼結果不是在不改變現有制度的前提下進行重分配?比如說,不釋出投票權,但是答應每人每年加發十公斤豬肉?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承諾是不可信的(not credible):一旦示威群眾從廣場散去,要再集結起來就幾乎不可能,掌權者當然就也不必信守承諾了。倒推回來,群眾就必須堅持下去,直至合理可信的安排出現為止。而當政治制度將更多人納進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時,此一廣納式的安排,也就增加重分配政策出現的機率,並減少社會的不平等。閱讀至此,對臺灣一九八○年代開始的民主化過程,與接著下來的社會福利擴張相對照,是否有似曾相識之感?這兩篇文章其實就是兩位作者一起研究的起點,書中所使用的廣納與榨取二詞,也是由此演化而來。
除了計量分析的嚴謹外,大量的歷史資料與旁徵博引的史實,更讓人佩服兩位作者的寫作功力!當討論到殖民地死亡率的問題時,他們就舉了兩個有趣的例子:第一個是十七世紀的一批宗教移民,在最後關頭只剩兩地的決選名單中放棄了圭亞那(Guyana),選擇了另一個死亡率較低之處;第二個則是一七八五年英國的博尚(Beauchamp)委員會,本來考慮要將罪犯運至西非岡比亞(Gambia),最後也是因該地死亡率「連對罪犯來說都太高」而作罷。讀者或許會好奇:接下來歷史如何發展呢?那一批清教徒最後落腳在麻州東岸的普利茅斯,而英國罪犯,則被送到澳大利亞!而當討論到投票權如何擴張,作者也以英國、法國、德國、瑞典的政治史加以佐證,能夠同時將理論(數學模型的推導)、實證(資料的統計分析)以及歷史事實加以結合論證結果,不僅是在經濟學界,甚至在整個社會科學界都是非常少見的!
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看法
使用這個概念,兩位作者也對目前流行的中國崛起論提出了他們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本質上仍是一個榨取型制度。改革初期的高速經濟成長,有一部分是由於將誘因結構引進原來完全無效率的生產制度,因此將整個中國原來完全錯置的資源「歸位」所產生的。另一部份則是因短期內快速引進了最有效率的生產技術取代原有低生產力技術而來(即經濟學家所謂的technology catch-up)。因此一開始的高經濟成長率,是在基期很低的情況下計算出來的,即使以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在二○一二年也只有八千八百美元,比泰國、哥倫比亞、土耳其都還要低。而近期的經濟成長,也有部分是由於共產黨獨占大量的經濟資本,因此可以藉由在短時間之內移動大規模的資源到某個部門而來的。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擁有審批權與選擇性執法權力的政治菁英,才是趁機攫取了大部分的經濟租的最大受益者。最近有關中國是由幾百個菁英家族透過綿密的政商關係加以統治的報導,以及前陣子《紐約時報》的獨立調查所揭露的總理綿密投資網絡,似乎證實此言不虛。而在這樣榨取型的政經制度之下,權力輪替的後果不是人民福祉的改善,而只是換了一批不同的政治菁英獲取利益而已。雖然在過去幾年,我們的確見到中國出現了一些零星的政治改革,但是這似乎仍不足以將中國推向一個廣納型政治與經濟制度之間的良性循環。
另一個他們對中國發展不表樂觀的理由,則是來自於熊彼得「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此概念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經常是不連續的──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人冒險成功,導致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改變,這個新生產技術會將舊技術徹底淘汰,而這比起在原有的技術上做小規模的改良,是更能夠增進生產力的。但是創造性的破壞只能在廣納型制度下才有辦法被孕育──想像依靠舊技術獲利的政治菁英,怎麼可能不運用各種力量去打壓此一威脅他們既得利益的點子。因此中國只能山寨既有的技術,無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過創造性破壞的過程,發展出取代舊做法的新技術,這樣很容易就會達到經濟學上所謂邊際產值遞減的狀態,無法再繼續支持經濟成長。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對中國宣稱已經找到結合「政治控制與經濟成長」的神奇處方這個說法不買帳的緣故。以下這個稍帶嘲諷的說法,準確地傳達了他們的訊息:「你可以想像一個二十歲的大學輟學生,向國有銀行貸款,準備開一家可以挑戰國營企業的公司嗎?在中國?(除非他是政治菁英的一員)」
這些看法對正站在十字路口上的臺灣有很大的啟示:對於正朝廣納型制度的良性循環邁進的我們,要如何避免被吸入榨取型制度的惡性循環中?
兩人個性背景迥異互補恰到好處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兩人所代表的,其實是汲取歷史分析與政治經濟學理論模型的養分、以統計方法結合歷史資料、使用國家層級資料為分析對象、並藉由歷史的自然實驗為切入點的歷史與經濟發展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記得十二年前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學貝克(Gary Becker)教授的應用個體研討會見到艾塞默魯教授時,大家還對這種角度有許多疑慮,但是經過這些年來兩人的努力,這樣的手法已經被許多人所接受了。我本年度正好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頂尖大學聯盟交換學者,也因此與兩位學者熟識,最後就讓我對兩人的背景與風格做更進一步地介紹。
艾塞默魯成長於伊斯坦堡,一九九二年以二十五歲的年紀就拿到倫敦政經學院博士並留校任教,隔年即被麻省理工挖角至今,在經濟成長、政治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等領域皆著作等身,是公認的多產且跨領域的天才型學者。二○○五年獲得克拉克獎時,哈佛的曼昆(Greg Mankiw)還開玩笑的說:「達倫!是時候讓你的祕密雙胞胎出來了!(it is time to let your secret twin out!)」 同行對他的評價,可見一般。
他曾提到,其實在高中修習經濟學時,他就已經對世界各國為什麼發展如此不同產生極大興趣。再加上成長過程中經歷過土耳其的軍事統治,更是讓他選擇以政治制度角度切入的重要理由。而不論是上課或在會議上報告,他總是聲如洪鐘、自信滿滿,再加上身材高大,看起來就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去年十月在美國國民經濟局(NBER)一場以「中國經濟何處去」為題的演講中,一開始以就以一九六○年代美國經濟學者錯誤預測蘇聯經濟會在一九八○年超越美國的往事作為開場白(也可以說是結論?),把大家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迷思,即大家對所謂中國式的「競爭」領導機制、隔代指派與共產黨正確經濟政策是造成中國經濟成長的說法,以本書的論點加以一一反駁。這樣不和稀泥、據理力爭、捍衛自己的論點,也是成就一位好學者的重要特質。
羅賓森的父親則是英國派駐殖民地的官員,從小跟父親住過迦納、奈及利亞,以及千里達多巴等地,這個特殊的童年經驗,顯然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為什麼這裡人的生活與我如此不同」的疑問。而二○一二年秋季我旁聽了他與努恩合開的比較歷史的經濟發展課程,也更親炙其教學魅力。他不但上起課來博學多聞,隨手拈來的史實與所要論證的觀點環環相扣,而且經濟、政治、社會學家的觀點,在他手上玩弄起來也是那麼輕鬆自然。更重要的是他一點也沒有架子,總是耐心聽完學生們的想法,再一一與其討論。對於他不喜歡的論點,也僅會以詼諧帶點嘲諷的方式加以評論;而對於尖酸批評他們的觀點,他也不會如某些沒有安全感的學者,以侵略性的言語加以反駁,頂多只是淡淡地說:「嗯,但這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上。(ya, but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QJE.)」展現出一派輕鬆寫意的英國紳士魅力與氣度。
針對一般讀者而寫的科普書籍,市面上並不少見,但是能夠將背後有扎實推論基礎的學術研究成果,轉換成一般大眾可以閱讀作品的學者並不多見。本書與《蘋果橘子經濟學》大概是過去幾年來,在可讀性與嚴謹度上最好的兩本書。(該書作者李維特,也盛讚此書是「簡潔有力」的精采!)而這本書的出版,也讓他們在非學術圈的名聲越來越大,不但世界各地演講與邀約不斷,據說連中國的領導階層也都在閱讀這本書:有人把書名翻成「國敗論」(與國富論相對應),其影響力可見一般。不過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正值學術能量的高峰的兩人,仍然堅守在學術的崗位上持續創作。他們這兩年也共同發表了如「法國大革命的長期制度影響」、「納粹大屠殺對蘇聯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國家選擇何種經濟制度較為有利」等多篇論文。羅賓森甚至還到哥倫比亞研究當地軍閥如何形成治理制度,並與其他軍閥和政府之間相互競爭的過程!其實,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制度的起源,長期影響以及演變、及與其他經濟社會狀況間的互動,仍有許多未解的難題。以兩人的研究能量,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再看到下一本類似的作品!
【書摘2】
序言
本書討論的主題是世界上的富裕國家如美國、英國和德國,以及貧窮國家如下撒哈拉非洲、中美洲和南亞的國家,在所得和生活水準上的懸殊差距。
在我們寫這篇序言時,北非和中東正經歷「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震撼,這場運動始於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一名叫博阿齊齊(Mohamed Bouazizi)的街頭小販自焚激起大眾的憤怒,進而點燃所謂的茉莉革命(Jasmine Revolution)。到了二○一○年一月十四日,從一九八七年以來就統治突尼西亞的總統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已經下臺,但反對突尼西亞統治菁英的革命浪潮不但未曾平息,反而益發強烈,並蔓延到中東其他國家。嚴密掌控埃及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遭罷黜。當我們寫完序言後,巴林、利比亞、敘利亞和葉門政權的命途已岌岌不保。
這些國家內部不滿的根源在於貧窮。埃及人平均所得水準只有美國人的十二%左右,預期壽命則少十年;二○%的埃及人口生活在赤貧中。雖然這些差異很顯著,但比起美國與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如北韓、獅子山和辛巴威還算小,因為後面這些國家生活在貧窮中的人口遠超過半數。
為什麼埃及比美國貧窮這麼多?有哪些限制因素使埃及人無法變富裕?埃及的貧窮是無法改變的呢,或者它的貧窮可以根除?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順理成章的方法是,聽埃及人自己談論他們面對的問題,以及為什麼他們挺身反對穆巴拉克政權。二十四歲的哈梅德是開羅一家廣告代理商的員工,她在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示威時清楚地表達她的觀點:「我們受到貪腐、壓迫和劣質教育的荼毒。我們生活在一個必須改變的腐化體系中。」廣場另一位示威者、二十歲的夏米是一名藥學系學生,他表達相同的看法說:「我希望到今年底時我們能有一個民選政府,公民自由獲得保障,而且我們能終結掌控這個國家的貪瀆。」解放廣場的抗議者異口同聲譴責政府的腐化、無能提供公共服務,以及國內缺乏機會平等。他們尤其控訴壓迫和缺乏政治權利。正如國際原子能總署前署長艾爾巴拉岱(Mohamed ElBaradei)二○一一年一月十三日在推特(Twitter)上寫的:「突尼西亞:壓迫+缺乏社會正義+封殺和平改革管道=定時炸彈。」埃及人和突尼西亞人都認為他們的經濟問題根源是缺乏政治權利。當抗議者開始更有系統地表述他們的要求時,埃及抗議運動領袖之一、軟體工程師兼部落客哈利勒(Wael Khalil)張貼了第一份十二項立即要求,全部集中在政治改革上。提高最低薪資之類的議題只出現在中程要求當中,留待稍後實施。
對埃及人來說,導致他們落後的原因包括一個無能且貪腐的國家,一個讓他們無法發揮才能、雄心和原創性的社會,以及他們所得到的教育。但是他們也知道,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們面對的經濟阻礙,來自於政治權力在埃及由少數菁英行使與壟斷的方式。他們瞭解,這是他們首先要改變的事。
然而,解放廣場上的抗議者對這個議題的看法,卻與主流思想明顯背離。當辯論為什麼像埃及這樣的國家如此貧窮時,大多數學者與評論家都強調完全不同的因素。有些人強調埃及的貧窮主要由地理條件所決定,因為這個國家大部分是沙漠,且缺乏足夠的降雨,土壤和氣候不適於高生產力的農業。其他人則指出,埃及人的文化特質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繁榮富裕。他們說,埃及人缺乏讓其他國家繁榮興盛的工作倫理和文化特質,而且還接受與經濟成功相衝突的伊斯蘭信仰。第三種看法在經濟學家和政策專家當中是主流意見,這種看法認為埃及統治者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來促使他們國家繁榮起來,並且在過去一直採用不正確的政策和策略。這種看法也認為,如果這些統治者能接受正確的顧問提供正確的諮詢,富裕興盛將隨之而來。對這些學者專家來說,統治埃及的少數菁英只顧自己利益、犧牲社會福祉的事實,似乎與瞭解這個國家的經濟問題毫不相干。
在本書,我們將論述解放廣場上的埃及人看法才是正確的,而不是大多數學者和評論家的看法。事實上,埃及之所以貧窮就是因為它被一小群菁英統治,他們以圖利自己的方式組織社會,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用來為掌權者製造龐大的財富,例如前總統穆巴拉克顯然累積了七百億美元財富。輸家是埃及人民,而且他們有切身之痛。
我們將證明,對埃及貧窮的這種詮釋(也就是人民的看法),也對「為什麼窮國會貧窮」提供一種普遍的解釋。不管是在北韓、獅子山或辛巴威,我們將說明窮國為什麼貧窮的原因就和埃及貧窮一樣。英國和美國之類的國家變富裕,是因為它們的人民推翻掌控權力的菁英,創造了一個政治權利更廣泛分配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府需要回應人民並對人民負責,而且廣大民眾都能夠利用經濟機會。我們將說明,要瞭解今日世界何以有這種不平等,就必須深入過去,研究各個社會的歷史演進。我們將發現,英國之所以比埃及富裕,是因為英國(精確地說是英格蘭)在一六八八年發生一場革命,促成了該國的政治轉型以及伴隨的經濟轉型。人民爭取並贏得更多政治權利,而且利用這些權利來擴大自身的經濟機會。其結果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與經濟演進軌跡,並在工業革命達到高潮。
工業革命及其解放的科技發展並未擴散到埃及,因為該國當時在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掌控下,受到的待遇和後世穆巴拉克家族的對待相去不遠。鄂圖曼在埃及的統治於一七九八年被拿破崙推翻,但該國隨後又落入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掌控,他們對促進埃及的富裕繁榮和鄂圖曼人一樣興趣缺缺。雖然埃及人終於擺脫鄂圖曼帝國和大英帝國、並在一九五二年推翻君主政體,但這種改變與一六八八年英國的革命不同;埃及政治並未從根本上轉型,只是把權力交給另一批菁英,而他們對於為埃及人民創造富裕的漠不關心也與鄂圖曼和英國如出一轍。結果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並未改變,埃及也依然貧窮如故。
本書將探究長期下來這些模式如何自我複製,以及為什麼有時候它們會改變,就像一六八八年英國發生的事件,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這將協助我們瞭解今日埃及的情況是否已經改變,以及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會不會帶來一套能夠帶給一般埃及人民富裕的新制度。埃及過去曾發生過未帶來改變的革命,因為發動革命的人只是接管被罷黜者的統治,重新建立類似的體系。一般人民確實難以獲得真正的政治權力,並改變社會運作的方式。但真正的改變仍然可能發生,而我們將看到它在英國、法國和美國,以及日本、波札那(Botswana)和巴西等國家如何發生。基本上貧窮的社會想變富裕,需要的就是政治轉型。有證據顯示埃及可能正在發生這種轉型。另一位解放廣場的抗議者邁特瓦利說:「現在你看到穆斯林和基督徒站在一起,你也看到老年人和年輕人同心協力,他們都想要相同的東西。」我們將看到社會中這種廣泛的運動就是這類政治轉型發生的關鍵。如果我們瞭解這類轉型發生的時機和原因,我們將更有能力評估哪些運動就像過去那樣將以失敗收場,以及哪些運動我們可以期待將獲得成功,並改善數百萬人的生活。
【書摘1】
推薦序:大哉問,大哉答
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交換學者
在戴蒙(Jared Diamond)教授親自主持、依其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製播的影片中,一開頭戴蒙的新幾內亞朋友就問他:「為什麼白人有這麼多好物,而我們新幾內亞人這麼少?」
這個問題乍聽之下平淡無奇,但卻很可能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問題:長期經濟成長與發展的來源到底是什麼?一千年前,世界各地人的生活水準並未有太大的差異,為什麼一千年後,美國人的所得是阿富汗人的五十倍?而非洲大部分國家每人平均國民所得都不超過一千美...
目錄
目次
推薦序:大哉問,大哉答/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序言
第1章 很近卻很不一樣
第2章 無效的理論
第3章 富裕與貧窮的形成
第4章 小差異和重要關鍵:歷史包袱
第5章 「我已見過未來,它行得通」:榨取制度下的成長
第6章 漸行漸遠
第7章 轉折點
第8章 別在我們的領土:發展的障礙
第9章 倒退發展
第10章 繁榮的擴散
第11章 良性循環
第12章 惡性循環
第13章 當今的國家為什麼失敗
第14章 打破桎梏
第15章 瞭解富裕與貧困
致謝
參考書目與資料來源
引用書目
目次
推薦序:大哉問,大哉答/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序言
第1章 很近卻很不一樣
第2章 無效的理論
第3章 富裕與貧窮的形成
第4章 小差異和重要關鍵:歷史包袱
第5章 「我已見過未來,它行得通」:榨取制度下的成長
第6章 漸行漸遠
第7章 轉折點
第8章 別在我們的領土:發展的障礙
第9章 倒退發展
第10章 繁榮的擴散
第11章 良性循環
第12章 惡性循環
第13章 當今的國家為什麼失敗
第14章 打破桎梏
第15章 瞭解富裕與貧困
致謝
參考書目與資料來源
引用書目


 2023/08/11
2023/08/11 2022/10/20
2022/10/20 2021/11/22
2021/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