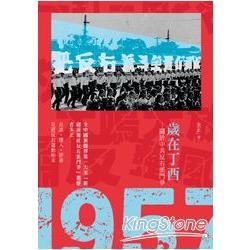【丁酉年紀事】
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 ―― 辛棄疾〈沁園春〉
一
一九五七年,我在長沙新湖南報社,在這裡經歷了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全過程。
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我被列為鬥爭對象,在整整一年時間裡,享受了每一隻「老虎」都享受過的一切待遇:檢查交代,批判鬥爭,不必說了。最難受的是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時,從吃飯到拉屎,都有專人看管,比起後來我在看守所和勞改隊的經歷,都管得更嚴厲些。鬥了一年,沒有查出什麼反革命的材料。於是說我參加了一個「思想落後小集團」,以撤職和降一級工資結案。我很覺得委屈,又不敢申辯,就這樣心有餘悸的過了幾個月。我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進入一九五七年的。
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初,我感覺到空氣似乎有了一點鬆動。《文匯報》復刊了。它連載了斯特朗的《史達林時代》,其中「巨大的瘋狂」一章是寫蘇聯肅反的,同我不久前身歷的大同小異。在《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停刊前不久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駁了史達林的「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公式。可以看出,空氣是有了一點變化。同事的臉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有一位大約是做工會工作的同事還要我去申請困難補助。我敬謝了她的好意,告訴她:我的《魯迅傳略》快要出了,將要得到一筆稿費。
三月,副總編輯蘇辛濤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回來,興沖沖地作了傳達,還傳達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四月,《人民日報》陸陸續續發表社論,宣傳新方針。費孝通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我也感到了一種早春的天氣。
五月一日,報上刊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一個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開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鎮反肅反那些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風細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原則,並且規定:「開會應該只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還說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幾天之後,總編輯官健平在全社大會上作動員報告,宣布報社開始整風,號召全體人員向報社領導提意見,反對三個主義。內容大體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說的。動員大會之後,即分小組開會座談,向領導提意見了。
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還規定了:「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我不是黨員,即根據這一規定提出不參加整風運動。我要報考大學,需要時間複習功課,準備考試。一天晚飯後,文教部同事黎風邀我同去散步,勸我還是參加整風運動。他說,黨有決心克服三個主義,希望你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他還說了:你不會沒有意見吧。我說,我只對於把我列入肅反對象有意見。他說,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提往事,不過是說清楚一下事實,並不是對黎風兄有任何抱怨之處,第一,我猜想,他是奉命來同我談話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間素無惡感(大約這就是由他來同我談話的原因吧),他絕沒有加害於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沒有他的勸說,事情的結局也不會有任何不同,因為,不久國務院就發布了《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的決定》,宣布「凡是進行整風的單位,所有工作人員,都應當積極地參加這一運動和鬥爭。」取消了原先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的規定。
就這樣,我就參加整風的小組會了。
那時,《人民日報》逐日詳細報導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新湖南報社內部的座談會也從這些報導中受到啟發,一些人學著說他們說的那些話,例如外行領導內行之類。在這一方面,他們對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評,說他對報紙業務一不懂二不鑽,外行得很。徐鑄成在〈「牆」是能夠拆掉的〉一文中,說《文匯報》的一位黨員副總編輯「有一套本事,能夠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這話在《新湖南報》引起了共鳴,一些人說,官健平所有的,正是這樣一套本事。
我在小組會上只提了一個問題,肅反運動肅我是錯了。一九四九年八月長沙解放,九月我即考進了新湖南報辦的新聞幹部訓練班,這時我還不滿十八歲,中學還沒有畢業。不但是沒有政治歷史問題,可以說還沒有政治歷史。為什麼要把我列為肅反運動對象呢?在肅反運動後期,宣布處理之前不久,報社肅反五人小組找我談話,念了一個〈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給我聽,我越聽越覺得同我沒有關係。這個文件中說的特務間諜、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惡霸、土匪、胡風分子、托匪分子、漢奸、蔣匪軍、政、警、憲人員、敵對階級、現行反革命破壞分子……都跟我扯不上邊。肅反運動一開始,就宣布俞潤泉、張志浩、朱正、鍾叔河四人是一個「反革命集團」。這四個新聞幹部訓練班的學員,過去並不怎麼接近,現在大約是因為都要加以打擊。就臨時編為一個小集團了。
有趣的是這個小集團的稱號,或者說「所定的性質」,開始,反革命小集團;批鬥若干時日之後,調子稍稍有點降低:反動小集團;最後定案材料上寫的,卻更加客氣,只不過是思想落後小集團了。當我看到拿給我簽字的這份定案材料,真是啼笑皆非。肅了一年,並沒有把我肅成反革命,這是因為十人小組的那個文件規定了一些具體界限,現在不說我反革命了,只說是思想落後,我有什麼辦法證明我的思想並不落後呢?在整風小組會上,我說:如果這是肅落後運動,我落後,肅我是肅對了。現在是肅反運動,在定案材料上沒有一條反革命的內容,肅我是肅錯了。
這裡簡單插說一下新湖南報社的肅反運動。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新湖南報立案審查的有十餘人,他們之中,像朱正、鍾叔河,在政治歷史上毫無問題。有些人有問題,例如許任飛,曾任國民黨軍方報紙桂林《掃蕩報》總編輯,後來又在重慶《大公報》任編輯;諶震曾任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主席劉建緒的秘書,掛過上校參議的頭銜;鄒今鐸原為新四軍,皖南事變中被俘,在上饒集中營關過。他們的這些問題都不是在肅反中查明,而是相反,都是因為自己早已交代了這些問題才被列為肅反對象。這十多個「老虎」被內查外調、檢舉坦白、批判鬥爭,折騰了大約一年。其中諶震、許任飛、俞潤泉三人還被宣布逮捕法辦,捉到看守所關了幾個月,到運動結束時才放回報社來。我還記得,每捉去一個,就把我們這些「老虎」領到寫了這事的黑板報前面(逐個帶去,每次一個),嚇唬一番:你得爭取時間,坦白交代,否則下一個就是你了!如此等等。這樣一年肅反運動的結果,報社並沒有肅出一個反革命分子來。這些「老虎」,包括「逮捕法辦」的三個,除了自殺和病死的以外,現在多已享受離休老幹部待遇了。
肅反運動的這種情況,並不是新湖南報社一處獨有的,其他單位的肅反也大同小異。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中提供了幾個數字,拿來計算一下,就可以知道這種情況是必然的了。社論說,在肅反運動中,「有一百三十多萬人弄清楚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問題」,這就是說,給一百三十多萬肅反對象寫出了並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換句話說,就是肅錯了的。而在定案材料中定為反革命分子的,社論說是「有八萬一千多名」。兩項相加,肅反對象共約一百四十多萬人。取整數以一百四十萬為分母,錯案率是百分之九十四強,每一個在運動結束時定案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個不能定案為反革命分子的肅反對象作陪。
這裡說的是全國的情況。至於新湖南報社的肅反運動弄得這樣一塌糊塗,還有一個特殊情況。那就是報社肅反五人小組組長是官健平,而他,正是毛澤東所說的那種「別有來歷」的人物。當時他是報社最高領導人,我們這些在下面的編輯記者無從知道他的底細。文化大革命開始,那時他當了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長。省委機關造反組織「永向東」去調查了那些「走資派」的情況,一查,可就不得了。「官健平何許人也?現已查明,他的姓名、年齡、籍貫都是假的,只有性別是真的。他曾是追隨『反共救國團』的得力幫兇,抓過農民領袖,打殺過共產黨人,後來又成為國民黨第四戰區游幹班特務中隊長的心腹,結業後又被提升為工作隊的分隊長。還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廣西一個中學任訓育主任時,結識了在該校當教師的地下黨員何大群。此時,他一方面秘密擔任國民黨湘桂鐵路特別黨部的監察委員,一方面又和我地下黨交往密切。日本投降後,他來到長沙,取得地下黨的信任,混入了黨內,並施展種種伎倆,迷惑上級領導,當上了地下工委書記。解放後,官健平對頂頭上司阿諛奉承,青雲直上,飛黃騰達。」(鄧鈞洪〈追記《新湖南報》的「反右」鬥爭〉,載上海《新聞記者》雜誌一九八九年第六期)這樣一個人,這樣一些經歷,豈不正是肅反運動應該審查處理的對象嗎?可是不成。他是五人小組組長,肅反運動正是由他主持,他當然不會把自己列入鬥爭對象。他需要的是轉移視線,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於是把那些主動交代了歷史上的某些問題的人作為對象,還湊不足數,再找一些歷史上毫無問題並且毫無疑點的人作為對象。這些人,自己本沒有什麼問題,或者沒有隱瞞什麼問題,卻被列為肅反對象,平白無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鬥,不免有些怨氣。整風運動開始,號召向領導提意見,於是好些肅反對象就把這問題提出來,要求「給一個說法」。
……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23 |
科學科普 |
$ 379 |
中國歷史 |
$ 422 |
中國歷史 |
$ 432 |
中國近代史 |
$ 43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
1957,丁酉年,一場對中國知識份子產生重大影響的「反右運動」正式展開了。
反右運動以糾出「右派」為目的,然而運動牽連日廣,被「錯劃」者不在少數。作者朱正身為新湖南報社的一員,也成了反右運動的親歷者,以見證人的身分,藉由親身經歷、友人事蹟和相關歷史論述的探討,重新還原反右運動的歷史現場,驚人的呈現出近一甲子之前,中國知識份子所面對的厄運。
作者簡介:
朱正,1931年生,中國湖南人。1957年在長沙新湖南報社親歷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長期蒐集相關史料文獻,撰有《兩家爭鳴》等作。
TOP
章節試閱
【丁酉年紀事】
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 ―― 辛棄疾〈沁園春〉
一
一九五七年,我在長沙新湖南報社,在這裡經歷了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全過程。
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我被列為鬥爭對象,在整整一年時間裡,享受了每一隻「老虎」都享受過的一切待遇:檢查交代,批判鬥爭,不必說了。最難受的是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時,從吃飯到拉屎,都有專人看管,比起後來我在看守所和勞改隊的經歷,都管得更嚴厲些。鬥了一年,沒有查出什麼反革命的材料。於是說我參加了一個「思想落後小集團」,以撤職...
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 ―― 辛棄疾〈沁園春〉
一
一九五七年,我在長沙新湖南報社,在這裡經歷了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全過程。
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我被列為鬥爭對象,在整整一年時間裡,享受了每一隻「老虎」都享受過的一切待遇:檢查交代,批判鬥爭,不必說了。最難受的是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時,從吃飯到拉屎,都有專人看管,比起後來我在看守所和勞改隊的經歷,都管得更嚴厲些。鬥了一年,沒有查出什麼反革命的材料。於是說我參加了一個「思想落後小集團」,以撤職...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前記】
可以說,我在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後,就開始了我對反右派鬥爭這一歷史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發表了研究的成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在這段時間裡,我不斷給它補充增訂,讓它從三、四十萬字增加到七、八十萬字。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了這部書稿,不久即將以《反右派鬥爭全史》這個新的書面推出。
在這些年裡,除了這部整本的書之外,我還寫了一些關於這個題目的長長短短的文章,有的是應報刊編者出了題目來約稿,有的是遇到了想寫的題目自動...
可以說,我在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後,就開始了我對反右派鬥爭這一歷史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發表了研究的成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在這段時間裡,我不斷給它補充增訂,讓它從三、四十萬字增加到七、八十萬字。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了這部書稿,不久即將以《反右派鬥爭全史》這個新的書面推出。
在這些年裡,除了這部整本的書之外,我還寫了一些關於這個題目的長長短短的文章,有的是應報刊編者出了題目來約稿,有的是遇到了想寫的題目自動...
»看全部
TOP
目錄
前記
【自述】
丁酉年紀事
我對反右起因的解釋
【懷人】
憶鳳翔
紀念朱純
讀《柏原流年》
藍翎,走好!
龔育之同志於我
我和公劉兄的兩面之緣
尋找一個精神的支柱――讀戴文葆兄的一個抄本
君子和而不同――紀念李慎之先生
舒蕪和我的《兩家爭鳴》
【論說】
在一九五七年之前
關於「陽謀」
一九五七: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
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
反右派鬥爭:歷史關節
從郭小川看反右派鬥爭
胡適和他的右派兒子胡思杜
士可殺不可辱――電影明星石揮之死
炎黃子孫不要...
【自述】
丁酉年紀事
我對反右起因的解釋
【懷人】
憶鳳翔
紀念朱純
讀《柏原流年》
藍翎,走好!
龔育之同志於我
我和公劉兄的兩面之緣
尋找一個精神的支柱――讀戴文葆兄的一個抄本
君子和而不同――紀念李慎之先生
舒蕪和我的《兩家爭鳴》
【論說】
在一九五七年之前
關於「陽謀」
一九五七: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
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
反右派鬥爭:歷史關節
從郭小川看反右派鬥爭
胡適和他的右派兒子胡思杜
士可殺不可辱――電影明星石揮之死
炎黃子孫不要...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朱正
- 出版社: 要有光 出版日期:2013-04-2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12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