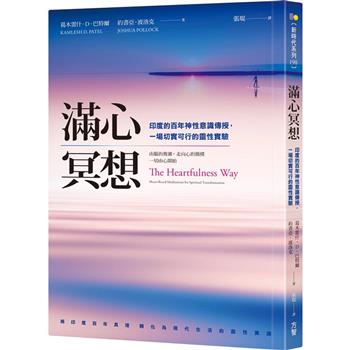不論是不是自己選擇的,面對孤獨都需要很多勇氣!
「如果他在這裡再多待一會,他會迷失,回不去因紐特人的國度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在這裡從來不曾覺得完全自在,更何況吶娃拉吶娃的靈永遠進入了他的骨髓裡,這是他一直都知道的。」
年輕的因紐特人尤利克離開了終年白雪的部落與他心愛的吶娃拉納娃,前往陌生的大都市,在時空和文化的衝擊下,他與幾位女子建立起意想不到的關係,但他仍感到巨大的寂寞和孤獨……他不斷地提醒自己,他的離開,為的是希望有機會重返吶娃拉吶娃的身邊……
越是生活在這裡,這裡的兩性關係越令他無法理解:女人似乎可以不要男人,而男人也不明白女人在想什麼。雖然雙方不斷用各種方法尋找另一半,也各自提出相處的條件,卻是各說各話似的難以獲得最大的公因數。他們外表看起來光鮮亮麗,但心理的本質卻是孤獨難語的。他困惑了,在這裡有這麼多的好女人,她們要如何才有辦法在茫茫的人海裡,找到「對的男人」?
「你們在男人和女人之間還有一個交換系統,我們呢?我們有一點失去了我們的交換系統。」
尤利克的新朋友—艾克拖醫生這麼告訴他,不過身為心理醫生的他也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迷失了方向。面對這些擁有自由之身的女人,男人如何能在唯一的女人身上停下來?他們又有辦法對屬於自己的那個女人維持忠誠嗎?
作者簡介
弗杭蘇瓦.樂洛赫 Francois Lelord
1953年6月22日出生於巴黎,精神科醫師及作家。求學時期主修醫學及精神科醫學,1985年獲博士學位後,前往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返國後始嘗試寫作,長踞各國暢銷書榜,全球發行超過百萬冊。
他善於以淺顯易懂的文字,經由寓言式的手法,為普羅大眾闡述精神醫學方面的主題,風格頗受《小王子》作者聖修伯里及伏爾泰的影響。目前受聘於亞蘭-卡本特基金會擔任精神科醫師,經常往返於巴黎及曼谷兩地。
譯者簡介
尉遲秀
一九六八年生於台北。曾任報社文化版記者、出版社文學線主編、輔大翻譯學研究所講師、政府駐外人員,現專事翻譯。譯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 書》、《雅克和他的主人》、《小說的藝術》、《無知》、《不朽》、《緩慢》、《生活在他方》、《相遇》、《戀酒事典》、《渴望之書》(合譯)等書。


 2013/05/25
2013/05/25 2013/05/23
2013/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