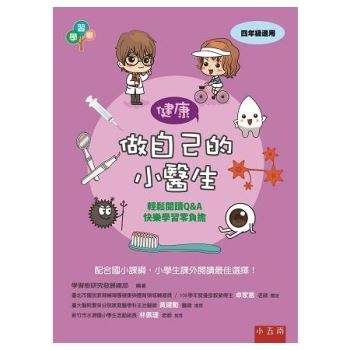1. 葉家
那時葉家還沒有敗落。三個兒子、三個媳婦、六個孫子女,都住在葉家的老房子裏。那是好大的一幢兩層樓房子,是戰前那種呈「品」字形的洋樓格局。最顯眼的是前面的門樓,上層為三面都是窗的一間方形前室,下層是騎樓;除了可以用作停泊汽車,也可以讓小孩在那裏遊戲,是所謂的「讓了三五尺地,卻多占了一份天」的那種精明而實惠的設計。葉家老房子門樓上層的那間前室,葉安平老先生用來做書房。每天傍晚時分,米鋪上了鋪以後,他回到家裏來,第一件事就是上樓直入他的私人書房。這時葉家的女人,葉老太太已為他備好茶,擺好瓜果、糕點。大多數的時候都會坐下來陪他說說話,也無非是家裏的一些瑣屑事,說完要出去之前,她總是對這葉家的一家之主說:「吃飯時我讓水晶來叫你。」水晶是葉家老三的女兒──個子瘦小,皮膚較暗,是那種淺黃帶褐的膚色;高鼻樑,小嘴巴,雙眼皮的一雙大眼睛,烏溜溜地轉;迎面跑過來,冷不防猝眼一瞥,還當以為是個混血的或者是馬來小女孩。葉家的孩子,也就只有水晶一個有如此的長相。
且說葉家老房子,因為是好大的一幢花園洋樓,圍在圍牆裏面不僅是一幢房子的占地,而是好大的一片園子,除了種些花花草草以外,還有兩棵紅毛丹樹與房子齊高,終年枝繁葉茂,樹影婆娑,幾乎遮蔽住了樓上三個房間窗前的天光。那一排而過的三扇窗戶,經常敞著,裏面卻一整天也沒動靜。偶爾一陣輕風掠過,窗簾也就隨風被掀起來了;只見簾上的花式圖案一點紅、一點黃地顫動著,似有無數的影子在那裏晃動,跑馬燈般地旋轉,但這種熱鬧隨著風一過就完全就靜止了,倒是樓下大廳和大門口樓前的騎樓是最熱鬧的。三個媳婦,光是孩子便生了六個:大媳婦一子一女,二媳婦二子一女,三媳婦也是一子一女。可三媳婦的那個男孩生下來不久便夭折了。雖說除了最小的水晶之外,全都上學了,但是五個孩子不可能全都在同一個時間上下課,總有一些是上上午班,一些是上下午班的,於是便有得好鬧的了;光是上樓下樓,蹬蹬蹬的腳步聲便終日地蹬個不停,沒一刻安寧。有時葉老先生在米鋪裏感到疲憊,想回家睡個午覺,歇息歇息一會,卻總不得一刻的安寧。每回都是這樣:當一踏入家門,他便禁不住要皺起眉頭──人生總有不盡如意的事情讓他皺眉:輕者是想午休一時片刻也未必能如願,重者則是他心頭上的那一樁事──雖說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但那終究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這陣子,葉安平葉老先生他開始意識到,他們葉家的經濟是大不如前了。首先是米鋪的生意,當然這也不全是因為對面新開張了一間米鋪所致,真正的原因是這陣子市道冷落,凡是做生意的都不見好景。米鋪是他一手一腳打理的,小兒子明量也只是幫頭幫尾,始終擔當不了重任。二兒子明泉、大兒子明弘倒都是精明能幹的經商之才:一個管理橡膠園,一個管理米較廠(即碾米廠)。毫無疑問,葉家在小城鎮上是有頭有臉的大戶。二十多年前就在這裏買了房,置了地;另外在鎮外,那一片一望無際的膠林,有四分之三是屬於葉家的。除了米較廠,也有些稻田,可都分身乏術沒法管理了,只好租給也是姓葉的鄉親,讓他們去耕種算了。可這些日子來,市道冷落,膠價也大不如前。於是,葉老先生就開始意識到,未來的日子是難以想像的。於是,這些日子以來「富貴不過三代」這句古老的諺語便一直縈繞在他的耳畔以及腦海裏,揮之不去……他是真正地領會到人生的不能掌握、世事的不可預測以及天命不可違的那種冥冥之中的安排……
2. 逃亡到南洋
葉老太太翻箱倒櫃,終於在箱底翻出一串佛珠,那是一串紫檀木的珠子,握在手裏,葉老太太很清晰地感覺到它的份量。這麼多年過去了,在歲月已然蒼老、往事煙消雲散的此時此刻,翻出這一串佛珠,她感到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思念的同時也領受到了另一種的情深意切,這是來自父母親的永遠也不能磨損的生命質感。在她嫁入葉家這幾十年歲月裏,葉老太太和丈夫共同生活了這麼多年,但是關於自己的過往,包括娘家的一切都沒有被再提起過。在她的內心深處,彷彿有著一種使命感般的堅守意識,要她把有關自己家族的一切過往隱藏在生命的背後。其實,也沒有人要求她這麼做,而是她自己不願意讓人知道他們家族的歷史,更認為這是她與她的家族共有的有秘密,因而產生了對自己家族的責任和使命感。
這一個下午,葉老太太在翻箱倒櫃好不容易翻出這一串檀木佛珠時,她的心情一下子地就變得陰暗起來;她用深情的目光來回檢視著手中的佛珠,同時記憶清晰地把父母親的形象在腦海中再進行一次更為深刻的細節領會:那時候她多年輕啊,可是只在一瞬間,她的臉上便出現了一種憂怨,眼神因游離而迷茫……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某個夜晚,父親從鎮上匆匆趕回家,一進門便令母親趕快收拾細軟,說要趕緊離開,否則就要出人命了!母親聽了頓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然後她忽然放聲大哭,此時她終於明白了:災禍終於降臨了。
在那個一九二七年的夏夜,天空中布滿烏雲,雷聲隆隆,轉眼間烏雲化作傾盆大雨。母親在雨聲中收拾細軟,男人把妻子認為非要帶上不可的家當用繩索捆綁成兩大包,迅速扔上停在門外的馬車上。再折回到屋裏,聽見妻子對十一歲的女兒說:「達娃,妳聽著,什麼都不要問,我們必須馬上走,逃命要緊。」全名為「達娃拉姆」的女兒睜著一雙大眼睛困惑地看著母親,她仍不斷地問:「為什麼呢?」女人的眼裏忽然噙了淚,她說:「我們這下是大禍臨頭了,妳明白嗎?是整家人!」達娃的臉頰刷地慘白了,然後兩眼噙滿淚水,卻極力強忍住沒有哭出聲來,她似懂非懂地拚命點著頭。男人在門外看見屋裏的那母女倆心裏頓然湧上一種如刀割般的疼痛,他痛苦地閉上眼睛,然後做了個深呼吸,他想:「當下我必須保持冷靜和敏銳的察覺力,否則……」是的,他必須相信,他的命中是具有遇險呈祥、化險為夷的好運氣和能量的,而實際上也的確如此。
男人在心裏不斷直呼著妻子的名字,此時,他的眉宇間仍可以隱隱地看得見有著一絲堅定的執拗。這在平時是輕易可見的,那是因為他對所謂「命運」之說,始終抱著不相信的態度,正如他不認為天機是不可以洩漏的那樣。
然而,世事難料,禍福更難預測。之前他怎料到會遭此厄運,且還連累妻子女兒?
他,札西頓珠,行年已五十,他將很快地老去,但是妻子還這麼年輕,要等她逐漸地老去,還有好長好長的一段歲月呢。而女兒達娃拉姆,正當花樣的年華,可愛得讓人心顫。因此,他更加不能相信命運,不能就此認輸!他想,這不過是上天跟他開玩笑罷了。即使是世事難以預料,也不可能是這樣的。是的,不可能的,那一定是上天跟他開玩笑了。
這樣想著,札西頓珠的焦慮,很快地被一種堅毅的鎮定替代了,他感到有一陣從未有過的從容──人生總得要有一些波折的。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遺夢之北:李憶莙長篇小說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29 |
文學小說 |
$ 332 |
小說 |
$ 332 |
現代小說 |
$ 333 |
小說/文學 |
$ 369 |
中文書 |
$ 370 |
小說 |
$ 378 |
現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遺夢之北:李憶莙長篇小說
喇嘛正當盛年,終日坐在寺裏很寂寞,有天來了個女孩,兩人竟然一見鍾情,盛年的精力爆發成強盛的情欲,拉了女孩便往青稞地裏去。喇嘛喘著大氣,女孩嬌羞地漲紅了臉,他們在藍天白雲和青稞芳香的圍繞之中好好地愛了一場。
水晶經常作同樣的一個夢,夢裏看見很長的布帷,一重重地圍著一張銅床,裏面坐著一個人,卻始終看不清那人的臉,可總聞到一種香氣,縈縈繞繞的……
作者簡介:
李憶莙
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祖籍海南省文昌市。現任大馬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
十八歲開始文學創作。作品以小說散文為主。曾主編《馬華文學》達十餘年之久。並主編《馬華文學大系》短篇小說一九六五至一九八零年卷。經常出任全國各項文學獎評審。
曾多次獲獎,包括首屆《馬來西亞優秀青年作家獎》、《雙福長篇小說》優秀獎、首屆新加坡《方修文學獎》散文首獎,二零一二年第十二屆《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獎》,以及《遺夢之北》獲評選為二零一二年亞洲週刊十大中文小說等。
發表於國內外報章雜誌的文學作品逾二百多萬言。已出版著作計有長篇小說《春秋流轉》、《鏡花三段》; 中短篇小說集《癡男怨女》;中短篇小說集《李憶莙文集》、《夢海之灘》、《女人》;散文集《去日苦多》、《漫不經心》、《城市人》、《地老天荒》、《歲月風流》、《大地紅塵》、《年華有聲》等。
章節試閱
1. 葉家
那時葉家還沒有敗落。三個兒子、三個媳婦、六個孫子女,都住在葉家的老房子裏。那是好大的一幢兩層樓房子,是戰前那種呈「品」字形的洋樓格局。最顯眼的是前面的門樓,上層為三面都是窗的一間方形前室,下層是騎樓;除了可以用作停泊汽車,也可以讓小孩在那裏遊戲,是所謂的「讓了三五尺地,卻多占了一份天」的那種精明而實惠的設計。葉家老房子門樓上層的那間前室,葉安平老先生用來做書房。每天傍晚時分,米鋪上了鋪以後,他回到家裏來,第一件事就是上樓直入他的私人書房。這時葉家的女人,葉老太太已為他備好茶,擺好瓜果、糕點...
那時葉家還沒有敗落。三個兒子、三個媳婦、六個孫子女,都住在葉家的老房子裏。那是好大的一幢兩層樓房子,是戰前那種呈「品」字形的洋樓格局。最顯眼的是前面的門樓,上層為三面都是窗的一間方形前室,下層是騎樓;除了可以用作停泊汽車,也可以讓小孩在那裏遊戲,是所謂的「讓了三五尺地,卻多占了一份天」的那種精明而實惠的設計。葉家老房子門樓上層的那間前室,葉安平老先生用來做書房。每天傍晚時分,米鋪上了鋪以後,他回到家裏來,第一件事就是上樓直入他的私人書房。這時葉家的女人,葉老太太已為他備好茶,擺好瓜果、糕點...
»看全部
作者序
感言之一
《遺夢之北》獲選二○一二年《亞洲週刊》十大中文小說,藉此再版的機會,說幾句話與讀者分享心情,也就是所謂的「感言」。
長久以來,我都有著這麼的一個想法:要寫一部關於馬來西亞的小說,要很細很細地描繪這塊被稱作「南洋」的州府地──這裏的人,這裏的事。並不僅僅因為這裏是我的家園,是我所生長的地方。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我對這裏的一切都特別有感受;我不僅熟悉她、愛她,還有許多說不出來的為什麼。但我卻能明確地知道,這些都關乎情感,關乎我內心深處的一小片溫暖的世界。總的一句:我對這裏特別有感情。
對於一個...
《遺夢之北》獲選二○一二年《亞洲週刊》十大中文小說,藉此再版的機會,說幾句話與讀者分享心情,也就是所謂的「感言」。
長久以來,我都有著這麼的一個想法:要寫一部關於馬來西亞的小說,要很細很細地描繪這塊被稱作「南洋」的州府地──這裏的人,這裏的事。並不僅僅因為這裏是我的家園,是我所生長的地方。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我對這裏的一切都特別有感受;我不僅熟悉她、愛她,還有許多說不出來的為什麼。但我卻能明確地知道,這些都關乎情感,關乎我內心深處的一小片溫暖的世界。總的一句:我對這裏特別有感情。
對於一個...
»看全部
目錄
目次
第一章
1. 葉家
2. 逃亡到南洋
3. 祖母
4. 兄弟
5. 懷雲
6. 母女
7. 分家
8. 化敵為友
9. 妯娌
10.出軌
11.雨中分手
第二章
1. 水晶
2. 離異
3. 姑姑
4. 檀木佛珠
5. 懷雲瘋了
6. 水靈
第三章
1. 新村一九六九
2. 林保海
3. 眾說紛紜
4. 陳佛然
5. 情愫
第四章
1. 酬神戲
2. 蓮花姑與阿蘭
3. 戲棚腳
4. 大伯公廟
5. 咫尺天涯
6. 阿蘭之死
7. 愛情
第五章
1. 銀花
2. 各有想法
3. 觀音娘娘的寶誕
4. 夢見阿蘭 ...
第一章
1. 葉家
2. 逃亡到南洋
3. 祖母
4. 兄弟
5. 懷雲
6. 母女
7. 分家
8. 化敵為友
9. 妯娌
10.出軌
11.雨中分手
第二章
1. 水晶
2. 離異
3. 姑姑
4. 檀木佛珠
5. 懷雲瘋了
6. 水靈
第三章
1. 新村一九六九
2. 林保海
3. 眾說紛紜
4. 陳佛然
5. 情愫
第四章
1. 酬神戲
2. 蓮花姑與阿蘭
3. 戲棚腳
4. 大伯公廟
5. 咫尺天涯
6. 阿蘭之死
7. 愛情
第五章
1. 銀花
2. 各有想法
3. 觀音娘娘的寶誕
4. 夢見阿蘭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憶莙
- 出版社: 要有光 出版日期:2013-06-05 ISBN/ISSN:978986895160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0頁 開數:16*23 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