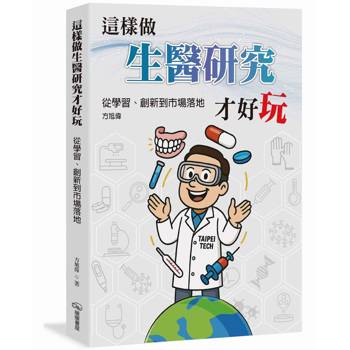魯一棄等人被迫踏浮冰從黑龍江順流而下來到海邊,按獵神狼天青的指示尋到魯家舊交——舵手步寸半,在他的帶領下,一行人駕船沿海岸南下尋「天、地、人」三才之一的地寶。船剛入海,即遭對家船隊圍追,一場海上船戰在所難免,魯家鐵頭叉尾桐木雙桅船如何才能在驚濤駭浪中殺出重圍;與此同時,魯天柳攜無字黃綾,橫穿太湖小島上千翎山百翎谷,破木八卦、過火靈橋、闖迷蹤村、解碾鬼磨、躍疊步巷,直奔五行水寶而去。待回頭時,谷澗山洪撲面而來……
本書特色
千煞之器,其器一出,
驚天動地,殺必成!
網路3:1高評比=每3個讀過的人中就有1人推薦
與《盜墓筆記》、《鬼吹燈》並稱「網路三大神作」!
總銷量逾50萬冊的機關暗器小說
千古難破的殺戮機關‧鬼斧神工的致命武器‧纏繞永世的絕命詛咒
機關暗器大全。故事嚴絲合縫,懸念百出,翻書都小心謹慎,生怕觸發了機關暗器……
新通俗小說。故事緊湊、驚險,懸念叢生,危機不斷,讓人欲罷不能,直到看完了,才能透一口長氣……
取材新穎。展現的是作者那瘋狂的想像力,表達的主題卻是「恐懼」……
網友推薦
故事的鋪陳十分引人入勝,原以為已經見到最終的結局,正要放下心來,下一刻卻又陷入了另一層的危機,讓人跟著作者的步調,一同進入書中的世界,也期待這一個故事,將會如何展開。——網友‧QAQ
氣氛鋪陳緊張刺激,內容用到大量的風水術語,並且夾雜著許多獨特的招式、機關,充分營造出神祕感!令人好奇之後的發展。——網友‧CAT
一部題材新穎、讓人大開眼界的小說!——網友‧judy
一個千年未破的難題,千百個精心巧置的機關,各有所長的挑戰者,組成一個精采絕倫的故事,等你來細細品味。——網友‧青春不老
讓我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懸疑小說迷們都會喜歡的一本書,看慣了遍地天馬行空的玄幻,突然感覺回歸了神祕和真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感覺和主人公一起尋找古老的使命,和機關暗器一起進入一個好玩刺激的世界。——網友‧辣手摧花
作者的用字綿密卻又不會讓人覺得艱澀難懂,劇情結構在峰迴路轉之間糾結之際又能柳暗花明,有些劇情更讓人驚嘆作者豐富的想像力。——網友‧娃娃茵
想必作者經長時間觀察與體認才有此著作,心思的細膩不亞於當年的魯班,「細燒密青磚」,雖然簡樸,但創作的心應該像「雨金剛」那樣神通廣大吧!——網友‧叮噹
跟著故事的主角一同冒險之餘,也跟著吸收各形各色的歷史知識,雖然其中穿插的部份的傳說以及佚事,但都開闊了我們的視野。——網友‧Soca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魯班的詛咒4:劫殺連環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46 |
驚悚/懸疑小說 |
$ 246 |
驚悚/懸疑小說 |
$ 25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魯班的詛咒4:劫殺連環局
內容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