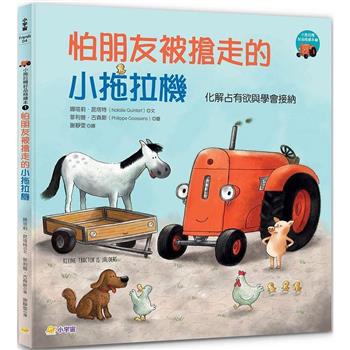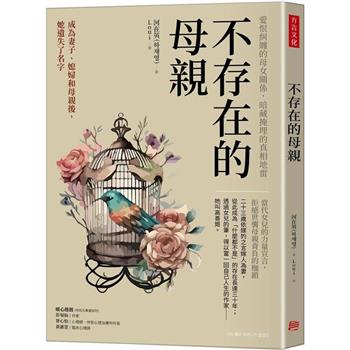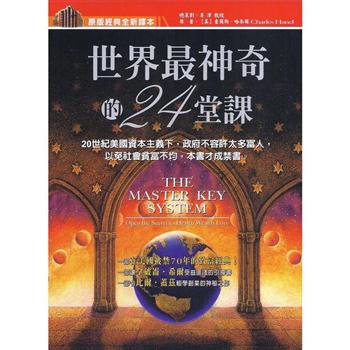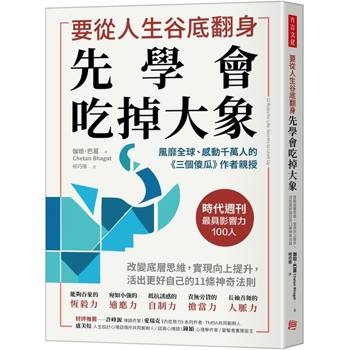第一章 雨點江南,墨汝點眉
清越年間是金陵的鼎盛時期,素有「十里秦淮」、「天朝金粉」之譽。兩岸飛簷漏窗,畫舫凌波,加之人文薈萃,成江南佳麗之地。
清越帝慕容雪弄下令,上元節在秦淮河上燃放小燈萬盞,華影璀璨。如今是斌朝定陶十六年,雖政局不穩,金陵繁華如舊。
這日正是上元夜,花市燈如晝。
一玄衣少年剪手立於河堤,月色如水,映出修長的眉、清雋的眼,有種清冷的雅致。他不過十二三歲,然眸光清冽,如沿劍鋒劃過的水滴,凝著隱約傲氣。
眼下的秦淮河碧陰陰的,厚而不膩,是女兒的胭脂所凝,香豔迷離。
少年脊背硬挺,身姿越發孤標卓然。這樣的紙醉金迷、濃酒笙歌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是天下的權柄!只有握了生殺大權,才有資格醉臥美人膝。
他是當朝四皇子―慕容雲寫。
江南是個富碩之地,那些人是想藉江南胭脂讓自己沉淪吧?
慕容雲寫細薄的唇,勾出冷嘲的弧度。
忽見華貴畫舫中一隻小舟穿行,舟約莫九尺長,六尺寬。舟頭是一個道者,大抵十五六歲,一身素白裏衣外披藍褐輕紗,頭戴逍遙巾,手反剪著卻不見傲然孤高,倒有一股恬然清氣,風骨靈秀,像幅清淡畫卷,一紙墨淺淺。
他一時恍惚,來江南這麼多日未見山水,卻在這一個人的身影裏看透風景。
江南風骨,天水成碧。
見道者一字的眉微蹙。
「若世間皆如江南,方為上善。」
他忽被打動,對黑暗中的人微一點頭。
舟上人在渡口停下,採買了日常所需,黑衣人走了過來。
「先生,我家爺有請。」
他體格魁梧,面容剛毅俊朗,眼透精光,顯然是個高手。
道者張口欲應,手被小童拉了拉。
「貧道於此處未有熟人。」
「我家爺歎先生所歎,故請一茶。」
道者似被觸動,對小童頷了頷首,隨黑衣人來到門前,湘竹門簾背後是窗戶。時天剛破曉,一線晨光透窗射入。
道者看見一個人側倚軟榻,清素雪衣,肩骨清標,長髮舒鬆委曳,身影慵慵地掃過天空。
或是聽到腳步聲,他仰起頭,脖頸頎長,形如孤鶴。
臉與過窗的光呈一線,道者恰可看到他側臉骨骼,似用最好的玉,刀雕劍琢而成。唇極薄致,如沾水桃花,瑩潤媚麗。
一時間自負風雅的道者竟也驚豔得忘了腳步。
要何等樣的人,才能如此完美地將雋傲與清嫵融於一身?
「先生請!」黑衣男人掀開竹簾。
「離昧來訪。」道者慎重地道,有種進少女閨閣的緊張。
榻上人攏了攏舒散的衣襟,起身斟茶,動作如行雲流水。遞了一杯給道者,見他慎重接過,盡情一飲。
「如何?」詢問,聲韻有梨花沾水的雅致,亦有劍破秋水的清銳。
道者瞑目細品,香馥如蘭,味甘而雋永,乃虎跑泉水煮的西湖龍井。
「醉人。」
「怕是人先醉吧!」
笑容玩味。
道者恍惚,他的笑竟似花落清流般令人心醉。果然是人已先醉了嗎?側首一吟,清笛入耳。
「醉臥紅塵一水間,這茶亦是紅塵一水。」
他斜倚窗前,笑意慵慵。手指沾了茶水在竹案上寫下:「雲寫」,一筆一畫瘦勁姿媚,端逸有格。
道者淺笑,也寫下:「貧道離昧」,行筆優柔婉妙,結字疏朗勻稱,穩重之中寓含飄逸。
兩人相視一笑,各盡盞中茶。
三年後,黔西,初春。
仲夏以來,地上便再未下過一滴雨,龜裂的土地、乾涸的池塘,冬麥、大豆等作物皆乾死,農民欲用淚澆灌,苦於眼中無水。孩子的唇乾裂,老人的皮膚脫下一層層細屑。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公子,這裏會有水嗎?」
深山老林裏,衣衫破爛的小童問前面的男子,他形容不雅卻沒一絲狼狽,眉宇斂含清氣,是道者離昧。
他原是北邙山一脈,俗家名喚段閱。父親是員外,信仰道教。小童子塵亦非出家弟子,是他撿的棄嬰,離昧八歲時二人同上北邙求道。
「書上記載涪陵水便是發源於這座香爐山。」離昧篤定道,拉著松樹向上爬。
子塵奄奄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並不是他不信離昧的話,只是找了這麼些日子,累了,小孩子難免會有些抱怨,且眼看著水只剩幾口,乾糧也要吃完了,更是急躁。
離昧道:「你看一路走來樹是不是越來越高大茂密?」
「是又怎麼樣?」
子塵趁機找個地方坐下來,他不明白公子這麼瘦的身子怎麼能走這麼久的路,他一個會功夫的人都累了。
「有水的地方樹木才能茂盛。我們按照此一直走,一定會找到的。」
子塵低聲咕噥:「就算找到,我們的乾糧也吃完了。你看這山裏連個鳥也沒有,我們吃什麼啊?」
離昧直視著他的眼睛:「鄉親們把最後兩壺水讓我們帶著,我們就這樣回去嗎?」
子塵低下頭:「可……可是……」
看到離昧的腳,鞋早破了,又用衣服裹起來,依然有血滲出來,染紅了他所站的土地。
「公子,我揹你吧!」
離昧笑笑拍拍他的頭:「你別拖我後腿就行了。走吧!」
向山上爬去。
「公子,你好歹歇息一會!」子塵痛惜。
離昧怎會不明白,艱澀道:「我們多耽誤一會,就會有更多人渴死。」
子塵只得跟上他。忽見離昧腳下一滑,順手巴住一塊石頭,哪想那石頭年久風化,竟一下裂開了,大大小小的石頭一起向他砸來。
「公子!」
子塵閃身過去,離昧已被石頭砸中,身子沿著陡峭的山坡往下滾。子塵幾個騰挪才拉住他,藉著一棵松樹避開石頭。
「公子,你沒事吧?」
離昧頭被石頭砸中,流了不少血,昏昏混混,聽子塵喚勉強睜開眼。子塵趕忙拿出隨身帶的藥替他止了血,將最後幾口水餵他。
「公子,我們還是回去吧!」
離昧喝了水稍有精神:「我剛才是怎麼了?」
子塵看了看他摔倒的地方:「你被青苔滑倒了。」
「什麼?」離昧眼神一亮,「你再說一遍?」
子塵不解:「你被石頭上的青苔滑倒了。」
離昧猛然推開他,如有神助般地跑到摔倒的地方,果見一塊青石覆滿青苔,青苔上還有一道滑痕。
「有青苔的地方肯定就有水。看!前面有個山洞!」
他們疾步向上爬去,果然青苔越來越厚,到洞口聽到裏面有水聲,二人一怔,接著不知哪來的力氣,拔足狂奔,直到一個水潭前!
離昧喉間一哽,張臂匍匐在水潭邊,憋噎半晌才驚叫:「有救了!有救了!我們找到水源了!子塵,我們找到水源了!」
子塵連捧幾捧喝了,猶覺不夠,「撲通」一聲跳到水潭裏,埋頭在水裏像老牛一樣大口大口地喝。不想喝得急了嗆住,一邊咳一邊還不停地往嘴裏灌,還不忘打手勢讓離昧快點喝水!
離昧拿出繩投入水底,撿根樹枝在地上寫寫畫畫一陣,眼睛清亮得如沁出的山泉水。
「以這個水量夠村子裏的人用了,沿著水脈開挖,至少可解方圓百里的憂患,快做好記號,我們這就回去告訴鄉親們好消息!」
「公子!你先喝口水啊……」
寂靜無人的山道,兩匹馬疾馳而過,馬蹄捲起一路黃塵。
山路曲折,下坡的拐彎處驀然出現一道木樁,尖銳的木頭正對馬頸!馬上人眸色一厲,一聲長嘯,但見兩馬四蹄踏風,縱身一躍,輕巧跳過木樁,穩當落地。
二人駐馬,只見兩旁皆是崇山峻嶺,地勢極為複雜。
「這裏已是黑峽寨的範圍。」
言者身著白衫,雖一路疾行衣袂不染點塵。聲音輕靈,細看竟是個著男裝的女子。
身旁黑衣男子會意:「洛陽唐證,拜會黑峽寨的各位好漢!」
他聲音雄渾,如驚雷在群山之間迴旋。
片刻山路上出現一隊人,為首之人書生裝扮,二十來歲,儒雅斯文,全不像土匪之流。
「原來是洛陽唐大俠,久聞大名,幸會!不知這位是何人?」
唐證道:「黑峽智囊徐夫子的名字唐某早有耳聞。」指著身邊女子,「此乃江南南宮楚。」
徐魏道:「黑峽寨何幸,竟得唐大俠與南宮公子同來?」
黑峽寨素未與江湖人往來,不知來意如何。
唐證開門見山:「為一筆大買賣。」閉口,卻有聲音直入徐魏耳中,「奪習水縣贓款。」
徐魏臉色一變,十指握成拳:「二位請隨我見大當家!」
黑風寨建在大山深處,極其隱蔽,山崖溝壑,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
徐魏直接帶他們來到密室,大當家張栓坐在虎皮椅上,身材高大雄壯,一臉絡緦鬍子,帶著大野莽漢的氣息。
徐魏道:「大當家,這兩位就是洛陽唐大俠、江南南宮公子。」
張栓一抱拳:「明人不說暗話,到底是一樁什麼買賣?」
唐證一字一頓道:「劫縣衙。」
張栓冷冷道:「徐先生,匪不與官鬥,這規矩你清楚吧?」
南宮楚摺扇一撒,笑意嫣然:「大當家不願做這單生意也成,只是半個月後,這兒連西北風也沒有了,兄弟們可喝什麼呢?」
張栓、徐魏臉色齊變!這人什麼來頭,竟將寨裏缺糧的消息都打聽得如此清楚?
南宮楚歎息:「可憐黔西一旱六個月,百姓餓死過半,貴寨就是藏了金山、銀山到這時也要吃空了。如今有這些貪官,不取白不取。」
張栓一拍桌子:「我是粗人,南宮公子有話直說!」
「朝廷知黔西大旱早已下發賑災糧款,然百姓依然餓死,錢糧全被貪官私吞。故請寨內兄弟取這些財,以黑吃黑,他們必不敢上報。」
張栓問:「搶誰?」
南宮楚道:「習水縣令張冒。」
張栓聽聞看向徐魏,只見他雖極力隱忍,臉上忍止不住抽搐,狠狠一拍桌子:「好!老子搶了!」
四人商議完行事計畫,南宮楚應邀留在山寨。唐證策馬回去,見行驛書房燈還亮著,敲門,聽裏面人許可推門而入。
青燈下,一玄衣男子伏案臨卷,雪白的臉微有倦色,薄唇輕抿,眉間一點朱砂像浸了血般紅豔―這人正是慕容雲寫。
「爺,一切均如所料,皆已辦妥了,只待後天行事。」
「嗯。」男子低應了聲,「做得乾淨點。」
「是!」唐證恭敬道。
見他放下筆,拍手命侍女打水來,悄然退下。
張家村,破舍。
「公子!你怎麼就起來了?你要多休息幾天!」
子塵進門看到離昧坐在破桌上寫字,急忙奪他的筆。
離昧信裝入信封中:「你隨我去一趟縣衙。」
「你去那個地方幹嘛?」提到縣衙子塵立時一臉憤恨。
離昧憂心道:「如果這樣取水,這個水源怕不久就會乾涸,而且還會因為搶水而出事故,需要縣衙維護開挖,這才是長久之計。哎……這乾旱何時才是個頭啊!」
「可是他們會理你嗎?你忘了上次……」
離昧打斷他,「這次已經找到水源了,他們總不至於見死不救吧?走!」
子塵又是氣惱又是歎息,知道勸不住,只能跟著他去了。
縣衙離鄉村很遠,他們到時差不多未時,可縣衙竟早早關門了。無奈只好來到縣令府中,向守衛的道明來意。那人上下打量了離昧一陣,露出一個令人十分不舒服的笑,伸出手。
子塵早窩了一肚子火,憤然要打他,離昧攔住,將一塊碎銀子遞給他。
守衛掂量掂量:「這還差不多。等著!」
不一會跟著一人出來。那人腦滿腸肥,八字眉,小小的眼睛,撚著兩根鬍子上上下下打量著離昧,對守衛說:「不錯!」
守衛對他點頭哈腰一陣,對離昧道:「這是我們師爺大人,你隨他去見老爺吧!」
離昧跟他進去,子塵隨後,卻被守衛一擋:「縣令府豈是容人隨便進的,你在外面等著。」
「你!」
子塵恨不得一腳將這人踹飛,被離昧擋住,眼見他隨那腦滿腸肥、不懷好意的人進去,又急又氣,恨恨得跺腳。
離昧只覺越走越偏僻,狐疑問:「施主,敢問這是何處?」
「自是接待你的地方!」
離昧聽他聲音,脊背一寒:「縣令大人可是在此處?」
「大人正忙,就由我來接待你。」
他看著離昧,兩隻眼睛幾乎瞇成一條線,搓著兩隻手向他靠近。
離昧退後一步,正色道:「施主,貧道此來是獻水源圖,開挖水源以救難民。請施主帶路,功德無量。」
「難民?哪來的難民?這兒水多著呢?只是像你這樣清秀的美人卻少。只要今兒你陪了爺,明兒我就請大人挖水,保你榮華富貴,享之不盡!」
離昧知對這等人多言無益,轉身就走,立時有幾個人攔住他,將他丟進房子裏。胖子關上門一步一步靠近。
「到了這兒你插翅也別想出去!」
離昧臉色鐵青:「貧道是男人!」
「爺就喜歡男人,你今兒就……」
步步逼進。離昧昂然而立,並未退縮,待他靠得近了,手一彈,一股霧氣升落,胖子搖搖昏過去。
此時窗戶輕吱一聲,子塵探進頭來,狠狠踹了胖子幾腳:「死豬!」
「好了!我們去找縣令。」
子塵啐一口:「那狗官正在聽歌舞呢!公子,這幫狗官都是一個樣,才不會管百姓的死活!去了也是白去,我們還是回去吧!」
「來都來了,不試一下怎麼行?」
「可是我們怎麼去呢?沒有人帶是不可能見到他的!硬闖也不行。不如這樣,公子你把信寫得恐怖一點,我用飛鏢放在他頭邊,這些人都怕死,說不定一嚇還真成功了呢!」
離昧輕斥:「胡鬧。你這一嚇我們還出得了這府嗎?你也看出這裏守衛很森嚴。」
子塵吐了吐舌:「那你說怎麼辦吧?」
這時忽聽門外有人叫:「師爺,大人叫你呢!」
兩人一驚,子塵趕忙學胖子的聲音將人擋回去。從窗戶出了房間,避開守衛來到一個房間,可聽見裏面絲竹歌舞,透過窗見一個肥肥胖胖的人坐在紅紅綠綠中間,就是縣令了。離昧就要過去,突然一個人叫:「有刺客!保護大人!」
接著就有箭向他們射來!幸好子塵反應靈敏,及時拉過他。
「貧道尋得水源,請大人救百姓!」
縣令一聽「刺客」臉都白了,結結巴巴:「殺!殺了!都給我殺了!」
箭接二連三射來,子塵拉著離昧左藏右躲甚是狼狽,不由憤恨:「你這狗官,那麼多百姓渴死了你不救,反倒隨便殺人!有沒有天理!」
眼見圍過來的人越來越多,抱著離昧一縱身跳到屋頂上,將他安置在角落裏,自己跳到廚房裏,尋找食用的油四散倒開,一把火燒著。
離昧從屋頂上看去,四周的衙役都向這裏集來,唯有一處巋然不動,心想必有異處;又見不少難民裝扮,卻並不面黃肌瘦的人向那裏靠近,好奇不已。
「公子,我們走!」
子塵抱著離昧突飛出去,還不忘將手裏信一扔,灌了內力的信像劍一般狠狠地刺到縣令的肩膀上。接著,他足點屋簷,幾個縱跳消失在夜空中。
大旱了這麼幾個月,房屋一點即著,衙衛哪裏還顧得著他二人,紛紛去救火,卻沒發現一隊難民裝扮的人悄悄靠近府庫。
遠處的高樓上,玄衣男子負手而立,見火起薄唇一抿,笑容冷涼。
「蕭滿,你以為將我驅出朝野我便奈何不了你嗎?」
忽見火光之中一個白影躍出,身姿輕逸,皎若滿月,不由一怔。
黑峽寨滿載而歸,看著一箱一箱的金銀珠寶,土匪們眼睛都紅了。
「兄弟們!我們發了!這些錢夠我們花幾輩子了!」
唐證長刀一橫,壓住銀箱:「大當家,這銀子你動不得!」
此話一出,四周殺氣凜凜!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獵帝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99 |
文學小說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85 |
其他武俠小說 |
$ 435 |
言情小說 |
$ 484 |
中文書 |
$ 484 |
武俠小說 |
$ 495 |
中國歷史小說 |
$ 495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550 |
歷史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獵帝
秦淮河初遇,離昧是雲遊道士,慕容雲寫是落魄皇子。
一句「男生女相,鳳生龍命」的讖言,將他們捲入龍鳳之疑、皇權之爭。
雲寫十八年隱忍,同室操戈,終於問鼎天下,
離昧追查身世,撥開重重迷霧,卻走上帝王寶座。
也曾盟誓造福蒼生;
也曾榻上魚水情濃;
也曾共遊醉臥紅塵。
當巔峰對決、挽弓獵帝時,可還記得,當年相約話酒桃花殿下?
作者簡介:
詩念,生於中原,客居江南。
拖著八零尾巴而來的小女子,癮著文字如同酒鬼癮著酒,願做文字的寄生蟲,寫他個半江書香,墨染風雨。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雨點江南,墨汝點眉
清越年間是金陵的鼎盛時期,素有「十里秦淮」、「天朝金粉」之譽。兩岸飛簷漏窗,畫舫凌波,加之人文薈萃,成江南佳麗之地。
清越帝慕容雪弄下令,上元節在秦淮河上燃放小燈萬盞,華影璀璨。如今是斌朝定陶十六年,雖政局不穩,金陵繁華如舊。
這日正是上元夜,花市燈如晝。
一玄衣少年剪手立於河堤,月色如水,映出修長的眉、清雋的眼,有種清冷的雅致。他不過十二三歲,然眸光清冽,如沿劍鋒劃過的水滴,凝著隱約傲氣。
眼下的秦淮河碧陰陰的,厚而不膩,是女兒的胭脂所凝,香豔迷離。
少年脊背硬挺,...
清越年間是金陵的鼎盛時期,素有「十里秦淮」、「天朝金粉」之譽。兩岸飛簷漏窗,畫舫凌波,加之人文薈萃,成江南佳麗之地。
清越帝慕容雪弄下令,上元節在秦淮河上燃放小燈萬盞,華影璀璨。如今是斌朝定陶十六年,雖政局不穩,金陵繁華如舊。
這日正是上元夜,花市燈如晝。
一玄衣少年剪手立於河堤,月色如水,映出修長的眉、清雋的眼,有種清冷的雅致。他不過十二三歲,然眸光清冽,如沿劍鋒劃過的水滴,凝著隱約傲氣。
眼下的秦淮河碧陰陰的,厚而不膩,是女兒的胭脂所凝,香豔迷離。
少年脊背硬挺,...
»看全部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雨點江南,墨汝點眉
第二章 情如洛水,梨花似夢
第三章 桃花浸酒,釀君風流
第四章 江南風骨,天水成碧
第五章 青衣西辭,素女鉤吻
第六章 有匪君子,新月堆雪
第七章 囹圄之災,生死一線
第八章 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第九章 重來回首,琵琶別抱
第十章 劍舞破陣,清刃含碧
第十一章 愛我所愛,牢獄洞房
第十二章 景致如畫,情濃似酒
第十三章 因愛生恨,牽機斷腸
第十四章 戰場重逢,刀兵相見
第十五章 烽煙遍地,白骨如霜
第十六章 堆雪長逝,愛恨情絕
第十七章 埋骨他鄉,英雄無淚
第十...
第一章 雨點江南,墨汝點眉
第二章 情如洛水,梨花似夢
第三章 桃花浸酒,釀君風流
第四章 江南風骨,天水成碧
第五章 青衣西辭,素女鉤吻
第六章 有匪君子,新月堆雪
第七章 囹圄之災,生死一線
第八章 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第九章 重來回首,琵琶別抱
第十章 劍舞破陣,清刃含碧
第十一章 愛我所愛,牢獄洞房
第十二章 景致如畫,情濃似酒
第十三章 因愛生恨,牽機斷腸
第十四章 戰場重逢,刀兵相見
第十五章 烽煙遍地,白骨如霜
第十六章 堆雪長逝,愛恨情絕
第十七章 埋骨他鄉,英雄無淚
第十...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詩念
- 出版社: 要有光 出版日期:2013-09-11 ISBN/ISSN:978986898524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30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武俠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