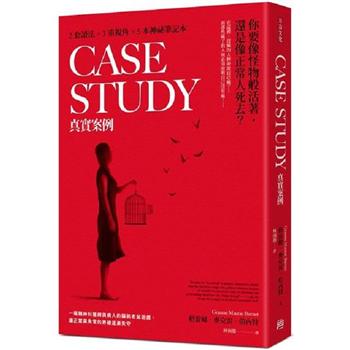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驀然發現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82 |
華文現代詩 |
$ 205 |
詩 |
$ 221 |
小說/文學 |
$ 228 |
中文書 |
$ 229 |
現代詩 |
$ 234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260 |
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驀然發現
碧果是語言世界的達利,卻是孤寂的先行者。他也是生命的禮讚家,以一雙巨眼金睛凝視著這世間,不,是這宇宙。他的身上混同的是少年的李金髮,老年的夏宇,以不苟同於所謂主流正派,躲在世界的一角不停地建構強化自身的生命力度,對文字充滿了叛逆敵對和不信任感,時時直覺的對生命和文字之「本不可穿透性」興起一種反彈和嘲弄,他的絕然凜然地出入實與幻的能力和耐力,比同世代的詩人走得都遠。
但他的確是樂於活在當下的人,懂得活在當下的人,當他以一雙火眼金睛瞪著人和事物時,絕對與之有「換魂」「交肉」(交換肉身)的力道和效果。
──詩人‧詩評(論)家白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