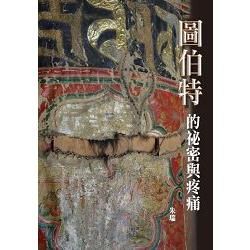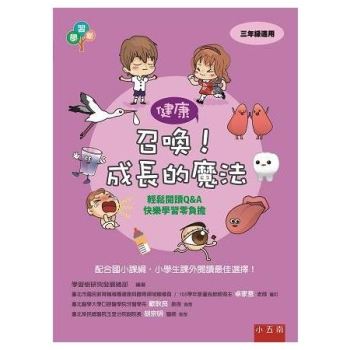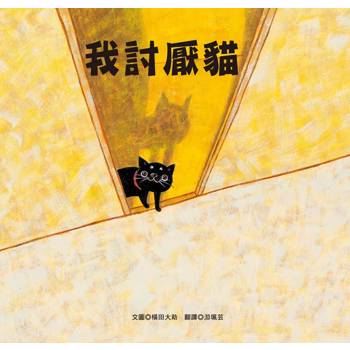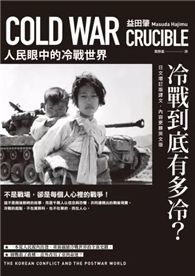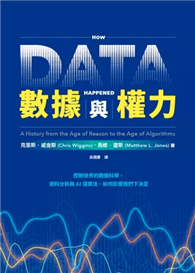贖罪
我從來就對強者不感興趣。這可能與我的基因密碼有點關係。小時候,看那些國產戰鬥影片時,愛看的總是國民黨軍官,儘管他們是失敗者,可我還是覺得,他們很好看,包括那身筆挺的軍服,也比共產黨那灰禿禿的衣服像樣兒;看剿匪片時,我愛看的也是土匪和他們的小老婆,並總想知道更多的關於土匪的真實生活,比如湘西那些土匪的往事,因為他們被共產黨殺得更慘。
初到圖伯特時,我也對「三大領主」產生了好奇,還特別去了江孜的帕拉莊園,看到帕拉用過的電話、羽毛球拍、鋼筆,以及他讀過的那麼多的佛學書籍,就感到,這是一位精神世界十分豐富的人。尤其是他年輕時那張氣宇軒昂的照片,與我所見到的一切漢人都不同。可能有人會不服氣了,問道:中國之大,就沒有一個如帕拉一樣的人?沒有,這是另一種氣質。
後來,我又與夏劄先生、朗頓班覺先生、恰巴先生、倫珠朗傑先生等圖伯特自由時期的貴族,都成了朋友。當然,他們並不完美,也有人類的弱點,不過,對善,都有著堅強的信心,也都有修行,過著一種道德的生活。他們的價值觀,與漢人的物質為上,完全不同。
在圖伯特,我的眼睛總是舒服的,包括我在鄉間旅行,比如快到桑耶渡口時,出現的那些土林,去敏珠林寺的路上,看到的那些碎石隆起的大山,讓我總覺得自己進入了另一個宇宙。尤其是人文景象,像寺院的壁畫:人可以長著許多隻眼睛,許多支手臂,許多隻頭顱,不僅如此,還可以飛翔,甚至一個鼻煙壺,一把藏鎖,都充滿了奧義。
於是,我放下以往的寫作題材,開始全心寫作圖伯特,以小說、詩、散文等多種形式,表達我這個中國人,對圖伯特文化的敬意。
後來,恰巴先生請我幫他寫回憶錄,當他談到1959年達賴喇嘛尊者出走,中國的大炮如何攻打拉薩, 甚至直接打到了羅布林卡噶廈辦公室裡,就從首席噶倫的寶座上方穿過,警衛喇嘛在屋裡當即死去……拉薩的大街小巷,如何堆滿了藏人的屍體,又如何拉到幾曲河邊燒掉,那焚燒屍體的氣味,一直在拉薩的空氣裡迂迴不散,……我簡直驚呆了,我從不知道,我們敬愛的解放軍叔叔,如此嗜血,這哪是對待自己的同胞啊!
再後來,我還看到了淪為殘垣斷壁的甘丹寺,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中,阿尼赤烈曲珍的被槍殺、木斯塘悲劇,以及一次次西藏人民抗議的失敗……失敗了,但沒有屈服。
我越來越感到,是中國侵略了這個國家,而一天比一天增多的中國移民,正在把我們平庸的價值觀,強加給他們,以我們的局限,否定人家的無限,把一切與我們的不同,都看成是落後的,包括宗教文化、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等,等等,有的是公開說出來了,有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我慶幸今生看到了圖伯特。離開了那個平面的、僵化的、功利的中國,包括那裡的學校教育,都在誘導著我們向強勢屈膝,使「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勢力哲學,千百年來,像腫瘤一樣,在中國人的精神裡不斷擴散,扼殺了他們對公義的基本感應。
我與圖伯特的關係,這時,顯然,已超越了對弱者的同情。說實話,自打一踏上圖伯特,我就踏實了,仿佛流浪的魂靈,找到了棲息的家,我只是一個被撫慰者、被保護者、被接納者。因此,很多藏人都說,我的前世也是一個藏人。也許吧,在我出生的「祖國」,我老是彆彆扭扭的。
不過,我的確是個中國人,至少這一世,是這個殖民利益鏈條上的一個恥辱,要麼,我怎麼可以如此大搖大擺地進入圖伯特呢?甚至比一切外國人都優越,比博巴——圖伯特的主人還優越,可以不被限制地走進西藏高原的任何一個角落!
如果可能,我還願意成為一個贖罪者。不僅表達我對圖伯特文化的敬意,還有我對圖伯特現實困境的感知,即中國入侵後,給圖伯特帶來的沒完沒了的災難。而這部《西藏的秘密與疼痛》,就是一次嘗試。
需要說明的是,隨著對圖伯特現代史的瞭解,我對國民黨也有了新的審視,其實,國民黨與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不過是五十步與百分之別,都極不誠實。比如杜撰「五族共和」、謊稱圖伯特代表「出席」了國民代表大會、謊稱吳忠信主持達賴喇嘛尊者登基典禮,並以護送九世班禪大師為名,派兵進入圖伯特……,只是因為,當時他們不具備足夠的力量,不敢像共產黨一樣全面佔領,當然,這是另外的話題了。
朱瑞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圖伯特的秘密與疼痛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圖伯特的秘密與疼痛
中國作家朱瑞以贖罪者之姿,用文字表達對西藏文化的敬意及對西藏現實困境的感知,即中國入侵後,給西藏帶來的沒完沒了的災難。而這部《西藏的秘密與疼痛》,就是一次嘗試。全書分人物、文化、殖民、燃燒紅色屠殺、被改寫的歷史等五類論述。
作者簡介:
朱瑞,漢人,小說作家。大部分作品以西藏為主題。著有詩集《秋天的情緒》、散文集《撩開神秘的面紗》、《傾聽西藏》、《境外西藏》,長篇政論文《略述達賴喇嘛尊者對西藏文化和人類的貢獻》,長篇歷史小說《拉薩好時光》等。現居加拿大。
TOP
作者序
贖罪
我從來就對強者不感興趣。這可能與我的基因密碼有點關係。小時候,看那些國產戰鬥影片時,愛看的總是國民黨軍官,儘管他們是失敗者,可我還是覺得,他們很好看,包括那身筆挺的軍服,也比共產黨那灰禿禿的衣服像樣兒;看剿匪片時,我愛看的也是土匪和他們的小老婆,並總想知道更多的關於土匪的真實生活,比如湘西那些土匪的往事,因為他們被共產黨殺得更慘。
初到圖伯特時,我也對「三大領主」產生了好奇,還特別去了江孜的帕拉莊園,看到帕拉用過的電話、羽毛球拍、鋼筆,以及他讀過的那麼多的佛學書籍,就感到,這是一位精神世界...
我從來就對強者不感興趣。這可能與我的基因密碼有點關係。小時候,看那些國產戰鬥影片時,愛看的總是國民黨軍官,儘管他們是失敗者,可我還是覺得,他們很好看,包括那身筆挺的軍服,也比共產黨那灰禿禿的衣服像樣兒;看剿匪片時,我愛看的也是土匪和他們的小老婆,並總想知道更多的關於土匪的真實生活,比如湘西那些土匪的往事,因為他們被共產黨殺得更慘。
初到圖伯特時,我也對「三大領主」產生了好奇,還特別去了江孜的帕拉莊園,看到帕拉用過的電話、羽毛球拍、鋼筆,以及他讀過的那麼多的佛學書籍,就感到,這是一位精神世界...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
人物
獅子法座上的達賴喇嘛尊者
阿嘉仁波切的一天
近距離的唯色
我見過沉默的波米仁波切
以一盞香燭,為朗頓‧班覺先生送行…...
她和流亡藏人共命運
索朗的死裡逃生
回避真相的「詩人」
想起第一次見到達賴喇嘛尊者的法像
與日本畫家井早智代相識
圖伯特的朋友:中原一博
文化
認知圖伯特
動物的天堂與地獄
中國人的二維視野和藏人的多維視野
談談所謂的「雙修」
阿尼格桑旺姆談佛學與科學
中國皇權與圖伯特佛法
醜,在替換美…...
沒有窮鄉僻壤的國度
殖民
在西藏,我們毀了多少「圓明園」?
中國民族政策...
人物
獅子法座上的達賴喇嘛尊者
阿嘉仁波切的一天
近距離的唯色
我見過沉默的波米仁波切
以一盞香燭,為朗頓‧班覺先生送行…...
她和流亡藏人共命運
索朗的死裡逃生
回避真相的「詩人」
想起第一次見到達賴喇嘛尊者的法像
與日本畫家井早智代相識
圖伯特的朋友:中原一博
文化
認知圖伯特
動物的天堂與地獄
中國人的二維視野和藏人的多維視野
談談所謂的「雙修」
阿尼格桑旺姆談佛學與科學
中國皇權與圖伯特佛法
醜,在替換美…...
沒有窮鄉僻壤的國度
殖民
在西藏,我們毀了多少「圓明園」?
中國民族政策...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朱瑞
- 出版社: 雪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10-08 ISBN/ISSN:978986898686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12頁 開數:15x21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