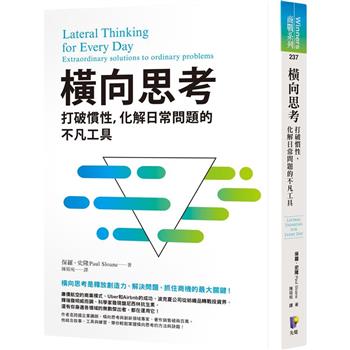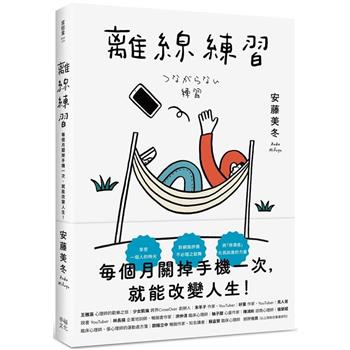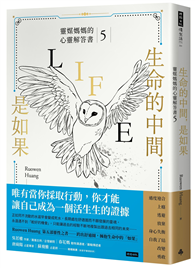我告訴自己,即便這個男人負了我這麼多
我所能仰仗指望的,還是只有他。
因此,我不能再如越王府中時般任性,他的心再虛渺,我也還是要抓住。
他說她會一輩子對她好,可一轉眼,他有六宮妃嬪如雲,將她推入深不見底的永巷,用深淵埋葬她傾盡一生的愛情。
他尋她三年,驀然回首,她已是帝王愛妃。他看著她的痛苦,她的掙扎,她隱忍不住的淚水,輕輕道,一切,我來為你了斷。
當一切得償所願,他擁她在懷,她卻已失了心,失了魂。誰能告訴他,愛情裡的機關算盡,到底是對還是錯!
那淩空一劍當胸刺來時,是誰的身軀擋在她的面前?是深宮鎖住了愛情,還是愛情困在了深宮?
當失去她時,六宮失色,天下無妃!
一個人的相貌給人的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然而當兩人在一起天長地久的廝守之後,卻才悵然發現,原來最不重要的,便是那外表了。
我的唇邊忍不住泛起一絲譏諷的笑,笑自己曾那樣自命不凡,而更無可救藥的,就是明知如此,我卻依然愛著他……
這個男人說會一輩子對她好,但一轉眼,他已六宮嬪妃如雲,置她的深情不顧。
另一個男人尋她三年,非卿不取,然而驀然回首,她已是帝王愛妃。
兩個男人,她究竟該愛誰?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後宮嬪妃風雲,熱烈上映中!
本書特色
角色性格鮮明,男主角為清新俊逸型,女主角為魅惑才女型。
劇情不僅限於深宮爭鬥,還有愛慕女主角者為爭奪女主角而鬥智的情節,極端緊湊,高潮迭起,是絕無冷場的精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