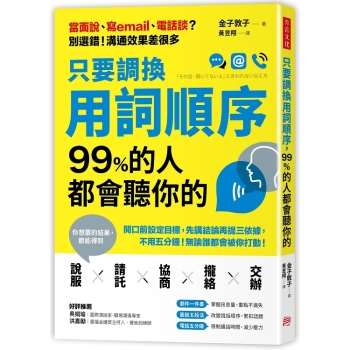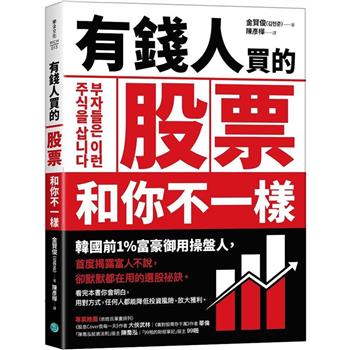掬一縷風的柔情
恍若昨日的一個夢境
在我南閣子的抽屜裡,躺著一疊藍墨水的稿子。
那靜靜的藍,鋪陳於淡黃色的信箋紙上,
似在訴說流水的光陰,懵懂的青春,和恬淡的歲月。
──〈藍墨水〉
這是一本紀錄無聲歲月的書
七年
寫曾經少女情懷總是詩
也寫為人妻 人母的愛戀
寫四季更迭
寫歲月靜好
亦是感謝 那些記憶中永遠美好的時光
本書特色
本書收錄多篇散文,寫舊日回憶、寫愛戀感動、寫旅途散記;
細膩而溫柔的文字,紀錄了一段最深情而動人的日子。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七年:愛戀生活札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31 |
華文創作 |
$ 290 |
大眾文學 |
$ 290 |
大眾文學 |
$ 297 |
華文愛情小說 |
$ 297 |
文學作品 |
$ 297 |
中文現代文學 |
電子書 |
$ 330 |
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七年:愛戀生活札記
內容簡介
目錄
第一輯:七年
七年
教堂
愛侶
拔牙
打針
哥哥
窗臺邊的水仙花
漂亮丫頭,傻老爸
壽司
郵局
油菜花
沿著綠道走一圈
婦人之衣
膩愛
牆內
童花頭
布鞋
第二輯:我的寶貝
水果糖
秘密
雨鞋
帳篷
芭比娃娃
奶油蛋糕
老姑娘
錢老師
佩佩
姑婆
故鄉
方言
寺廟
巧克力
八寶糖
雪糕
兒童節,兒童節
我的寶貝
第三輯:春光回憶
春光回憶
香水百合
梅花
霧
立春以後
曲奇餅,舊陶瓶
艾草
菖蒲
香囊
粽子
瓦罐
清明節
初夏時節
採桑果
寫在秋天的話
喝茶
妊娠紋
步雲橋
墓園
爺爺
第四輯:老照片
露天電影
初夏,光陰和女人
老照片
夏天的夢
怕黑
藍墨水
錦時
南方有小鎮
寂寞紫筍茶
荒村記
第五輯:雙城記
美麗的大麥塢
建德印象
長江遊記
婺源散記
雙城記
台灣散記
跋:在流水的時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