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憑什麼能聽懂鳥語〉
春天再次光顧笠帽山時,笠帽山的帽沿破了一個小窟窿。確切地說,窟窿是在山腰,從遠處看,剛好是從帽尖順勢而下宕開緩坡的位置。四五月份的皖南山區,綠色深濃得有點邪氣。這時候你若在山道上走,隨便望空抓一把,興許能揪一撮綠的精魂,再一揚手,興許它們又忽地一下遁形而去,枝上,葉上,起伏綿延,接地連天,綠汪汪、清潑潑,到處都有它們附身。如果是以前,笠帽山的風鑽過樹林掠過枝梢,你似乎能感覺那風腰身綿軟地在山坳裡轉圈,從帽子尖俯衝而下,又蛇一樣擦著坡面遊走、迴旋、轉向,所過之處,枝葉紛披,草木搖盪,伴著陣陣風嘯聲、松濤聲和近處的枝葉嘩啦啦的招展聲,笠帽山湧浪一樣跌宕起伏,呈現一種優雅深邃渾然一體的美。我說的這一切都是以前。
最早發現這個窟窿的是看山人沈老頭。兩個月前,他就瞧出了不對勁。那時山上還很冷,早上,他帶著呆頭在林子裡轉了一圈。呆頭是隻成年公狗,麻黑健壯,是沈老頭看山的忠實夥伴。呆頭其實一點兒也不呆,只是在牠還小的時候,和一群山喜鵲搶食吃差點被啄瞎眼睛,沈老頭一想起呆頭當時畏畏縮縮的熊樣就笑得直喘氣:真是呆頭!幾隻鳥就把你嚇成個癟三……呆頭似乎也沒什麼不高興,搖搖尾巴,不好意思地嗚嗚幾聲了事。這天早上呆頭異常警覺,一路狂奔上躥下跳,衝著對面的山腰汪汪汪大叫。沈老頭凝神細看,看到幾個陌生人在那裡指手畫腳。他帶著呆頭走過去,他怕有人打那些國外松的主意,那一棵棵勁拔拔棒小夥一樣的國外松已有碗口粗細,正是成材的時候,被人盜伐他可擔待不起。後來鎮裡有個管事的告訴他,笠帽山的礦石資源富得冒油,這裡馬上就要熱鬧了。
沈老頭每天瞅著那道坡,瞅了一段日子卻絲毫不見動靜。兩個月後,它忽然一夜間就被開掉了一片綠林,露出了一塊小窟窿。那是一個難看的窟窿眼,揭掉綠皮,黃色的新土裸露出來,像露出骨肉的傷疤。笠帽山的風飄著盪著,走著飛著,到那裡似乎就踉蹌起來,就阻住了滯住了,毫無防備地跌個跟頭,又踉蹌地爬起來繼續飛,平白地就減了風勢和風姿。沈老頭愣愣地盯著窟窿看,好像那傷口在吸著涼氣嗞嗞地喊疼——被風吹得疼。好好的山,要廢掉了。他喃喃自語,回到簡陋的小土屋,像往常一樣端出一碗冷飯餵鳥。
他提一口氣,嘬起嘴朝林子深處呼喚:嘓——嘓嘓嘓——,瞬間,林子裡響起一片撲喇撲喇的搧翅聲,一群灰喜鵲喳喳叫著飛撲而來,圍著沈老頭上下翻飛。沈老頭抓一把飯粒往空一撒,嘴裡念叨:小東西們,吃吧吃吧,蟲子吃不飽要吃飯啦!鳥們收起翅膀棲落地面,爭先恐後低下黑色的小腦袋,啄食沈老頭為牠們準備的口糧。呆頭站在沈老頭身邊涎著舌頭喘著熱氣,安靜地看著鳥們啄食。沈老頭蹲下身,他聽著鳥們滿足的喳喳叫聲,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來,眉眼慈祥,像個疼孫子的老爺爺。
林子裡的鳥是沈老頭的伴兒。有人說,笠帽山是這個城市深藏的最後一片淨土,離城區遠,交通閉塞,由此帶來的好處是山好水好空氣好。有林就有鳥,除了沈老頭,沒有人知道笠帽山有多少種鳥,畫眉、烏鴉、煤山雀、黑卷尾、黃鸝、灰喜鵲、毛腳燕,還有一些連沈老頭自己也叫不出名字的鳥,他就根據牠們的叫聲和毛色來區分命名,白胸脯的叫白脯雀,花尾巴的就叫花尾雀,反正,牠們都是雀子。遠離城市的笠帽山寧靜得像清晨的山霧,沒有塵世紛擾,能聽得見山中歲月晨昏流轉的腳步聲,太陽從林中升,又從林中落。似乎是孤單的,但沈老頭習慣了這種孤單,況且,聽聽鳥語和狗吠,陪著草木生死榮枯,伴著樹葉回黃轉綠,就這樣寧靜地打發掉一生中最後的時光,似乎也是一件享福的事情。
但是眼看沈老頭的願望要落空了。隔不幾天,沈老頭發現那個小窟窿旁多了一所小房子,是就地放倒一片國外松,找一些磚石土坯簡易搭建的。再後來,小房子頭頂冒出裊裊的煙來,他明白那裡是住了人。他帶著呆頭巡山時去探虛實,是午後時分,小房子門開著,裡面坐著兩個男人,睡著一個男人。一個坐著的男人胳膊上紋了蝙蝠,嘴上吊著煙,對他不冷不熱地喂了一聲,也許壓根看不上他這個看山老頭。以沈老頭的閱歷判斷,他們是常年在外跑碼頭的生意人。沈老頭後來證實了自己的判斷,還是上回那個管事的人告訴他,這撥人在外省同時開著好幾家礦山,這幾天他們先頭部隊在這裡做些準備工作,等一些大型開採設備進山。一直要開到什麼時候?沈老頭謹慎地問。這還早著哪。管事的回答。
沈老頭的日子便平白地不安起來,他總覺得會發生點什麼。這座山,他坐在門前想,恐怕就要完蛋了。那時候,他一把老骨頭不知道會埋在哪裡,鳥們又去哪裡,呆頭又去哪裡。他覺得有時候鳥比人可靠,起碼鳥有什麼說什麼,不會騙人,他相信鳥的語言。春天裡鳥雀們發情,叫聲婉轉動聽,唧哩滴哩,水流一般,樹葉彷彿都洗得青了又青;看到詭祕爬樹的蛇,鳥們的叫聲是短促惶恐的,嘎嘎唧唧,單調地重複簡單的音節,沈老頭就曾在這樣的提醒聲中發現了蓄謀向他進攻的赤練蛇;還有燕雀的聲音,像水哨一樣成串往外迸,濺起一個個浮起的水泡,也許是牠在熱情地邀伴;毛腳燕的聲音很單薄,細聽像秋天的蛐蛐唱歌,說不定牠就是閒了在練唱;竹雞的聲音嘹亮清脆,聽上去像誰捧起一把把山泉往外撒,唔,那是牠在求偶了……沈老頭在山上生活了十幾年,從早到晚聽的都是鳥語。住在深山他不覺得孤清,沒有鳥叫他才會覺得日子有多寂寞。
林子裡的黃昏來得格外早。沒有任何預兆地,林子裡驚起一陣鳥的聒噪,彷彿平靜的湖面猛地沸騰了一鍋水。沈老頭記得好長時間林子裡都沒有這種驚魂未定的鳥雜訊了。他守了近二十年的山,日子相安無事,自從看到那個窟窿眼,他就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宿命感,也許是老了,安定的日子要到頭了。呆頭早已嗚嗚囂叫著衝出去,沈老頭彎腰撿起牆角的砍刀跨出門去,多年前他見過這山上有狼,有狐狸,還見過一隻渾身長刺的野豬,難道說是狼或狐狸逮著了雀子?
鳥們還在聒噪,呆頭垂下尾巴伸長脖子,警覺地汪汪狂吠。沈老頭放眼看去,林子深處水波不興,風在吹,隱隱能聽見一陣一陣的松濤聲細浪般滾過。他用眼睛四處探尋,林子像一潭深水,或者就如一片深邃的海,生出幾分神祕感,掩蓋了水底的動靜。他百惑不解地抬起頭問樹上的鳥:叫什麼叫?怎麼了?引起委屈的鳥們一陣更緊密的聒噪。
眼下,牠們需要撫慰。嘓嘓嘓——他柔聲喚孩子一樣招呼牠們。呼喇喇一陣搧翅,一群鳥棲落地面。他一揚手,撒出一把飯粒,又一揚手,又是一把飯粒。一隻後頸黑亮、天藍色長尾巴的灰喜鵲撲一聲飛到他跟前,張嘴啄他手上的飯粒。小喜子!調皮!他輕聲喝斥。就在這時,林子深處傳來一聲短促的悶響,呯——彷彿一顆石子投進了湖水。沈老頭心裡一凜,槍聲,他聽到的分明是槍聲。很多年以前,那時他是一個出色的獵人,他曾背著獵槍在山野出沒,這種短促俐落的聲音他熟悉得像自己噴出的飽嗝。鳥們呼啦一聲散開,飛上枝頭戰戰兢兢地伸長脖頸張望,一隻灰喜鵲張惶地喳——喳長鳴數聲,其他的灰喜鵲隨即附和著鳴叫。沈老頭點點頭說我知道了,我真的知道了。
他領著呆頭向槍聲的方向走。他穿過樹林,樹木擦著他的身子,國外松和杉木長得很高了,密匝匝地,看不到頭頂的天空。呆頭一路小跑,突突地噴著鼻息,沈老頭把牠招到跟前,拍拍牠油黑光滑的皮毛,示意牠安靜。呯——幾十公尺外又是一聲槍響,他和呆頭快速衝過去,一個手持獵槍的男人從不遠的密林深處站起身。在一叢蒿草旁,沈老頭看見了尾隨而來、此刻中槍栽落的小喜子。他拾起小喜子,牠羽毛凌亂,眼皮垂下,子彈從牠胸膛穿過,一道鳥血從槍眼流出,染紅了牠胸前的灰白羽毛。
呆頭狂吠起來,向持槍男人猛撲過去。男人端起獵槍,呯呯又是兩聲。呆頭嗷嗷慘叫,倒在地上掙扎。沈老頭緊繃著嘴脣,死死盯著那個男人,他怕一不小心喉嚨裡就有血和火往外噴。持槍男人向他伸出手,討要他的戰利品。一隻蝙蝠紋身在他胳膊上面目猙獰,這個來挖礦的不速之客,從見他第一面起,沈老頭就死死記住了他的樣子。沈老頭攥緊小喜子,從牙縫裡迸出幾個字:你不是人!鳥都說你們不是人!
蝙蝠男人大笑起來,眼淚都快出來了:真沒見過你這麼有趣的老頭,你說的什麼鳥語?鳥都說?鳥告訴你的?你聽得懂鳥語?我怎麼就沒聽見?!
沈老頭低吼一聲:你憑什麼能聽懂鳥語?你不配!!他感覺心裡巨大的痛感衝撞著他,像風吹過笠帽山的傷口。他拚盡全力,提著砍刀衝過去……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張詩群散文集:初夏的圖書 |
 |
張詩群散文集:初夏 作者:張詩群 出版社:龍視界 出版日期:2014-02-1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66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8 |
文學 |
$ 304 |
現代散文 |
$ 304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張詩群散文集:初夏
綠苔痕
舊時光
胭脂紅
斑駁影
文字清麗唯美,如江南流水,於美中透出理性思辨的光芒。
江南女子張詩群,文字清麗唯美,哀婉沉涼,如江南流水,在石拱橋下低聲潺湲,絮絮訴說著舊日纏綿,卻又能濾去感性氾濫的浮沫,於情美中現出理性思辨的光芒。本書收錄張詩群關於人生體悟、自然歲時抒懷的清新散文創作。
作者簡介:
張詩群,女,祖籍湖北,生於江南。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蕪湖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已出版文集《陌上清歌》、《相思樹上合歡枝——李商隱的詩歌人生》、《浮生六記——浮生與溫暖》、《在最好的年華遇見你——他們曾這樣相愛》、五人合集《有一種胸懷叫大氣》等,有多篇作品被轉載或收入各種文選。
章節試閱
〈你憑什麼能聽懂鳥語〉
春天再次光顧笠帽山時,笠帽山的帽沿破了一個小窟窿。確切地說,窟窿是在山腰,從遠處看,剛好是從帽尖順勢而下宕開緩坡的位置。四五月份的皖南山區,綠色深濃得有點邪氣。這時候你若在山道上走,隨便望空抓一把,興許能揪一撮綠的精魂,再一揚手,興許它們又忽地一下遁形而去,枝上,葉上,起伏綿延,接地連天,綠汪汪、清潑潑,到處都有它們附身。如果是以前,笠帽山的風鑽過樹林掠過枝梢,你似乎能感覺那風腰身綿軟地在山坳裡轉圈,從帽子尖俯衝而下,又蛇一樣擦著坡面遊走、迴旋、轉向,所過之處,枝葉紛...
春天再次光顧笠帽山時,笠帽山的帽沿破了一個小窟窿。確切地說,窟窿是在山腰,從遠處看,剛好是從帽尖順勢而下宕開緩坡的位置。四五月份的皖南山區,綠色深濃得有點邪氣。這時候你若在山道上走,隨便望空抓一把,興許能揪一撮綠的精魂,再一揚手,興許它們又忽地一下遁形而去,枝上,葉上,起伏綿延,接地連天,綠汪汪、清潑潑,到處都有它們附身。如果是以前,笠帽山的風鑽過樹林掠過枝梢,你似乎能感覺那風腰身綿軟地在山坳裡轉圈,從帽子尖俯衝而下,又蛇一樣擦著坡面遊走、迴旋、轉向,所過之處,枝葉紛...
»看全部
目錄
一、綠苔痕
1、你的春天有沒有長大
2、初夏
3、土
4、親愛的民歌
5、遠去的渡口
6、你憑什麼能聽懂鳥語
7、有些路是溫暖的河流
8、醒著的暗夜
9、依稀採蓮
10、大浦,許多夢開花了
11、馬仁山,你在夢誰?
12、一城靈秀在江岸
13、城事
14、溪邊風物已春分
15、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
二、舊時光
16、明月曾照彩雲歸
17、那個松林般沉鬱的人
18、慈親倚門望,不見萱草花
19、生命因你而豐盈
20、看見花開
21、記得當年年紀小
22、歲月溫厚
23、入川
24、走到哪裡都是生活
25、那些老柿子
26、又是一年蘭花白...
1、你的春天有沒有長大
2、初夏
3、土
4、親愛的民歌
5、遠去的渡口
6、你憑什麼能聽懂鳥語
7、有些路是溫暖的河流
8、醒著的暗夜
9、依稀採蓮
10、大浦,許多夢開花了
11、馬仁山,你在夢誰?
12、一城靈秀在江岸
13、城事
14、溪邊風物已春分
15、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
二、舊時光
16、明月曾照彩雲歸
17、那個松林般沉鬱的人
18、慈親倚門望,不見萱草花
19、生命因你而豐盈
20、看見花開
21、記得當年年紀小
22、歲月溫厚
23、入川
24、走到哪裡都是生活
25、那些老柿子
26、又是一年蘭花白...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詩群
- 出版社: 龍視界 出版日期:2014-02-11 ISBN/ISSN:978986901009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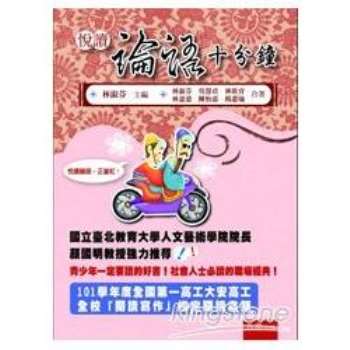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