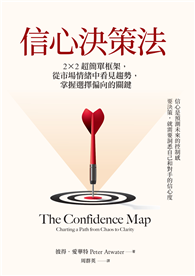億萬光年間,在地上的是微塵,發生在微塵中的一切,沒有重量。
有沒有一種愛,是沒有重量的?
他和她是經歷了很多輕輕的戀人和戀人的身體才走在一起的。七年後,她第一次感到愛的重量。愛與身體愛的糾纏,身體不再愛,還能愛嗎?她出走到太空,在無始無終的時空飄蕩,與似曾相識的他遇上。無重的空間,無重的身體,便能無重地愛嗎?
「有沒有一種愛,是沒有重量的?」這是《無重紀》所蘊含的問題意識,那是一句疑惑,也是一聲嘆息。
在葉飛的小說裡,經常沒有明確的時空背景描寫,她的文字總是更在意人心裡的暗湧,那些我們即使意識到卻也不願、不忍揭開探看的黑暗深處。《無重紀》走進了愛與慾望交纏的幽微角落。
關於追尋愛情的歷程中,我們總是墜落進去的,那往往是個意外,出乎我們的預期,愛情的書寫即是描述墜落的經驗。墜落的引力往往來自原欲的渴求。
人與人之間彼此交纏的肉體慾望,像是一波又一波復返的浪濤,瞬間將我們帶向高潮狂喜的峰頂,又旋即讓你失速墜落至低盪谷底,那股強烈的、不知所為何來的衝動與失落,有時與熱切愛戀下的兩人渴望融為一體的感受彼此排斥。愛裡總是無理可循,自相矛盾。
《無重紀》中的她出走到太空,太空是實質意義上的無重,在綿延無邊的宇宙裡,在寸草不生的洪荒星球上,我們脫離萬有引力的束縛,飄盪在失去上下界線的空間之中,由物質世界乃至於精神層次,擁有無重的身體是不是意味著能夠擁有無重的愛情?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想像,在葉飛的文字裡,時間與空間似乎是抽離的,我們見不到太多科幻細節的描述,《無重紀》寫的仍舊是人們無解的愛戀關係,我們只能在有限裡尋找無限,在束縛裡尋找解脫,我們的靈魂寄宿在肉體之中,在一隅之地裡探索精神世界的無底深淵。
在墜落中想像無重,在絕望中懷抱希望。
作者簡介:
愛電影,愛文字,喜歡埋頭埋腦做喜歡的事情,在心流裡蕩,不然會覺得好無聊。
跟林峰毅成立飛文工作室,希望文字,影像自由。
著有小說《愛流離》和《4個葬禮與快樂時光》。
繪者簡介
王君宇
台灣台南人。有份正當的工作但不務正業的部份做得比較好,甚至還比較有點成就感。開始拍照的時間已不可考,但記得國小照片就曾登上校刊。喜歡街景、行人,還有觀察人的行為。對我而言底片或數位都很好,但終究還是愛底片比較多。
林峰毅
屏東人,現於台北一帶遊蕩,從事視覺藝術創作與設計工作。與葉飛成立飛文工作室,著有小說《劍客的接待》。
Alan Kai
居於台灣的自由攝影師,對影像的記憶始於小學不能立刻顯影的傻瓜相機,八年前開始拍攝底片,五年前開始有意識創作,喜歡探索一些小事,並愛上由小事組成的生活。
章節試閱
序章:夢
未來。某時某地。
不是末日世代,城市一樣籠罩著濃濃的末日氣息,無過去,無現在,無未來,那是活在當下的意思。
這一年,鬱悶煩躁的城市,出現了一連串戀人莫名消失事件。消失者過了一段時間再回來,對消失期間經歷過什麼,出現或輕或重的失憶症。其中有些是永久消失的,更無從對証。
消失者回來後,他們的身體沒有什麼變化,但心理年齡卻顯著衰老了,呈現不同程度的健忘症,並不時出現虛浮暈眩的感覺,加上消失者身邊人出現不同程度的狂躁抑鬱症,不甘,失落等等,一一統稱為莫名消失症候群。當然有不少人也不當一回事,戀人無聲消失是日常不過的情節,用不著呼天搶地。
夏哲是其中一名莫名消失者。
她一年前消失,一年後又無事人般回來。回來第一夜,她若無其事的在丈夫林大維身邊深沉的睡,一切仿似如常。仿似天荒地老的一對。
認識他沒多久,她便每夜躺在他身邊睡。算起來,接近2000多個夜了吧,很長很長的一次愛戀,不可思議地跟他分享了接近1/5的人生。
那2000多個夜之間,是有一個空隙的,對林大維來說,一個不明所以又痛苦非常的空隙,空出了365天,他記得清清楚楚。
因為夏哲消失那天是一個除夕夜,再出現時已是下一個除夕夜,所以如何不記得細節的他都不能忘記,那又傷又痛的365天。
一個深夜, 他回到家,她睡在床上,跟他說了一聲,「你回來啦。」然後又睡過去。
她若無其事的,如剛巧出去什麼地方買了些什麼,又回來了,不過一眨眼間的事兒,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聲音平淡地,表情平淡地,自然得,如他365天加上思前想後的傷都不過是,幻覺。
看到她,他突然忘記了她365天的殘酷。他走上前去緊緊的抱著她,什麼話也沒說,然後,又激烈又溫柔地吻遍她全身。整個情緒激動的過程,她也沒有抗拒,不太激情也不太冷漠,微溫的。
那種激情讓他吃了一驚,他有那麼愛她嗎?他的恨意跑到那裡去了?過去365天的夜,他上過數不清的女人,仿似要把恨意逐天從身體驅逐出去,不然會屈死的。
在滲著單身男人和精液和愛液的氣味的床上愛,她一直閉著氣不去呼吸,直至快透不過氣來,她才張大口透氣。所以她一直愛一直喘著氣,身體也變得熱起來。那是妒意的作用?還是閉氣所得出的結果?
愛後,二人又一起在床上睡過去。二人弓著身,她背向他,他從後緊緊的抱著她,如不讓她再離去。他有那麼愛她嗎?
二人大概又會天荒地老地每夜睡在一起。或許,就讓身體偶爾出去浪。那是成熟與蒼涼與面對現實。
從來便沒有一生一世的愛戀,何苦苦苦的縛住身體讓愛的幻覺長存。一生一世的愛戀,只有愛自己。
他抱著她,半睡半醒的,問道:「這一年,去了那裡?」
她一樣恍恍惚惚的,說道:「一年嗎?」便又睡過去。
他沒再問,她也沒再說。
有些隱隱感到傷人的事情,掉進空洞裡便算了。那是兩個人走下去的默契,如霧裡看花,太清晰便傷人,太清醒便自傷。僻如他在一個個女體身上消耗掉的一個個夜。
她曾經問過:一個身體怎可以滿足各種各樣的慾望?
他說道:愛更重要啊。
抱著她,又愛起來。他在她的身體裡,痛苦的快樂游遍身體,她出神地呢喃:是愛先流失還是慾望?
他們約會的第一天便在床上愛,她曾經想:他愛我的身體還是我?七年之後,她知道他是愛她的,在變得疏落的身體愛之間,她再沒有疑惑。
清晨,他先醒過來,拉開厚重的窗簾,讓陽光透進來。他太久沒有在家中看到陽光了,那些浪蕩而糜爛的暗夜。
濛濛的陽光灑在她裸裎的身體上。她的身體還是那樣的美,他想,我是先愛上她的身體還是她?
她好像還是她,但又有什麼說不上來的轉變。怎麼說呢?
是了,她的憂悒變得稀薄了。
過去一年,她究竟去了那裡?
睡在床上的夏哲,由得林大維的眼光游遍自己的身體,一切仿如以前一樣。但身體裡有什麼感覺不一樣了?
她去了一個地方,感覺如一夜之間有什麼決定性的,無可挽救地改變了。一夜之間,她感覺自己蒼老了幾十歲,而身體卻一樣諷刺地美麗。
她去了一個地方,一切輕如烟,一切在飄浮,沒有觸地的沉重。
在那裡,她遇上她的無重情人,凌子軒。經歷著天上人間的愛戀,有一天,她卻無聲無息離他而去。
天上人間的愛戀美得讓人心碎。
回到林大維身邊,又過回以前的生活,接合得天衣無縫。只是,內裡挖空了一個小洞,不大不小的,就像彈珠一樣大小,正好在四個心房的匯合處,不影響什麼的,如無事人般又過著生活。
某夜,做了一個惡夢,一下子擾亂她的如常。
她睡在林大維身邊。夢中,她睡在凌子軒身邊,感到強烈的恐懼,心裡想:如果林大維在身邊,我便不會恐懼了。
她清醒過來,還是有心悸的感覺,如此熟悉的夢境。她一下子記起來了。
在那非常遙遠的地方,她什麼都沒了記憶,卻記著一個夢,不斷重複做著的一個夢,相同的人,相同的情節,不過角色掉換了。
在那遙遠的地方,她在凌子軒的懷裡睡。夢中,她躺在林大維身邊,感到強烈的恐懼,心裡想:如果凌子軒在身邊,我便不會恐懼了。
清醒過來,她有著深深的無力感。什麼都不能適應的無力感。
第一部曲:無愛紀
凌子軒總是一個人在清晨醒過來,一個人吃早餐,一個人在家工作,一個人吃午餐,一個人吃晚飯,一個人在酒吧,一個人睡。他總是一個人的,除了做愛的時間,兩個人,只有兩個人,從來沒有兩個人以上的實驗,根本沒一點那種幻想,那是他的執著。
兩個人身體的愛,透過一個管道連接起來,探索那如無盡頭的幽微地帶,那管道只容得下兩個人,連接上一個不知名的地方,類似極樂世界或什麼。
凌子軒執著的不是高高低低的高潮,而是兩個人仿似溶在一起的神秘時刻,他迷信那是上天給卑微的人類,超越一切界限的神秘管道,無邊際的蕩,他想起大海。
所以,他愛每一個跟他在大海中蕩的女人。是愛她們還是愛她們的身體,他分不清楚,正如汗水與淚水瀉進大海,有什麼分別?
正因為在大海中蕩,不能不承認,他有時對女人的淚水無動於衷。
所以當他每一個長長短短的partner,欲哭地問他同一個近似哲學性的問題:「你愛我的身體還是愛我?」他沒有答話。
Partner,這是他對他的女人的稱呼, 什麼女友, 情人,戀人等等,他都說不出口。伴侶,耐人尋味的。無獨有偶,他的女人離開他時,都有著類近的投訴:你當我是sex partner罷了。她們開始前是知道的,但開始後總以為這次是不同的,就讓時間去証實。
他沒有答話,只是更緊緊地抱著她們的身體去愛,那是他愛人的方式,不太激情,不太冷感,軟綿綿的愛如在大海蕩,閉上眼睛只專注身體的感覺,有時感到靈魂出竅,有一瞬間更似到達了一種忘我的境界,一瞬間,只一瞬間,如靈光乍現的出神瞬間,他如跟某些不可名狀的邊界接上。那樣的感覺讓他沉迷不已,那便是他的狂喜,而不是快感的高潮。
他嚮往的是極樂。所以,他跟一個個女體愛時,總閉上眼睛,等待那出神的瞬間到來。
你愛我的身體還是愛我?他想跟她們說:「我愛你,女人。女人跟男人是天衣無縫的結合。」
當然,他不會呆得把話說出口,沒有一個女人能忍受自己只是其中一個,你身邊眾多女人的其中一個。還有一個極至的想法,他也不好說出口 ——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在神秘管道裡完美地結合,是唯一的目的,最神聖而美妙的目的地。
沒能達到那樣神聖的目的地,愛不過是虛假的託詞,無望地把不能融合成一體的兩個個體困縛在一起。
因此,沒有到達目的地的那些晚上,他感到無比的失落,他不過在性交。什麼也不好說出口,他不過是一般人眼中的性上癮者,自圓其說地把情與慾分開,為性愛找藉口。
他曾經純真地相信靈慾合一,靈魂和身體無間地愛。他也曾經緊緊地抱著深愛的戀人,冷冷乾涸的身體,絕望得想哭。兩個人在一起,兩個人的孤寂。
開始時,不是這樣的。
進進出出於那神秘管道之間,他感到如回到母體的安靜。不再感到一個人在世間的孤寂,一切是連繫的。那樣美麗超脫的時刻,愛不愛不是那麼神聖吧。
所以他總是一個人,一個人不會感到寂寞,如呼吸般自然。
在大海中蕩,有時恍恍出神,有時欲飄欲仙,有時嘔吐大作。
是的,每當愛過後半夜醒來,看到睡在他身邊的女人抱著他睡死的樣子,在臉上看到滿足感,安全感,幸福感……他便想吐,真的光著身走進浴室便吐。然後輕手輕腳穿上衣服溜走,回家好好的抱頭大睡。
經驗累積下來,他發現那差不多是一種定律,不論身邊睡著的是那個她。久而久之,他強迫自己不要在愛過後便睡死過去,要挺起精神跟身邊的人聊聊天,直至天明才離開,或者女人先倦了,聊著聊著睡著了,他又輕輕的溜回家去。
這樣的他,吊詭地,剛開始時,總得到女人的寵愛,錯覺那是他纖細的溫柔。
不過是剛剛開始而已,時間累積下來,女人們都感到他的無情,差不多在等著自己半睡半醒間溜去,久而久之,那差不多是一場清醒與昏睡的拉鋸戰。而他總能保持清醒。
久而久之,她們發現,他留給她們的時間,只是一場不長不短的身體愛的時間,而且時間只會越來越短,直至他漸漸消失。
他漸漸消失的理由,只有一個 :女人漸漸在他身上需索愛,越來越多的愛。他同時看到恐懼,不安,嫉妒,佔有……無窮無盡的,因愛之名。
情慾的開端便是情慾,都明明白白的,他從來沒有說謊,他根本痛恨謊言,尤其是背叛的謊言。
愛和身體愛便能清清楚楚的割裂開來嗎?他身體力行的覺得可以。有時他會想,或許我根本沒有愛的能力,卻有著強烈的跟女體融合無間的慾望。跟性慾沒什麼分別吧?他不知道。
因為,他一直很在意嘔吐的感覺,吐的時間他如掉進萬劫不復的深淵,失落失落一直失落下去。想吐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不過是幻想靈與慾的可憐蟲,什麼如大海忘我的愛,不過是愛在女體裡射精的男人。
那不過是幻覺吧,那只是逃避日常愛戀的藉口 ,他清醒地想。想愛而不敢愛,以射精等同愛還來找藉口。他清醒的殘酷,一下一下的鞭打自己。很自虐很痛,不過是一個不能愛的男人,然後在一個個女體上蕩。
在出神的愛與現實之間,他感到如此的失落,如嗑藥後的失落。失落前,他是超越所有邊界的靈,失落後,他不過是性上癮的人。沒有解藥的,只好在一個個身體之間蕩。
為什麼會失落?為什麼連純粹享受身體的歡愉,在一個個女體身上尋找神秘的地圖,抱著一個個女體享受不同的愛和高潮也不行?
吐的時間,他覺得那形形式式的女體和愛,不過是千篇一律的性交。
他一個人不會感到寂寞,但一個人的時候會性飢渴,特別想做愛。一個人不寂寞,但一個人會慾火焚身。他感到身不由己,慾望會讓人上癮,沉到大海去。
開始時,不是這樣的。
他不過渴望簡簡單單地愛著一個人,簡簡單單地跟愛人一起生活,二人的生活。然後生兩個小孩,然後天荒地老。
開始時總不是那樣的,沒有人一開始便上癮的。
就在簡簡單單日復日的愛戀生活之中,在沒有愛情幻覺中,愛漸漸死亡,死得不能復生?
他記得開始時,那年他22歲,大學畢業後,便匆匆的跟初戀情人結婚,理所當然似的,他就想跟愛人一起過每一天,兩個人一起面對世間的一切美好與殘酷。
他沒幻想完美的愛情,不過是兩個人在一起去經歷現實,不然,一個人會寂寞得沮喪。
*
林大維不能一天沒有愛,一個人會寂寞得想死。所以,他花盡心思讓愛情與下一次愛情之間不留太長的空隙。愛情可長或短,但他最不能忍受的是 —— 一個人睡。
一個人在床上半夜醒過來時,如果身邊空蕩蕩沒人,他會突然感到絕望,一個人在世間的孤寂。
那寂寞得想死的時刻,大概是他最有形而上感受的時間了,其餘時間,他大概是現實主義者,超現實主義的,愛得腳踏實地,無論如何,儘可能留著一個人在身邊。那也是需要氣力才能做到的事情,交替與交替之間難免不讓人神傷。
神傷不同於傷痛,他記得從來沒有為一次又一次的分手痛過,他不懂那種感覺。第一次分手時,那種惘然感是絕無僅有的,只屬於初戀。
他的無癢無痛不是一開始便是那樣的,他也曾經對所有事情抱過夢想,當然包括愛情,只是他學習能力奇快,很快學曉現實的運作模式,然後腳踏實地地做一切事情,很努力地,當然也愛得腳踏實地。
惘然過一次之後,他變成一個日常生活的狂人,熱情地工作,熱情地追求愛情,兩者都不可或缺,不然,他會突然感到很空虛很空虛,然後突然想起初戀帶給他的衝擊。
初戀給他以後的人生類似一種基調的東西:理想不理想,還是要做,不斷地做。
識破理想,活得實在,不就是所謂的成長?所有成長的什麼,都是他媽的殘酷的,沒有空隙留給爛傷感。
不能傷感,不能空虛, 一下子的空虛已讓他有虛脫的預感,他不能空虛,連床也不能空虛,床的空虛會擴大一個人的空虛。
在床上愛一個個女人,他有活著的實在感。他沒想過自己成為了俯拾皆是的愛情獵人。
他不再談夢想什麼的,但有很多很多千奇百怪的幻想,一個個未接觸過的女體給他無窮的性幻想。那便是愛情獵人的哲學吧。
愛情獵人大概都很怕空虛,空虛便有獵殺的慾望,那跟愛情無關,不過有時獵殺需要披著愛情的糖衣,他想起豺狼,有時他覺得自己很豺狼,會說甜言蜜語的豺狼。
有一夜,他跟第20個女友分手後空窗期已兩個月。出奇地長的空窗期,因為那陣子他出奇地忙,忙得睡死了,醒過來又工作的天昏地暗日子。
60天如是者忙過去,忙完了,他不醒人事的死睡了兩天兩夜48小時後,正正半夜三時扎醒過來,從床上彈起來,坐直身子,很清醒地看著半邊空蕩蕩的床,突然很想哭,感覺很空虛,很寂寞,很久沒有抱過有著體溫,柔軟的女體了。他突然很懷念撫摸渾圓的胸部的複雜觸感。那觸感連帶自己也有著鐵漢柔情起來的感覺。
經歷了三個女體之後,他便知道自己無可救藥地迷戀女子的乳房,不同形狀,不同大小的乳房也可以,他是乳房的搜獵者,蒐集不同乳房的不同觸感。
作為蒐集者他有他的準則,三大不接受的乳房。一,不能是假的乳房,觸感總有說不出不自然的感覺。二,不能沒乳房,即是如男孩的平胸。三,乳房不能下垂,下垂的胸會讓他想起乳牛。理由是,他很怕任何讓自己有機會聯想起動物性愛的物事。
就在他空窗期兩個月後的一個深夜,他扎醒過來,想念著女子的乳房,非常非常的想念,連帶隱隱的有一點微苦的感覺。無可救藥的迷戀,想念的苦。
那一夜,他走進夜店裡時已接近四時。他知道在這時還未找到伴的女子,不會怎樣的了。 他覺得自己像野獸一樣,第一次飢渴得走進夜店來覓食。
環顧夜店裡,剛搭上的一對對性伴侶,他根本別無選擇,他只看到一個單身女人坐在吧台的中央,一個人喝著悶酒,挺標緻的模樣,最重要的是,在淺杏色貼身絲襪質料的高領入肩連身直裙下,裹著的是堅挺而線條優美的梨型胸。
盯著那樣的胸部,他覺得自己這夜有點走運,半夜四時,遇上沒話說的獵物。
什麼都有第一次,他生澀的初次一夜情的整個過程也是難忘的。
他最記得那女子容易受傷的神情,讓他受不了,那感覺像是受侵犯的動物。他把視線向她的眼睛下移,很想直視她堅挺的胸部,又怕太露骨,雖然二人都知道那是今夜的目的地。於是,他禮貌地把視線放在她的眼睛和胸之間的頸項。
他生硬的走到吧台前坐下,離女子一個座位。
在那個生硬的距離下,他劈頭問了一句很作戲的話:「一個人嗎?第一次來這裡?」
女子也答的奇特,如答問題機器般連環給了三個答案,「是的。不是的,我一星期來一次。」林大維心裡想,想不到。
最後她加上一句,差不多把生澀的林大維擊倒,「你是第一次吧?」
林大維故作鎮定地說道:「是的,第一次來這裡。」還有第一次生澀地上夜店尋人。
他好奇地想問她,一星期一次,每次都找到人嗎?還想問,一星期一次便因為想找人做愛?他還深層地想,一星期一次找人,不會太倦了嗎?
他們東拉西扯了十多句話後,眼神容易受傷的女子,說話卻毫不忸怩,「我叫青青。很晚了,想嗎?」
想。那是二人今夜的最終目的地,不用轉彎抹角的。
恍然間,他覺得自己回到少年時代,一群男生死黨同學圍著一位剛失身的處子,講述失身的經歷,就是找一位妓女給自己開竅,那是失身的其中一種典型,怕在情人前顯得手足無措,或者遇不上情人的,也想嚐嚐那是怎樣的一回事,看A片也看過太多了。情與慾誰說分不開,很多男子的身體早早有著這樣的體認。
林大維不想那樣失身,他跟很多人一樣,曾經做過愛情夢,遇上夢中情人,然後一生一世。帶著那樣的夢的他,不能想像讓身體隨便跟一個人愛。他曾經耐心地等待,等待夢中情人的出現。那種等待帶著希望,沒有焦灼的感覺,有一種青澀的氣味。
在情人酒店的房間裡,林大維坐在床上,聽著浴室裡傳來的水聲,錯覺自己是處子少年人,等待妓女出來,進行成人禮。
林大維在呆想之時,浴室門打開,白濛濛的水氣先湧出,然後是青青,穿著白色的浴袍走出來,身體挺得直直,出於一種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自覺,她的胸部仍一樣的堅挺。
看著那樣的胸,林大維聯想到浴袍下半透明通花桃紅馬甲胸衣,還有吊帶襪。多老派而媚俗的性幻想,管它呢,有用便好。想著想著,他的那兒也堅挺的挺起來。
「你沖沖身吧。」青青輕柔而自然地說道。但不知道為什麼她的話讓他冷了下來,又想起自己少年處子身的窘態。
從浴室走出來,只剩下床頭暗黃的燈光。青青已然脫掉浴袍躺在床上,桃紅馬甲衣的幻想給打掉,可看見露出杏色胸罩吊帶的雙肩,被子蓋至腋下的位置。
沒有意外,一切如常進行,很熱很熱,二人都很熱。在床上的青青也確實主動而嫻熟得如,妓女。
半夜四時的邂逅沒什麼好埋怨的了,連搭訕的時間都縮至最短,說了不多於30句話。
一件一件的,可以脫的都脫去了,只剩下她的胸罩,還有她堅挺的乳房。他幾次想進攻那高聳的城堡,她都以手按著自己的乳房,在他耳邊輕輕地說:「直至最後最後才能吻她,她飢渴得不得已……」
聽著聽著,林大維也感覺很飢渴,熱得抱著她便進入了那秘密的管道。他想,她是性事的調情高手,就是妓女,也是特種的高級技女。他想跟她說:「我下次會再call你的。」
越不能接近便越有致死的吸引力,無原因的,就是未得到滿足而煎熬人的慾望。這是所有人的死穴,無分男女的,慾望便是那麼的一回事。
到了慾望的目的地,慾望的魔力隨著瓦解。肉體便是肉體。
最私密的管道已然進入,他整個身體還是那麼的躁動,想著那神秘高聳的城堡。他實在按捺不住,身體的擺動完全沒有停過下來,手在城堡的後邊活動著。
她問道:「你真的想吻她?」
「很想很想,想了一整個晚上。」他說道,包含半夜醒來的焦灼。
「先把燈關上吧。」青青輕輕的說道。
他想,她在玩什麼遊戲,也只好把燈關上。
在黑暗裡,他的身體霎時冷了1/4。在黑暗中抱著一個陌生的身體,原來有一種唐突而不自然的感覺。
林大維想,男子的身體並不如一般人想的那麼簡單,越用腦,那裡便越不起勁。他唯有又專注在那兒,不讓自己亂想。
一切靜下來,他的身體仍停留在管道內 。那樣的靜,讓神經緊張起來,他想起戰戰兢兢的初夜,記憶普普如他也不會忘記的事情之一。
他的記憶字典的哲學是這樣的 :我們的生命不外乎以幾件重大的生命事件的開始與結束組成。人生,不就是一團團的混沌。
那樣的靜,那樣的黑,他差不多快要想不起她的臉,卻停留在她身體最私密的地方。那麼吊詭。
她的手捉著他的手,慢慢的貼近那神秘而高聳的城堡。如此接近,越來越接近,摒著氣,快要給火熱的慾望燒死了。
接觸的一剎那,他一下子軟下來,身體和那兒。
城堡之下,是平原,平坦一片的。那樣描述不夠真確,平平的身體上有著突突不平硬硬的組織。那是一次身體接觸的震撼。
他的身體各部分無能為力地僵在原處,不動。他也頹然地躺在那裡,不動。他突然清楚地想起青青的樣子,還有她容易受傷的神情。
「對不起。」他為自己身體的軟弱無力而充滿歉意,也為自己如不懂人事的少年的吃驚而抱歉。
身體的僵硬漸漸軟化,他艱難地想抱抱青青,想給她一點安慰。
「不用了,明白的。」青青平靜而斷續的聲音。「所以說留到最後。」
完事後才看你好好收藏起來的傷疤?習慣了好好控制情緒的他,也不禁有一點點陌生的難過。他又僵在那裡,這時什麼動作也會變得充滿可憐的意味。
這夜沒有談上30句話的二人,反而談起話來,斷斷續續的,在黑暗中。
「為什麼?」他問道。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問什麼,有太多問號了。
「以後也不會再見的了。」她照樣平淡的聲音,好像明白他的問題似的。
「因為那個?」
「是吧。」
「不好意思,我不大懂這些,但應該,應該怎樣說呢……」
「做義乳吧。」她總是這樣直接,就因為不會再見?「我接受我自己的身體,問題不在於我。」
「有人會接受的吧……僻如先給那人一點心理準備之類。」
「剛開始不是那樣的。後來發覺也差不多,開始都說接受的,最後都跑掉。」
他一時無語。
「我以身體作証,現在愛我的人不會是因為我的身體。以前,愛人跑掉,我會想一些無聊的問題,僻如他是愛我的,其他人只是身體等等。」她平淡地說道。
「對啊,愛你也可以愛很多個身體。誰說的,每個男子都花心,不同的是有沒有控制能力。所以你每星期去酒吧一次?」
「你想問我是否一星期需要一次?」青青輕輕的笑起來,難得自然地談著老朋友也未必會談到的敏感話題。「只是讓自己覺得正常的次數。過了一些時間便去其它地方。」青青冷冷的說來,如說著別人的事情。
「這樣……」林大維有點遲疑的說,「這樣會讓自己受傷吧。」
「不會有更差的了,所以免疫了。而且以後不會再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你們!林大維忽然有一種受傷的感覺,他也不過是一大群色鬼的其中一個。
「不過,你是不同的,跟我談話。還有另外一個怪人,一直傷感地摸著我的傷口喃喃自語,我好辛苦才能逃離現場。想起也想吐。」
是那樣的一回事,我和一個戀傷癖的人是不同的,林大維呆呆地想。
「我先走,再見了,永遠。」黑暗中又響起青青冷漠的聲音,還有她翻身離床,穿衣服,上浴室,沖廁,水龍頭水流開與關,打開門離開,各種各樣瑣碎的聲音。
還有一次又一次習慣心碎的聲音?
他想起青青容易受傷的眼神。在一個陌生人前,一個陌生環境,割開自己的傷口來灑鹽,久而久之會不痛,是他媽的療傷的一種方法吧。
那初次一夜情的經驗是震撼的。從此,他遠離平胸的女子們。因為,他對身體的平原充滿不可名之的敬畏之心。而且再也不在夜店尋人,他覺得那地方充滿動物慾望的氛圍,並帶有絕望的氣味,焦灼都寫在眼裡,旁人都看在眼裡。他不想那樣,不想讓自己覺得無望,可憐,他要告訴自己,我有更多的選擇。
是那樣嗎?不在夜店裡,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焦灼不安地飢不擇食的。兩個人在一起如何寂寞,至少不飢渴。
40歲那年,他發現自己看見可以上的女人,也提不起勁去探索,大概是蒐集者的慾望褪減了,大概是有了年紀。他有了一種覺悟,長此下去尋找情慾,會很倦很倦,他想到安定下來,真真正正的兩個人在一起,過兩個人的生活,每晚總有一個人睡在身邊,床至少不會空虛。
就在這時,總要腳踏實地的林大維遇上28歲總如在夢中的夏哲。
在愛情路上浪蕩多時的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他真的很喜歡夏哲,感覺如初戀般,第一次真正的愛上一個人。
*
夏哲初次遇上林大維時,她的身體顫動了一下,知道將要跟這人在一起,或長或短的時間,但她沒想過會跟這人結婚。
那種身體顫動沒有任何命定的感覺,只是一種預感,男與女相遇,而他們剛好都是一個人。一切不過是時間和環境下的產物,那便是美其名的,所謂的緣分吧。
對於所謂的緣分,夏哲不存幻想,或許她對愛戀本身便不存幻想。美好的幻想只在愛戀前可能,愛戀後,幻想的空間慢慢被現實吞噬。
很多次很多次愛戀後,感到愛戀不過是美好的情慾感覺慢慢流失的過程,有時短暫得連愛過也談不上。
流失的過程曾經讓她受傷,哭了很多,流了很多淚水後,她免疫了,能不再哭。
她無可無不可的談戀愛下去,不因為怕一個人寂寞,不因為兩個人在一起沒一個人那麼寂寞。只因為她是一個人,剛好遇上一個男子也是一個人,有點好感,能談得來,不覺得討厭,便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
她不過想過平常人的生活,包括平常的愛戀。愛戀嗎?沒想像中的那麼美好吧。越美好便流失得越痛,無可無不可地愛便不癢不痛。
無可無不可並不是什麼也沒所謂的,她堅持不做第三者,有女友的男子,有小孩的人夫一律謝絕。想法很簡單,自己不傷便不要無所謂的傷人了,犯不著。 在現代三四五六角的混亂關係中,她有她的底線。
不想不明不白的做了第三者也不知,她固執地要跟她睡過的男子陪她睡到天明,不能完事便走。但她發現自己根本不能在半陌生戀人身邊好好地睡,在家好在男子家好,她總是等男子在完事後睡死了,便悄悄爬起身來抽她的事後烟,然後走到客廳的沙發上睡,都只能淺睡。
整個過程她都輕手輕腳,生怕在過程中,男子突然醒過來,以大情人姿態拉著她回床上,抱著她睡。
她想跟男子們說:「我跟陌生人睡便睡不好。」然後有意識地把話吞回去,不能那樣傷人。
她用各種藉口來掩飾,僻如不能睡陌生床,不能給人抱著睡,腰會痛等等,然後離開那人一個安全點的距離。不過,她還是會儘可能逃離那人身邊。
大概要長一點的時間才能習慣吧,僻如一年。一年,很多人都未能度過這段時間便消失了,她親密而疏離的半陌生戀人們。
她難以理解自己,也難以理解跟自己愛過長長短短時間的半陌生戀人。她記不起很多半陌生戀人的樣子來,卻清清楚楚地記得愛戀流失的過程。因為,那流失的過程如此的相似。
她不能好好適應愛戀的流程,卻記下了流失的過程。
她不怕一個人睡,卻大部分時間都是兩個人睡。大概很多人怕一個人的寂寞,一個人時遇上也是一個人的人,只要有點好感,便走在一起談戀愛。所以她一個人的時間少之又少,一直呆在戀愛的狀態中。
開始,不是那樣的。她不是那樣無動於衷的。大概是痛極而麻掉了神經,才能下去。大概是千篇一律的理由,不愛不傷,然清醒地愛。
鏡花水月或天長地久,重要嗎?最後,我愛過你,然後不再愛你,然後我愛另一個人,不愛另一個人,反反覆覆的。跟你在一起很長時間的人如分割了你的時間,變得更重要,就是那麼一回事。最後最後,我們還不是一個人?
夏哲在開始新的一場愛戀時, 隨意亂想,那是她第21次的愛戀了。
她覺得那些以戀人數目多而沾沾自喜的人很可笑,那不是加減乘除的簡單算題嗎?戀人多不過是不長情而已。
她的好友娜奧美跟她說:「是否開始得太快?」
她不置可否的聳一聳肩,「不知道啊。不那樣開始,可以怎樣開始?誰說的,現代愛情都在開始的一星期內搞定的嘛。現代愛情都在床上開始的。」二人笑起來。
「男子愛的速度跟女的完全不同啊,最過癮是狩獵時間,到床上是高潮,高潮後,熱情便慢慢冷卻,那是生理現實,沒法改變的。注定短命的,愛情還未開始便死了。」娜奧美說道。
「不然可以怎樣?拖延開始的步伐?由一天到兩天拖延到七天,然後讓他火山爆發?」二人又笑作一團。
愛由身體的愛開始,最先流失的也是身體的慾望吧。如果身體不再愛,還能愛嗎?
夏哲悲觀地想,只有柏拉圖式的愛才能天長地久,不然,愛都被困在身體慾望裡,一步步經歴愛流失驚心動魄的過程。開始便無可避免想到結束。
夏哲想,有沒有一種無重的愛?兩個人在一起在無重的狀態,什麼也輕如烟,觸不到地,愛在飛行中,不會受現實的磨損,不會變得沉重。但那樣的愛,其實跟現實根本無關。
序章:夢
未來。某時某地。
不是末日世代,城市一樣籠罩著濃濃的末日氣息,無過去,無現在,無未來,那是活在當下的意思。
這一年,鬱悶煩躁的城市,出現了一連串戀人莫名消失事件。消失者過了一段時間再回來,對消失期間經歷過什麼,出現或輕或重的失憶症。其中有些是永久消失的,更無從對証。
消失者回來後,他們的身體沒有什麼變化,但心理年齡卻顯著衰老了,呈現不同程度的健忘症,並不時出現虛浮暈眩的感覺,加上消失者身邊人出現不同程度的狂躁抑鬱症,不甘,失落等等,一一統稱為莫名消失症候群。當然有不少人也不當一回事,戀人無...
作者序
在墜落中想像無重/林峰毅
小說寫作的過程通常帶有某個問題意識,那是一段自我觀察與探問的過程,也是明知沒有目的地卻執意出發的旅途。
「有沒有一種愛,是沒有重量的?」這是《無重紀》所蘊含的問題意識,那是一句疑惑,也是一聲嘆息。
在葉飛的小說裡,經常沒有明確的時空背景描寫,她的文字總是更在意人心裡的暗湧,那些我們即使意識到卻也不願、不忍揭開探看的黑暗深處。
關於追尋愛情的歷程中,我們總是墜落進去的,那往往是個意外,出乎我們的預期,愛情的書寫即是描述墜落的經驗。我總想到愛麗絲墜入wonderland的洞穴,在那深長不止的墜落間,愛麗絲可以胡思亂想自己會不會穿越地心,甚至翻閱架上的書籍,不知何時是個了結。
W=mg,重量的換算公式,物理學告訴我們,重量來自於質量與自由落體速度的加乘,若要想像一種沒有重量的愛情,那樣的探問或許導因於愛情本身實然引領我們墜落的引力。
引力往往來自原欲的渴求,身而為人,我們總不喜歡將自身的性行為稱作性交(或更生物意義的交配),那總讓人想到獸類的原始行為,於是我們的修辭將愛納入其間,愛伴隨著性、性伴隨著愛;更甚者,愛即是性、性即是愛。然而,什麼樣的性堪稱為愛?
人與人之間彼此交纏的肉體慾望,像是一波又一波復返的浪濤,瞬間將我們帶向高潮狂喜的峰頂,又旋即讓你失速墜落至低盪谷底,那股強烈的、不知所為何來的衝動與失落,有時與愛是相互衝突的,愛被我們賦予不同程度的聖潔意義,使我們在背德狀態下同時感受到肉身的污穢沉重與觸犯禁忌的快感,那幾乎與熱切愛戀下的兩人渴望融為一體的感受彼此排斥,愛裡總是無理可循,自相矛盾。
因為嚮往無重的狀態,夏哲決定離開地球,前往太空。太空是實質意義上的無重,在綿延無邊的宇宙裡,在寸草不生的洪荒星球上,我們脫離萬有引力的束縛,飄盪在失去上下界線的空間之中,由物質世界乃至於精神層次,擁有無重的身體是不是意味著能夠擁有無重的愛情?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想像,在葉飛的文字裡,時間與空間似乎是抽離的,我們見不到太多科幻細節的描述,《無重紀》寫的仍舊是人們無解的愛戀關係,我們只能在有限裡尋找無限,在束縛裡尋找解脫,我們的靈魂寄宿在肉體之中,在一隅之地裡探索精神世界的無底深淵。
如此說來,愛情或許有著一點唐吉軻德式的自虐與浪漫吧,猶如無重紀裡的追尋旅程,在墜落中想像無重,在絕望中懷抱希望。
在墜落中想像無重/林峰毅
小說寫作的過程通常帶有某個問題意識,那是一段自我觀察與探問的過程,也是明知沒有目的地卻執意出發的旅途。
「有沒有一種愛,是沒有重量的?」這是《無重紀》所蘊含的問題意識,那是一句疑惑,也是一聲嘆息。
在葉飛的小說裡,經常沒有明確的時空背景描寫,她的文字總是更在意人心裡的暗湧,那些我們即使意識到卻也不願、不忍揭開探看的黑暗深處。
關於追尋愛情的歷程中,我們總是墜落進去的,那往往是個意外,出乎我們的預期,愛情的書寫即是描述墜落的經驗。我總想到愛麗絲墜入wonderland的洞穴,在那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