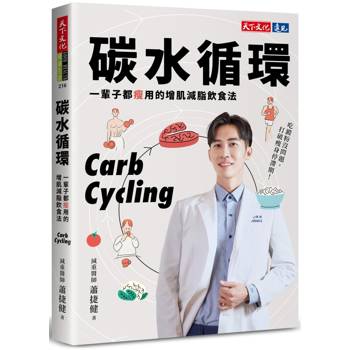遙遠的記憶片段,滿溢詩與歌聲
朦朧的愛與哀愁中,初識人生況味
《我的母親手記》前傳,一代文豪的形成史
盡管雙親健在,又有弟妹,井上靖卻遠離父母,與毫無血緣關系的祖母一起,住在一間倉庫中度過了童年時代。少年時又由於父親擔任軍醫,經常調動,所以獨自一人度過了自由的中學時代、狂熱的青春,回首來路,猶如時光的旅人,一代文豪於焉誕生。
• 如糖 如春
「童年憶往」裡,為思念母親的孤獨寂寞,想像自己猶如包覆在蠶繭裡,透過母親的肚子觀看這個世界,但與祖母既像戀人又似同盟的關係,雖然只有兩個人住在土倉相依為命,卻飽嚐了幸福。「每當我回憶幼年時代,都覺得能夠在故鄉伊豆的山村度過那段光陰實在是太美好了。」
•悠悠 盪盪
祖母隨著童年遠逝,一個人離開家人,或是住在學校宿舍,或是賃居寺廟,在沒有真正的監督者看管下,過著極為自由的少年時代。除了去學校上課外,和幾個意氣投合的朋友天天不是爬山,就是划船、散步,或是在街上遊蕩,玩得不亦樂乎。「應該說玩得天昏地暗才對。就是不管怎麼玩都覺得不夠的那種玩法。」高校時代,則因參加了柔道社,從中發現了自我,「柔道對我們而言僅僅是年輕時期的一種生活方式,我們用三年的時間苦練,只為探索自己力量的極限。我覺得柔道的生活和北國的氣候,給了我這個人某種決定性的東西。」
•啟蒙 創造
不若《我的母親手記》裡面對親情的冷靜自制,井上靖於本書中充滿孺慕的擁抱童年與青春,人生初始的愛與哀愁,或悲或喜,一如天地雛子。那些啟蒙自己的人事物,那些激發熱情的回憶,更有那全身投入大自然懷抱,在它溫柔撫育下成長的幸福。「到目前為止,我描述了人與風土如何在自我形塑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當我在思索自己這個人時,如果無視此前所提到的那些人以及我所住過的那幾個地方,那麼我將一無所獲。我還在中學和大學時代的友人帶領下得到文學的啟蒙。沒有這些朋友,我想我對文學或許不會發生興趣,也一定不會成為一個作家。」
作者簡介:
井上靖 (Inoue Yasushi, 1907~1991),
生於北海道旭川,父隼雄為軍醫,輾轉任職各地,戰前曾任台北衛戍病院院長。井上靖青少年時期多寄居故鄉伊豆親友家,未隨家人前往父親任地。1932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就讀,主修美學。1936年以《流轉》參加每日新聞社〈每日週刊〉徵文獲獎,因此機緣進入每日新聞大阪本社工作,負責宗教與藝術方面報導。1950年以〈鬥牛〉獲芥川賞,翌年自每日新聞社退職,專事寫作,完成許多質量皆可觀的連載小說。
1958年以《天平之甍》獲藝術選獎文部大臣賞,次年以《冰壁》獲日本藝術院賞;1960年以《敦煌》、〈樓蘭〉獲每日藝術大賞。之後亦是獲獎無數,包括讀賣文學賞(《風濤》)、兩度日本文學大賞(《俄羅斯國醉夢譚》、《千利休 本覺坊遺文》)、兩度野間文藝賞(《淀君日記》、《孔子》)。1976年獲頒文化勳章,1981年任日本筆會會長。
井上靖一生著述不斷,膾炙人口的作品還有《冰壁》、《風林火山》以及自傳性極強的三部曲《雪蟲》、《夏草冬濤》、《北之海》等。作品也大量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和舞台劇,如1988年《敦煌》改編為同名電影(佐藤純彌導演), 1989年由《千利休 本覺坊遺文》改編的電影〈本覺坊遺文〉(熊井啟導演)獲威尼斯影展銀獅獎(當年金獅獎得主為侯孝賢〈悲情城市〉),2009年《狼災記》由田壯壯改編為同名電影,以及2012年《我的母親手記》改編為同名電影(原田真人導演),堪稱昭和的大文豪、國民作家。
譯者簡介:
吳繼文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日本國立廣島大學哲學碩士。曾任聯合報副刊編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文學主編、叢書部總編輯,台灣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著有長篇小說《世紀末少年愛讀本》(聯合報「讀書人」年度好書)、《天河撩亂》(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
《天河撩亂》部份章節曾先後收入《中華現代文學大系》(馬森主編,九歌出版)、《台灣同志小說選》(朱偉誠主編,二魚文化)、英文版《天使之翼:台灣當代酷兒小說選》(Fran Martin主編,夏威夷大學出版)、《媲美貓的發情──LP小說選》(黃錦樹、駱以軍主編,寶瓶文化出版)、日文版《新郎新 '夫'——台灣性的少數者 [sexual minority] 文學3-小說集》(黃英哲等主編,作品社)等選集。
詩作曾選入《七十八年詩選》、《創世紀詩選1954-1984》;舞台劇《公園1999的一天》1998年11月於台北藝術大學首演。譯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記》(馬可孛羅)、中沢新一《看不見的人》(橡樹林文化)、井上靖《我的母親手記》(無限出版)以及吉本芭娜娜作品《廚房》、《哀愁的預感》、《鶇TUGUMI》等多種(時報文化)。
章節試閱
風 暴
颱風的季節,現在和過去並沒有什麽兩樣。每到夏末秋初時節,年年如此,就像彼此約好了一樣,暴風總是準時出現。如果九月沒來,十月肯定會來。一如二百十日或是二百二十日 這樣的說法,大家都確信暴風會如約到訪。
跟現在不一樣,那時的人並不會有颱風之卵在南方的珊瑚礁海域成形、孵化,漸次成長、壯大,然後朝日本列島北上這樣的觀念。當天空出現一些不尋常的徵兆,風勢也與平日有異,這時大人們心裡就會有迎接一場狂風暴雨的準備。風暴從天空的一角開始四處奔竄,如果哪個地方還沒吹到,好,那就去那裡給它翻攪一下,大概就是這樣解釋它的來由。一旦被鎖定你就認了,它一定不會放過你,好像這一切都是計劃好似的,大家都以認命的態度去接受它。
就像如今的人緊守收音機前面關注氣候動向,村民則是頻繁地出去觀察天空的變化。從雲的移動、雨勢大小還有風勢強弱,來判斷暴風雨是否來襲。如果看樣子這場風雨是躲不掉了,村民們立刻內內外外忙上忙下。他們去巡視一下田圃,在小溪邊築起河堤,並一定要幫橋樑補強以免被沖走。當這些共同作業告一段落後,接下來大家回到自己家裡,開始忙著各種防颱準備。盆栽要拿到牀板底下或放進倉房中,並且幫大樹綁上一根支柱,梯子收起來,草蓆則是卷成一束束固定在屋簷下以免被吹走。等這些都做好了,男人們就開始釘緊窗戶的雨遮版。家家戶戶都傳來敲打釘子的聲音。
我們喜歡風暴來襲前整個村落的氣氛更甚於春節。不管到村子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大人們利落的動作。即使那些平日懶散慣了的傢伙,這時也忙乎得很。在大家辛勤的防颱準備中,薄暮降臨了,彷彿不想讓村人的期待落空,雨勢也逐漸增強。
尚未就讀小學前年幼的我,都可以明顯感覺防颱之日那種異常的緊張與興奮。奶奶一次煮好兩天份的飯菜,準備了比較粗的蠟燭,也將水缸加滿,然後搬了許多用來接漏水的器皿到樓上去。水盆、木桶、洗臉盆、提水桶,這樣還不夠,連吃蓋飯用的大碗都要拿到南邊窗下的地板上備用。因為是土倉,不用擔心像別人家那樣遮雨版會被大風吹走,但屋頂卻讓人放心不下,視風向不同,屋瓦有可能隨處亂飛。
暴風來臨的夜晚,我們會比平常提早吃晚飯。用過晚餐後,我和奶奶立刻上床就寢。誰也不曉得深夜會發生什麽事,所以先睡飽再說。躺下來的時候,外頭已經下起大雨,風勢也越來越強。暴風雨不會往別處去了,它就是對準了我們過來,我是抱著這樣的想法入睡的。半是期待,半是不安,非常奇妙的滋味。
——哇,來了來了!
我躺在床上,豎起耳朵傾聽。奶奶理當有催我趕緊睡覺,但我因為興奮難耐,哪能說睡就睡。異常的事件就要發生,它的先頭部隊已經抵達,包圍了我們的土倉。
——你看,它來啦!
——不要說話,趕快睡。
——可是,人家睡不著。
——閉上眼睛就會睡著的。
可一閉上眼睛,別說睡覺,反而屋外風雨聲聽得更加的清楚。
——聽到沒有,好像有奇怪的聲音?
——不要怕,大概是柿子樹的樹枝被吹斷了吧。
——柿子樹折斷!?
我嚇得從床上爬起來。
——不是柿子樹,是它的樹枝啦。你就別擔心了。
我想我和奶奶之間大概會有這類的對話,並在有一搭沒一搭的對話中睡去。
等下次睜開眼睛時,外面的風雨聲又比剛才激烈了許多。
——奶奶……
我想確認奶奶是否還睡在我旁邊。
——乖,趕快睡吧。這種時候眼睛還睜得大大的小孩,村子裡一個也沒有吶。
奶奶的話讓我感到安心,於是再度沉入了夢鄉。
待我又一次醒來,奶奶還是躺在我身旁,而外頭的風雨依然狂暴,甚至還有雷鳴。房子裡面也發生了小變化。從屋頂滲進來的雨滴,以一定間隔「啪嗒、啪嗒」敲打著天花板。小鬼終於來了!每次聽到漏雨聲,我都會有這種想法。漏雨的小鬼不止出現在颱風夜。只要連續下幾天雨,這小鬼一定會來。
但是在暴風雨的夜晚,當一隻小鬼潛入之後,很快就會一隻接著一隻進來。先是聽到對面的天花板來了一隻小鬼,不久我正上方的天花板也開始有小鬼作怪。
一邊聽著天花板上惡作劇的小鬼發出「啪嗒、啪嗒」的單調聲音,我不知不覺又睡著了。天花板上面有小鬼比沒有好。這漏雨的小鬼一點也不可怕。總覺得它們是在陪我玩,讓躺在床上兀自睜著眼睛的我不致感到孤單。漏雨聲大人聽起來多少有些鬼氣森森,但在年幼的我心中既不陰暗,也不嚇人。小鬼們偷偷地從遠方將水運過來,並加以調節,讓它依著一定的間隔滴落。它們充滿耐心而且非常認真地進行這項秘密任務。
當我再次睜開雙眼,土倉二樓的情況完全變了一個樣。奶奶已經起來,一下把水桶提過來,一下將臉盆捧出去,和處處漏雨展開苦鬥。到這種程度,就不能說是小鬼的惡作劇了。天花板直接下起雨來,連小鬼們也嚇得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奶奶……
——糟糕、糟糕。
——現在我的臉上一直滴水。
——糟糕、糟糕!
不管我抱怨什麽,奶奶的回答永遠是「糟糕、糟糕」。實際看起來,周遭的情況也只能用糟糕兩字來形容。我躺在床上,讓奶奶移來移去;剛剛睡的地方,則開始放上面盆、水桶接水。櫃子裡的棉被和大包小包都被清空,因為那裡也開始漏雨了。
——糟糕、糟糕!
奶奶在嘴裡叨唸同樣的話,一邊樓下樓上忙個不停。這時也有一兩張榻榻米不得不翻起來。
從外面滲進來的風吹著油燈,忽明忽暗,映照著奶奶和她忙碌的身影。暴風雨釋放所有的能量,不斷擊打著土倉。不時有不明物體飛過來打在窗上劈啪作響,同時也可以聽到樹木的哀號。
——我肚子餓!
我從床上坐起來說。奶奶一聽立刻下樓,把準備好的飯糰拿上來,放在我床前的地板上。奶奶這時也藉機喘了口氣。兩個人一邊聽著暴風雨的咆哮聲,一邊大口咀嚼飯糰、喝茶充飢。那就跟現在的小朋友遠足吃便當一樣。不過比起來刺激有趣多了。
當暴風圈的一部份開始越過山嶺、風狂雨驟稍歇時,我的外祖父或是染坊的遠親爺爺就會過來看看情況。奶奶也知道他們會來,於是預先把樓下的門栓取下。不過染坊的爺爺多半只是站在北邊的窗戶底下喊話。
——喔伊……喔伊……!
在把天地翻攪得面目全非的風暴底下,傳來熟悉的呼喚聲;那聲音忽近忽遠。那時的景況在我的想像中,土倉外頭的世界無非波濤洶湧、一片漆黑的怒海。呼喚聲聽起來就像從遭難的船隻發出的求救呐喊。
——有人在叫我們!
——哪裡?
奶奶側耳傾聽,確認了來自遭難船隻的聲音後,稍微打開北邊窗戶的遮雨版。外頭依然狂風暴雨。
——是染坊的老爺嗎?
——是啊。
隔著窗子,土倉內部和外部的對話立刻充滿了生氣。
——真是嚇人啊。河堤差點就潰決了。
——麻煩您看看我們的屋頂,不知道變成什麽樣子了。
——你叫我看,天曉得看不看得到呢……屋頂好像都還在呀。
——我們房子裡面漏雨漏得可厲害了。
——如果只是漏雨那真算不得什麽。淺田 (Asada) 他們家儲藏室的屋頂被吹走,掉在淺井 (Asai) 家隱居小屋的屋頂上了。
——啊,對了,我們庭院的樹情況怎麼樣?
——石榴倒了。只倒一棵石榴的話算是小意思啦。天亮以後,你可以到橫瀨(Yokose) 家後門瞧瞧。簡直不得了。不看可惜啊!
染坊的爺爺裸著身子只繫條丁字褲,上面披了件蓑衣。他有時還會把蒲團給頂在頭上。
不是站在窗下,而是直接上到土倉二樓的,則是外祖父。滿頭滿臉都是雨水滴滴答答落。他睜大眼睛環視因為漏雨而沒一個踏腳處的房子。
——這座倉庫真是老得可以了。
他一開口就這麼說。
——屋頂不修一下不行吶。
奶奶回答。
——何必白費力氣,如果要修,不如直接拆了比較快。
——把這裡給拆了,我們就沒地方可以住啦。
外公沒有直接回答。
——樹倒了兩三棵。我明天拿竿子把它們撐起來。
說完立刻下樓離去。他這人有時不近情理,但也有親切的一面。雖然關心慰問的話一個字沒說,但深夜到訪,無疑就是表達對風災的關切。
不止染坊的爺爺和外祖父會過來關心災情。附近農家的人去巡視田園路過,或是在土倉的窗下問候幾聲,或是在樓梯入口大聲嚷嚷著什麽。不管是哪一種,慰問風災的深夜訪問者聲音都沒辦法聽得太清楚。因為被風吹得四處跑,只能斷斷續續傳來。怎麼聽都像是來自暴風雨的海上遭難船隻的吶喊。
每當聽到這樣的微弱叫聲,佳乃奶奶就會打開北面的窗子,或是到南面的窗邊仔細傾聽,也會下去一樓確認一些狀況。已經了無睡意的我,就一路跟在奶奶後面。
——嘿,你上床睡覺去。
奶奶雖這麼說,但這時可不是乖乖上床的時候。
——咦,又有人在叫了!
聽我這麼說,佳乃奶奶也豎起了耳朵。外面轟轟怒吼的聲音再度傳入耳膜。
——什麽也聽不到啊。
——哪裡,現在就有聽到。是阿幸 (Sachi) 的聲音。
——你在說什麽傻話?如果現在阿幸敢走到外面,早就被風不知道吹到哪裡去了。
——哎呀,我又聽到了。是阿町 (Omachi) 姐姐的聲音。
在風雨的怒號中,不斷聽到熟人的聲音。如果覺得是阿幸的聲音,聽起來就是阿幸;覺得是阿町姐姐,聽起來就是阿町的聲音。
——啊啊,又聽到了。
——是你的錯覺吧。
——才不是,我真的有聽到。你聽,有沒有?是坂下 (Sakashita) 家的爺爺呢。
——是嗎,他說什麽來著?
——說想吃柿子。
——一個牙齒掉光光的老人家,能吃柿子嗎?
大約這個時候,圍著土倉瘋狂擊打一整晚的怪物,逐漸收斂它狂暴的鋒芒。雨勢變小了,風聲也慢慢遠去。天色開始泛白。
我和奶奶躺回因漏雨而搬移到房間一角的床上。覺得所有狂暴的東西都逐漸遠離,我帶著一種意外滿足的安堵之感再次睡去。還有其他開心的事物在等著。待我醒來時,我一定要親眼去瞧瞧風災給村子留下的景象。那種令人期待的興奮,在臨入睡前的我面前閃閃發光。
關於暴風雨的夜晚,記憶中還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印象。我不知道被什麽人揹着,從土倉前往本家。
那時天空已經透出魚肚白,風暴逐漸平息。雨停了,只剩下陣風還會不時猛烈吹個幾下。就是在那樣的時刻,有人揹着我,從土倉走向母親的娘家。也許是因為漏雨太嚴重,所有的榻榻米都得翻起來,我必須換個地方睡覺。或者我發燒了,只好到人手較多的本家接受照顧。說不定,發燒的人不是我而是奶奶;奶奶不得已將我託給本家那邊來照顧。
不管是什麽情況,在風暴之夜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刻,我從土倉朝著本家,以那時的感覺來說,仿佛展開一段極為漫長的旅程。雖說是漫長之旅,其實自土倉到本家中間沿著道路也不過隔個幾棟房屋而已,以大人的腳程大概不到五分鐘吧。
我搭在不知道是誰的背上,穿過一片殘破的風景。彷彿騎著駱駝走在異國的土地上似的,在我心中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我到今天還是非常喜歡「曉闇」這個詞所形容的天色將亮不亮的時刻 。夜晚雖說已來到它的盡頭,但天又還沒亮起來。那是介於黑夜和白天之間一個曖昧不分明的時刻。類似幽冥前世的東西,在你周邊濃烈地徘徊不去。
之所以喜愛曉闇這種天色微明的時刻,恐怕是年幼時,暴風雨的夜晚將盡,我讓人揹着,走在曉闇旅路上的緣故。道路在大雨的沖積下處處碎裂,還有坑洞。路面上滿布斷落的樹枝和葉片。在那樣的路上,我讓人揹着一步一步向前走。只要抬起頭,就可以看到樹木在風中激烈晃搖,其中還有幾棵看起來就像女子的長髮被吹得四處飛揚。有些樹已經躺倒在地上,有的則斷裂欲傾。走過的人家都還緊閉著門戶。這大概是我五歲或六歲時的事了,我第一次在未知的風景和時間當中旅行。
風災之日從土倉朝本家移動,是我和曉闇的初次接觸。之後我屢屢重複這樣的體驗。由於置身黑暗逐漸稀薄的微明時刻,多少處於一種異於日常的狀態。
比方小學兩天一夜的修學旅行 。黎明前後,我們在小學的操場集合,分別搭上幾部巴士出發。旅行本身的記憶已經淡了,但籠罩整個操場的曉闇卻至今清楚記得。一開始根本看不清你隔壁的人,隨著夜色彷彿一層又一層薄紙被掀開,好友的面孔也逐漸浮現你的眼前。每個人都是一張睡眠不足的臉,只有眼睛,因為對即將展開的修學旅行之興奮期待而閃閃發亮。
收到徵兵令,從故鄉出發那天,也是排開曉闇走出家門,在村辦公室前集合,慌張地和村人彼此交換簡單的問候。獲贈千人針 的儀式同樣也是在曉闇下完成。
還有很多。在中國大陸進行野戰時,部隊通常都在曉闇中進發。我因為是輜重兵,必須牽著馬;和馬匹並肩走在曉闇中的情景,至今還懷念不已。士兵也好、馬匹也好,都是在半睡半醒中前進。我們在曉闇之中渡過河北省的永定河;向保定城外進發亦然。我一個人離開部隊,爲了轉移到後方的病院而前往石家莊車站,也是曉闇時刻。
成為小說家之後就不曾再與曉闇互動了。生活變得平凡無奇之故。雖然熬夜工作時,也會透過窗戶感覺到闇夜走向破曉,但人並沒有真的置身曉闇之中。
我很喜歡曉闇籠罩下天色將明未明的一段時間。因為人要正面迎向什麽東西的緣故。我們都知道有「衝破曉闇」這種說法,人在精神上確實會直面未明的黑暗,並衝破黑暗進行一些重要的事。
我在小說中好幾次處理曉闇的場景。我總是以小時候暴風雨夜的經驗為藍本。我不太寫黃昏,但我寫曉闇。我想是因為比起暮色降臨的感覺,曉闇所營造的氛圍更加強烈、更加特別。我不清楚有沒有「未明曉雪」這樣的說法,我很想找個機會使用曉闇之中白光若隱若現時的場景,卻一直沒有實現。
暴風雨的隔天,基本上都會放晴。彷彿渾然忘卻昨夜的風暴似的,天空蔚藍萬里無雲,太陽也大放光明。整個村子好像噴灑過消毒藥而且用力擦洗過一樣,骯髒的東西全都不見了。與此同時,因為擦洗過度,導致遍地傷痕。
小孩就是小孩,風災的次日也很忙。必須巡視村子各個角落,檢查暴風留下的爪痕。只要聽到誰家的柳樹倒了,那非去瞧瞧不可;誰家池塘裡的金魚被暴雨沖走了,那也要去看看已經空無一物的池塘。
還有其他各種有趣的事情。比方把緊緊黏貼在地面上的樹葉一片片撕起來,也是暴風雨的隔天才有得玩的遊戲。
——小鬼,精神真好啊。
風災後忙著整理復舊的大人們,偶爾也會丟過來一兩句話。他們要曬榻榻米,把遮雨版搬走,在竹竿上晾洗好的衣物,整天忙得不可開交。
小孩子就這樣混在忙碌的大人中間遊玩。看著大人們在自己遊玩的地方四周忙進忙出,總覺得有一種對抗的張力:大人們越是忙個不停,小孩子也玩得越是興致高昂。
——喂,別在那裡礙手礙腳,走開點!
有時會被大人叫去其他地方玩。轉換遊戲場完全沒有問題,到了新的地方照玩。
在風災的次日,記得我曾經在流過院子的小溪岸邊洗滌場,撿拾從上游流下來的東西。水深一般只到小孩膝蓋,但洗滌場因為用木板將水堰塞住,水位變得比較高。暴風雨翌日,水量大增,在濁流之上運送來好多東西:單只的木屐、空罐、軟木塞、木箱、硬毛刷……等等什麽都有。
這類東西如果流到洗滌場,不管是什麽我都會撿起來。在我撿到的許多漂流物裡面,曾經奶奶發現了一把飯勺子,就拿回土倉去。這把飯勺子從第二天開始成為我們的廚房用品之一。後來每次聽到奶奶跟別人提起這把飯勺的事,我都覺得是在稱讚我,讓我很有面子。仔細一想,那把飯勺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撿到有用的東西,而且是因為我的努力而獲得的報償。
風 呂
我的故鄉湯之島現在已經成為天城湯之島町 的一部份,是伊豆半島有名的溫泉鄉,但我小時候,她不過是天城山麓一座默默無聞的村落罷了。因為村子的溪谷有天然湧泉,所以開了兩三家旅館,還有一棟私人別莊,以及兩處公共浴池。溫泉旅館也不像今天這樣規模宏偉,就是偶爾有馬車零星載一些客人來,分別投宿於這兩三家旅館,還沒有什麽團客。旅館的數目之所以用「兩三家」這種籠統的說法,那是因為其中有一家旅館時而開門營業,時而閉門歇業。每年秋末,宮內省 的官員都會來天城山進行一年一度的狩獵活動,旅館也只有這個時候熱鬧一下。村人們稱呼這場活動叫「御狩 (Okari)」。
村民在結束山上或田裡一天的工作,圍著火爐吃過晚餐後,就會提著燈籠,前往山谷的公共浴池。到了公共浴池一看,如果人滿為患,馬上轉往旅館或別莊的浴場。旅館是同村的人所經營,別莊也是由村裡的某人來管理,所以沒什麼好客氣的。這是因為在大家的觀念裡面,溫泉是來自大自然源源不絕的供應,並非人與人之間的取與關係。有人大喇喇從正門進去,有的則繞道庭院;還有人乾脆爬窗。
大人的情況一如上述,夏日溫泉旅館的浴場,白天則完全是小孩的天下。我們先到溪谷泡水,等身體泡凉了,就跳進旅館的浴場,在溫泉裡泡到熱乎乎的,又回到清涼的溪澗。對小孩子而言,公共浴池的溫泉和旅館的溫泉毫無分別。從溪流的上游玩到下游,每個小孩都一絲不掛,不斷更換遊戲場,一下跳進旅館的浴槽,一下泡公共浴池大池,或是到別莊的浴室玩水。
在年幼的記憶中,如果說有什麽畫面是帶著點妖異之感的,那就是村中男女混雜共浴的公共浴池的夜晚。基本上浴場是男女有別的,可人一多起來,男性就會走進女湯,而女性也會泡男湯。在這一點上倒是融通無礙得很。
小時候夜間公共浴池的混雜,令人難忘的並非視覺上的印象,而是無以名狀的冶豔氣息。以今天的說法,也許可以用「官能的」這樣的字眼。往那邊一靠也是滑溜溜,往這邊一貼也是滑溜溜。感覺就是置身於一堆柔軟、濕熱和滑潤的物體當中。
多年後當我翻開岸田劉生 所著《初期肉筆浮世繪》,看到裡面所收的「彥根屏風」、「慶長遊女遊戲屏風」和「慶長湯女之圖」等照相製版的風俗畫,立刻讓我回想起故鄉夜晚公共浴池的情景。「彥根屏風」或是慶長 風俗畫中那些身形扭曲妖嬈的大量裸女,在蒸汽氤氳的浴槽中若隱若現,簡直就是老家夜間浴場水氣繚繞的奇特氛圍寫照。立膝 而坐的女子,洗髮的女子,懷抱嬰兒的女子,互相刷背的女子。裡面有年輕女孩,也有中年婦人和老太婆。彼此的身體在水氣蒸騰中碰觸推攘。浴槽擠得滿滿的,沖洗場也到處是人。
當時五歲還是六歲的我,就在那一片軟膩滑溜中,一下浴槽、一下沖洗場的穿過來鑽過去。在沖洗場,鄰家務農的大嬸蹲著把我夾在她大腿之間。
——把眼睛閉緊哦。我要從頭上幫你淋熱水啦。
我一聽立刻將兩眼閉得死緊。
——好了。現在換背部,你轉過去。
說是要轉過身子,滑溜溜地還真是輕易轉不動呢。好不容易轉過身去,面對面就是佳乃奶奶,或是用輕石正在搓腳踵,或是拿絲瓜布刷身體。看佳乃奶奶那用力的樣子,真懷疑她會不會把皮給剝一層下來。
——身體洗好了,再進去浴槽泡一下。
我幾乎是半滑進浴槽的,然後馬上又陷入一堆柔嫩濕滑的東西裡面。不管面對哪個方向,碰到的都是柔軟的物事。摸到乳房,撞到腰,觸到背。慶長的泡湯女子們,就在我的周遭挨挨蹭蹭。
不過和「彥根屏風」或慶長風俗畫中女子不一樣的是,浴場蒸汽中的女子們都非常健康,皮膚緊緻。農家的少女或婦女們帶著泥土味的肉體,在熱氣中變得紅潤起來,互相推來擠去。
天冷的時候我是不去的,但春、秋兩季每到晚上,我就會跟著奶奶或鄰近農家的人們一起去公共浴池,脫光衣服露出瘦弱的身體,投身那些或蹲或坐的肉塊當中。
春天或秋天泡過溫泉起來身體也不會覺得冷的季節,我都是到走路十五分左右的溪谷公共浴池,但冬天多半使用放置土倉旁邊的帶灶浴桶。浴桶上面加了個簡陋的屋頂,照說下雨天入浴也不會有什麽問題,但下雨的日子,我會前往本家借用浴室。本家那邊在院子的井旁也設了一個帶灶浴桶,但這邊的屋頂做得非常完整。
在我小時候,村子裡家家戶戶都在屋子外頭放一台帶灶浴桶。土間 比較寬闊的農家,如果把浴桶擺在土間或許比較便利,但燒洗澡水時會讓房間裡面充滿黑煙。單圍爐裡燒柴薪的煙就夠嗆了,如果再加上燒洗澡水的煙,屋子裡每個人的眼睛一定都會眨個不停。
偶爾附近的農家會邀我們去泡澡。只有在熱水中特別加了苦橙皮或柚子皮 ,或是放進裝鹽的袋子 ,抑或投入藥草一起煮的時候,村人們就會互相邀約。
關於戶外露天浴桶的回憶,總是多少帶點悽愴之感。寒風吹襲的季節,從浴槽出來,一定是抱著衣物一絲不掛地跑回土倉。有時還有寒月高掛天上,我一邊看著月亮一邊踏進露天浴桶。
——水溫如何?
蹲在火口添柴的奶奶會問我。
——好燙!
我說。奶奶聽我這麼說,立刻前往六、七公尺開外小溪的汲水場,拿桶子裝水回來。
——水變涼了。
奶奶於是開始專心添加柴火。不久水從腳邊開始熱起來。
——太熱了!
——你把水攪一攪嘛。
攪沒幾下上面下面全都變得很熱。奶奶再度前往汲水。
到別人家泡澡的時候,就數泡鹽湯最樂了。腳底體驗鹽袋粗糙觸感的同時,還一邊用舌頭嚐嚐熱湯有多鹹。
——好鹹!
——不可以吞下去哦。等一下會讓媳婦溫甜酒給你喝的。
泡過鹽湯接著就是去土間再泡一下不帶鹽分的熱水,之後多半大家會坐到圍爐裡的邊上喝主人招待的甜酒。
泡湯的招待,不外來自母親娘家或鄰近的兩三戶農家,其中之一就是奧田 (Okuda) 家。從土倉的後門斜切走去,就會來到他們家置放農具的儲藏間前面。帶灶浴桶就放在儲藏間旁邊,前去泡澡時或是先到主屋把衣物脫掉,要不然就是直接在浴桶邊脫了,掛在附近的樹枝上。
現在我對奧田家主屋的模樣或是他們家的人都已經毫無印象,唯一記得的,就是一個名叫阿藏 (Okura) 的女性。那時她應該是幾歲呢?總之彷彿不幸的表徵般暗沉而呆滯的阿藏,還深深銘印在我腦海裡面。
關於她的事,我是直到讀小學時才聽說的。阿藏在少女時代曾經失蹤,去向不明,過了幾天才在天城山中找到,那時她已經變得癡呆了。以今天的說法,阿藏因為患了精神官能症而失蹤,幾天之後被發現時她已經變成一個精神失常的人。我上小學的時候,阿藏總是出現在我們家東北角上所建的水車磨坊那邊洗衣服或餐具。她從不跟任何人說話,不管什麽場合也絕對不笑。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出喜怒哀樂的反應,整天默默地工作。在小孩子眼中阿藏是個怪人,雖然心裡面瞧不起她,倒也不敢捉弄她。阿藏在我就讀中學期間過世,我想她那時大概五十左右吧。
現在回想一下,比起我小學時代所看到的阿藏,或是中學時代偶爾返鄉時不期而遇的阿藏,我總覺得五、六歲時在我稚嫩的心中留下的阿藏形影,才是真正的阿藏。
去奧田家泡澡時,阿藏總是彎腰蹲在火口前,不發一語地幫浴桶添柴火。主屋那邊大家都已經圍著餐桌熱鬧地吃晚飯了,但這一切都和阿藏無關,她依舊默默地屈身蹲在浴桶的火口前面。
就在這種狀態下,我曾經在浴桶中突然大聲哭喊起來。奶奶和其他人聞聲立刻從主屋跑過來,可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麽要哭,別人問我也答不出來。我只記得那種無以名狀的情緒。
現在想想,或許年幼的我,看到總是蹲在浴桶火口那異常暗沉而不幸的物體,就覺得殊值一掬同情之淚。小孩子內心的反射板,說不定比大人來得敏銳而纖細。我一定是為阿藏的人生感到悲哀才哭的吧。
關於浴場,還有一件事在我小時內心的反射板上也留下刻痕。
同樣是五、六歲前後發生的。我曾經到四公里外父親出生的地方住過一晚。那邊住的是父親的哥哥,亦即我的伯父,和他的家人,所以我去那裡過夜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可對奶奶而言,讓我離開她身邊,縱使只有一個晚上,也是不容易的。那次大概是伯父爲了什麽事過來土倉,臨走問我要不要跟他回去,我糊裡糊塗就說好,於是一起坐上了馬車。整件事前前後後我幾乎都忘光了,唯一記得的,是在伯父家前院洗澡的經過。
我被脫光衣服,坐在水盆裡面,伯母用手幫我擦洗淨身。那真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奇妙感覺。伯母只要一開口,就會露出一口大黑牙。那是用鐵漿染了色的牙齒 ,但在年幼的我眼中,伯母的臉跟鬼沒什麼兩樣。
我覺得我真是被帶到一個超乎想像的地方,想必我的表情也是繃的很緊。坐在水盆裡面擦澡這種淨身方式是第一次,讓鬼幫我洗澡也是第一次。
不時,會有各色人等來到正在淨身的我旁邊,然後離開。有時是個男人,有時則是女人;還有小孩也會過來。一無例外我每個都不認識。大家難得遇到這種場面,一邊竊竊私語關於我的事。或許他們和伯母之間進行了如下的交談。
——喲,哪來的少爺啊,這是?
——那是啊,剛剛,我們家老爺從湯之島帶回來的哩。
——哦,就是住土倉那位少爺嗎?
——是啊。
——過來走動走動挺好的。他是個很懂事的小孩呢。不過太瘦了點。像隻弱不禁風的小雞。
——住在庫房裡面,你看,跟個蔥白一樣。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置身一個熟人也沒有的異鄉。周遭一個熟面孔都沒有,而且放眼所看到的一切,無一不是陌生的異鄉風物。
被放在父親生家前庭洗澡的我,小小的心中其實充滿了複雜的情緒。既感到不安,也覺得後悔。看到伯母黑漆漆的牙齒我都快嚇死了,然後帶我回來的伯父不見蹤影,也讓我感到很詭異。不時出現在眼前的男男女女,也不知道他們是來幹嘛的。不過所有這一切,銘刻在我內心的總體印象就是,這裡是異鄉,而我是一個異鄉人。之後一直到今天,我沒有去過比那裡更陌生的異鄉,也從來沒有比那時更像個異鄉人了。
風 暴
颱風的季節,現在和過去並沒有什麽兩樣。每到夏末秋初時節,年年如此,就像彼此約好了一樣,暴風總是準時出現。如果九月沒來,十月肯定會來。一如二百十日或是二百二十日 這樣的說法,大家都確信暴風會如約到訪。
跟現在不一樣,那時的人並不會有颱風之卵在南方的珊瑚礁海域成形、孵化,漸次成長、壯大,然後朝日本列島北上這樣的觀念。當天空出現一些不尋常的徵兆,風勢也與平日有異,這時大人們心裡就會有迎接一場狂風暴雨的準備。風暴從天空的一角開始四處奔竄,如果哪個地方還沒吹到,好,那就去那裡給它翻攪一下,大概就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