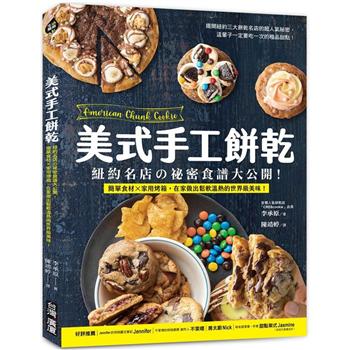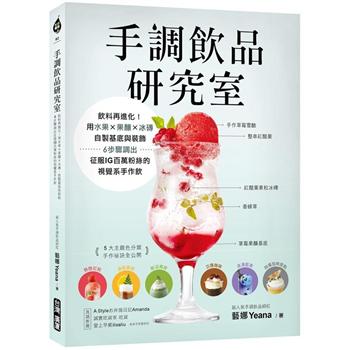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快樂的人看書並喝咖啡的圖書 |
 |
快樂的人看書並喝咖啡 作者:阿涅伊絲.馬丹-呂崗 / 譯者:邱瑞鑾 出版社:愛米粒 出版日期:2014-05-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快樂的人看書並喝咖啡
「他們下樓的時候在樓梯間裡嘻嘻鬧鬧,我後來聽說當卡車撞上他們的時候,他們還在車子裡玩鬧。我對自己說,他們死的時候是笑著的。我對自己說,我真恨不得跟他們在一起。」
黛安的丈夫和女兒在一次車禍中意外喪生,她從此一蹶不振,把自己封閉在家中,放棄了自已經營的一家名為「快樂的人看書並喝咖啡」的咖啡館的工作。除了她的心仍然跳動著之外,她周遭的一切都凝結不動。她執拗的封閉自己,痛苦的封閉起自己。在回憶之中迷了途,她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之道。
為了懷念她的丈夫柯藍,黛安決定帶著自己的過去逃避到愛爾蘭去。她會在哪裡找到重建自己的力量嗎?
作者簡介
阿涅伊絲.馬丹-呂崗Agnès Martin-Lugrand
本身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她以這部小說實現了她的作家夢。她自費出版了本書《快樂的人看書並喝咖啡》,立刻靠著口耳相傳,在所有的網路書店獲得了成功。請一起來閱讀這本在出版界造成不可忽視的現象的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