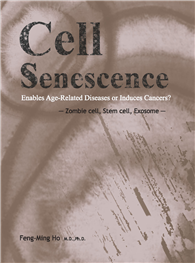十六字心傳
現在我們討論《孟子》最後一章〈盡心〉,這是孟子整個學術思想的中心,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孔孟心傳,是構成中國文化中心思想之一。這一貫的中心思想,絕對是中國的,是遠從五千年前,一直流傳到現在的,沒有絲毫外來的學說思想成份。所以後世特別提出,中國聖人之道就是「內聖外王」之道的心傳。歷史上有根據的記載,是在《尚書‧大禹謨》上,其中有舜傳給大禹的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一兩千年之後,到了唐宋的階段,就有所謂的「傳心法要」;這是佛學進入中國之前的一千多年,儒道兩家還沒有分開時的思想。當時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是因為得道;那時所謂道的中心,就是「心法」。
這十六字的心傳,含義非常廣泛。我國的文字,在古代非常簡練,一個字一個音就是一個句子,代表了一個觀念。外國文字,則往往是用好幾個音拼成一個字,或一個辭句,表達一個觀念。這只是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不同,而不是好壞優劣的差異。
中國古代人讀書,八歲開始讀書識字,這樣叫做「小學」,就是認字。例如「人」字,古文中怎樣寫?為什麼要這樣寫?代表什麼觀念?如何讀音?有時候,一個字代表了幾種觀念,也有幾種不同的讀音。所以中國的文字,任何學者、文豪,能認識二三千字以上的,已經是不得了啦!普通認得一兩千字就夠用了。外國文字則不然,每一新的事物,必須創造一個音、形皆不同的新字,所以現在外文的單字,以數十萬計。過去「小學」的基本功課,是先認識單字的內涵,其中有所謂「六書」的意義。什麼叫六書呢?就是「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這六種是中國傳統文字內涵的重點。現在讀書,已經不先研讀「小學」六書了,不從文字所代表的思想、觀念的含義打基礎,對於「小學」的教學,完全不再下基本功夫了。
「人心惟危」的惟字,在這裡是一個介辭,它的作用,只是把「人心」與「危」上下兩個辭連接起來,而本身這個惟字,並不含其它意義。例如我們平時說話:「青的嗯……山脈」這個拖長的「嗯……」並不具意義。至於下面的「危」字,是「危險」的意思,也有「正」的意思,如常說的「正襟危坐」的「危」,意思就是端正。而危險與端正,看起來好像相反,其實是一樣的,端端正正的站在高處,是相當危險的。也因為如此,外國人認起中國字來,會覺得麻煩,但真正依六書的方法,以「小學」功夫去研究中國字的人,越研究越有趣。如上一代章太炎這類的大師們,就具備了這種基礎功夫,鑽進去就不肯退出來。現代人寫的文章,不通的很多,連破音字都不懂,都用錯了。
《尚書》裡說「人心惟危」,就是說人的心思變化多端,往往惡念多於善念,非常可怕。那麼如何把惡念變成善念,把邪念轉成正念,把壞的念頭轉成好的念頭呢?怎麼樣使「人心」變成「道心」呢?這一步學問的功夫是很微妙的,一般人很難自我反省觀察清楚。如果能夠觀察清楚,就是聖賢學問之道,也就是真正夠得上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所以道家稱這種人為真人,《莊子》裡經常用到真人這個名辭;換言之,未得道的人,只是一個人的空架子而已。
人心轉過來就是「道心」。「道心」又是什麼樣子呢?「道心惟微」,微妙得很,看不見,摸不著,無形象,在在處處都是。舜傳給大禹修養道心的方法,就是「惟精惟一」,只有專精。堯舜所說的這個心法,一直流傳下來,但並不像現在人說的要打坐;或佛家說修戒、定、慧,以及道家說煉氣、煉丹修道那個樣子。
什麼叫做「惟精惟一」?發揮起來就夠多了。古人為了解釋這幾個字,就有十幾萬字的一本著作。簡單說來,就是專一,也就是佛家所說的「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或「一心不亂」,乃至所說的戒、定、慧。這些都是專一來的,也都是修養的基本功夫。後來道家常用「精一」兩個字,不帶宗教色彩。「精」、「一」就是修道的境界,把自己的思想、情感這種「人心」,轉化為「道心」;達到了精一的極點時,就可以體會到「道心」是什麼,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而這個「天」,是指形而上的本體與形而下的萬有本能。
得了道以後,不能沒有「用」。倘使得了道,只是兩腿一盤,坐在那裡打坐,紋風不動,那就是「唯坐唯腿」了。所以得道以後,還要起用,能夠作人做事,而在作人做事上,就要「允執厥中」,取其中道。怎麼樣才算是「中道」呢?就是不著空不著有。這是一個大問題,在這裡無法詳細說明,只能做一個初步的簡略介紹。
中國流傳的道統文化,就是這十六字心傳,堯傳給舜,舜傳給禹。後世所說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孔子的學生曾子、孔子的孫子子思,再到孟子,都是走這個道統的路線。以後講思想學說,也都是這一方面。但不要忘記,這個道統路線,與世界其他各國民族文化,是不同的,中國道統,是人道與形而上的天道合一,叫做天人合一,是入世與出世的合一,政教的合一,不能分開。出世是內聖之道,入世是外用,能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具體的事功貢獻於社會人類,這就是聖人之用。所以上古的聖人伏羲、神農、黃帝,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共祖,他們一路下來,都是走的「內聖外王」之道。
到了周文王、武王以後,「內聖外王」分開了,內聖之道就是師道,是傳道的人,外用之道走入了君道。其實中國政治哲學思想,君道應該是「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等於說君王同時是全民的領導人,也是教化之主,更是全民的大家長,所以說是政教合一的。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盡心 動心 知性 忍性
《孟子》全書快研究完了,從前面各章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孟子始終沒有出來做官,沒有擔任職務;他是以師道自居,指導當時的諸侯們,走上王道的政教合一之路,以達到人文文化的最高點。由於歷史的演變,人心的墮落,無可奈何,使他的這個願望落空了。不過他個人並沒有落空,他的光芒永存於千秋萬代,和其他的教主一樣,永不衰竭。
現在最後一章,是他在講完外用之道以後,講傳心的心法。孟子之所以成為聖人,因為他有傳心的心法,因此,〈盡心〉這一章書,非常重要。這一章以〈盡心〉為篇名,是以全章第一句話作題目,正是扼要點明重點之所在。
他一開頭就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這幾句話,就非常重要了,認真研究起來,十幾年也不能研究完,也許一輩子都鑽在其中了。
我們先從文字上研究,什麼叫做「盡心」?大家平常都會講的一句話:對這件事已「盡心」了;就是說,一件事情做完以後,成敗是另一問題,而去做的人,心總算盡到了。也就是用了所有的精神、心思去做,「盡」就是到底了、到盡頭了。依這個觀念來解釋孟子的話,就是我們把自心的作用,已反省觀察到底,然後可以發現人性是什麼了。
後來佛學進到中國,禪宗提倡的「明心見性」,也同這裡的「盡心知性」的觀念有關。佛學的《楞嚴經》所說的「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把明心與見性,分為兩個層次來解說。乃至玄奘法師所宏揚的唯識法相的最高成就「遣相證性」,也是把心與性分做兩個層次。孟子生活的時代,佛法還沒有進到中國,佛法正式進入中國,是在孟子之後八九百年到千年之間。
所以孟子是在佛法進來以前,就已經提出來先要「盡其心」,把自己心的根源找出來,然後才可以「知其性」。這是「明心見性」這個辭句的根源,能做「明心見性」;到了漢朝以後儒道分家了,道家叫做「修心煉性」。性要鍛煉,等於佛家禪宗所說的「就是這個」,得道是「這個」,跌倒是「這個」,爬起來也是「這個」。「這個」是什麼?說是悟了,就像一塊石頭裡面含有金子,也就是從金礦裡挖出來的石頭,裡面可能有金子。可是幾千億萬年,無數劫以來,金子被泥土裹住了,黃金和泥土混在一起,必須經過一番烈火的鍛煉,才能把光亮的黃金從中取出來,而將泥土──這些習氣,化為灰燼。所以道家說要「修心煉性」,先要修煉,在動心忍性或明心見性之間,不經過修煉是不行的。
儒家的修煉為「存心養性」,孟子這裡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的是什麼心?存一個仁心、善良之心,一個純淨無瑕,猶如萬里青天無片雲的天理之心。而養性,把人性原來善良的一面,加以培養、擴大、成長。所以後世儒家闡述,在起心應用上,要做到「親親,仁民,愛物」,這是儒家和佛家各自表述不同的要點。
佛法儒化 儒學佛化
儒家和佛家,在這方面,曾經發生過有趣的辯論。佛家指儒家這樣行仁道是不錯的,不過如果說想要成佛成道,還差一大截路。
可是儒家不接受這個說法,主張聖人做到了就是佛,佛也不過是聖人,雙方發生了辯論,實際上只是著手的工夫不同。儒家說,你們佛家,動輒講空,空到沒有捉摸處,下不了手,用不上力,只知道空;又沒有辦法使人類世界達到空,於是丟下這個世界不管,出家去了。這種只為一己修道,六親不認的做法,是不對的。
儒家又說,你們雖然講究慈悲,可是實施慈悲的下手方法也錯誤了。我們儒家則不然,我們講究仁,我們的慈悲有三部曲,是以「親親」為先,首先對自己的父母盡到了孝道,對自己的兒女慈悲。這些都做到了,再慈悲朋友的父母子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慈悲的對象範圍逐漸擴大到愛天下人,而成為「仁民」,視天下人都是自己的兄弟,都是同胞。這樣推己及人的工夫都做到了,於是「民胞物與」,最後是「愛物」,愛世界一切萬物,一步一步來。像你們這種慈悲,試問:假如釋迦牟尼佛站在河邊,孔子的母親與他的母親同時掉到河裡去了,請問釋迦牟尼先救誰?如果先將孔子的母親救起來,那是不孝;如果先把自己的母親救起來,照你們的說法,又是太不慈悲了,孔子的母親也是母親啊!
我們儒家的做法很簡單,假如站在河邊的是孔子,一定跳到河中,先救起自己的母親,然後再返身跳下去,救起釋迦牟尼的母親。這是非常簡單明瞭的事,也就是親吾親以及人之親。
這一套理論,佛家就很難置辯了。除非說,佛有神通,不必自己跳下水去,兩手向空中一抓,就同時把兩個母親救上來了。但是在儒家,先愛自己的父母,然後愛你的父母,你也愛我的父母,兩人共同愛兩人的父母,然後又共同愛第三人的父母,將這種愛,擴大、擴大、再擴大,於是擴大到仁民。所有人類都相親相愛,最後愛物,不但愛一切動物,甚至草木土石都愛。像你們佛家所說的,是無比的大,一上來就是一個空,反而落空了。
不知道誰的道理對,所以我不喜歡高談法理,如果做了法官,聽聽原告說的對,再聽被告說的也不錯,永遠也判決不了,這就是各說各有理。但是我們要注意,在中國的歷史上,歷代的高僧,都是先走儒家的路子,然後在佛法方面才能夠有所成就。即如近代的高僧印光法師,他的著作擺在我們眼前,文句多半出於儒家的精神,但他的教化則是佛家的,可以稱之為「佛法儒化,儒學佛化」了。虛雲老和尚也是如此,有儒道的底子,對儒家的學問也很透澈。再看明末佛家的四位大師:憨山、紫柏、蓮池、藕益,他們對儒家的學說,也是很深入的。
現在回轉來討論孟子的原意。孟子說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盡」是窮的意思,到頭了,到了極點。佛法中有句詩:「色窮窮盡盡窮窮,窮到源頭窮也空」,這是我的老師袁煥仙先生所作的詩,色相是空的,對它研究再研究,窮究再窮究,參空了,色相都是空的。空了也不對,「窮到源頭窮也空」,最後連空也丟掉了,說它空也好,不空也好,那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這就說明了「盡其心」就是窮其心,自己思惟、思惟、再思惟,正思惟到極點,心相的本體窮到了盡頭,就進到了空,然後見到了自性。見到了人性的自性以後,才見到了天性,就明白了形而上的性之體、形而下之用的本性。
這是孟子學問的中心。可見孔孟之道,不是隨便的,因為中國文化,古代文字的表達,喜歡簡練;外國的文字,喜歡分析、精詳,一個字,一個意義,在事理的表達上、處理上,也是演繹的。中華民族有一個奇特的民族性,對於太繁細的文字,不大喜歡看,越簡單越好,所以中國文字,在簡練中有深意。前面孟子所說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短短的十幾個字,就包涵了許多重要的人生修養的最高原則。
他又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這兩句話是講修養工夫的作用。「盡其心」,「知其性」,然後「知天」;而「存其心,養其性」是方法。要存什麼心?儒家的方法是隨時要存善念,所以後世的儒家說:「去人欲,存天理」,這就是至善之念。在古代,讀書人怎樣去具體實施呢?從前有一種「功過格」,在一張紙上畫許多格子,有的是三百六十格,一年用的,每天一格;也有一種是三十格,每月一張,一天一格;更有的是每天一張,上面有十二格,每個時辰一格。每天讀完書以後,要靜坐思過,有做錯的事,用墨筆在格中點一個黑點;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則用硃筆在格中點一個紅點,這樣天天反省。也有的是在口袋裡放了紅豆和黑豆,另外掛一個袋子,在書桌的旁邊,如果做了一件壞事,或者動了一個壞念頭,就投一顆黑豆子下去;如果做了一件好事,就投一顆紅色豆子。這樣一直反省到夏曆十二月二十三,灶君上天向玉皇大帝報告這家人的善惡前夕,就要自己去數紅黑點子或豆子。如果一年來,黑的多於紅的,就要在灶君面前跪下來,自己照數責打自己,而且第二年將是良心上不安的一年。這種反省功夫,做得非常嚴格,絕對不敢欺人或自欺,更不敢欺騙上天的神明。
所以「存其心」,就是每在起心動念、動心忍性之間,慢慢要做到善念的存心多。所謂「善則養心」,因為人在做了一件好事以後,心裡會很快樂,比做壞事害別人痛快得多,這就是「善則養心」的道理。「養其性」這個「性」,是習氣之性,養性就是把壞的習氣,慢慢變過來,變好了,變淨潔了。這種學問之道的修養,是「事天」的,侍奉天的。這個「天」是內在的天性,如信佛的人,也可以說是事佛天;信道教的人,可以說事道天,或者上天也可以,反正有這樣一個代名辭,代表一個看不見的無形力量。
現在講「心性」是兩層東西,還有一樣是「命」,這就厲害了,孟子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是短命而死,「壽」是活得長命。後世有一個界限,凡是未滿六十歲而死的,都稱「殀」,在訃文上,說到他的年齡時,只能說享「年」若干;滿了六十歲以後死亡,才能稱壽,說享「壽」多少年。
孟子這裡是說,一個人生下來,要想成為一個真正完整的人,在人生的學問修養上,隨時都要存心養性,而對壽命的長或短,應無所喜惡。縱然今日修這個道,做這種修養,明天就會死亡,也照樣繼續修下去,對生死問題,毫不考慮。正如孔子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天早晨懂了這個道,晚上死掉也可以;假如說修道而長壽,修養越高,壽命越長,也可以。
所以,「殀」也好,「壽」也好,要能生死無憂,就了卻了生死。這是唯一的不二法門,人生只有一條道路,生死不要被「殀」「壽」的觀念所困,非常豁達。真正的壽命,不是這個血肉之軀活得長短的問題,是有沒有明心見性的問題。明心見性了,就算明日死亡,也是不朽的;不明心見性,活千年也是白活。有人信其他宗教,或者信佛念佛幾十年,當他躺在病床上快死的時候,叫他放心拋開生死,安心祈禱或念佛,他卻說現在祈禱上帝也不靈了,佛也念不起來了。這就是因為沒有明心見性,弄錯了信仰上帝,信佛菩薩的真理。信上帝、信佛,並不是求此一血肉之軀的不死,而是要「修身以俟之」,是在明心見性以後,臨終即放棄這個血肉之軀,安然而去,這就是「立命」。
孟子教修身
以上三段,「盡心」「知性」「知天」是見地;「存心」「養性」「事天」是工夫;最後的「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則是行願。工夫達到了,生死已了,對於是殀是壽都無所謂了。
但是要注意,想要存心養性,必須「修身」。要注意這個「身」字;換言之,所謂「身」,就是由這個身體、五官、四肢、意識所表達出來的思想、觀念與言語、行為。至於怎樣「修身」,這裡他說「修身以俟之」,俟就是等待。等待什麼?等待那個命數,長壽也好,短壽也好,生也無所謂,死也無所謂。了知生死不相關,我只是把我自己的言語舉止、思想行為,時時處處事事都在道中,這樣建立了正命,等待自己命數盡頭的日子隨時到來。
如果把道家、佛家的見地、工夫、行願等修養方法,套上孟子上面這一段話,是可以寫一部專書的。
至於「命」,佛家不大管「命」的問題,佛家只管「正命」而活,不准自殺;自殺是非正命而亡,為戒律所不許。所以要正命而死,這和儒家一樣,要自然的命盡而死,自殺是犯戒的,也是罪過的。如何去修養正命呢?
後世道家就有性命雙修之說,到了宋代以後,道家與佛家,就因此而在修持方法上起了爭論。道家講「性命雙修」一派的人,認為中國唐朝以後信其他宗教的人,只修性不修命,因此說:「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但修祖性不修丹,萬劫陰靈難入聖」。這就是說,只修命不修性是不能成功的,但是只修性不修命的話,即使修億萬年,也不能得正果,所以性與命雙修才行。
佛家不承認這個說法,因為成道以後,證得菩提,是不生不滅,此命長存。這個命不是肉體的命,比肉體的命更偉大,那是儒家道家所說的「天命」,也就是兩家所共同承認,不生不滅的本體之性,所以叫做命。而所說孟子與盡心篇性命雙修的這個命,就是這個又稱做「丹」的命,是肉體之命,乃孟子所說的「修身以俟之」的「身」,為「身命」,後世又稱為「生命」。你這個身,是肉身,可以「殀壽不貳」,而我們不生不死的身,為法身,因此有法身、報身、化身的三身之說。
嚴格的說,形而上的最高哲學的性命之理,儒、道兩家是無法與佛家爭辯的,佛家分析精詳,歸納的結論也絕對是對的。而形而下的「修身以俟之」,乃至於起用,入世與出世的大乘精神,佛家不一定可以與儒、道兩家比。因為佛家空曠、空闊,看起來嚇人的大,蓋下來昏頭昏腦,行起來不著邊際,真是法海無邊,回頭是岸。岸在哪裡?照儒家的說法,法海無邊,回頭即在最近處,抓住一塊木板,慢慢漂流,終必靠岸的。所以他先抓住這個命,再找回到天命,那就不是這個肉體了。後世的道家與佛家的密宗修法,都是以這個肉體去修的。在這方面討論起來,又是一本大著作了。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這裡孟子所說的「正命」,又與後世道家所說「性命雙修」的「命」有所不同,而接近佛家大乘菩薩道的戒律。他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這是孟子在說明一切人的生命存在,生來自有固定的因緣。這也是大家困惑所要追問的問題。既然現有的生命,早已是命中注定,那又何必需要努力修為呢?這不是宿命論嗎?其實一般人所謂的宿命論,是認為自己的命運,被另外有個主宰已經定好了,無法改變。其實,這裡孟子所說的命,不是他力所定的宿命論。《詩經‧大雅•文王》早有「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的古訓,由此可見我們的傳統文化,素來都不是迷信宿命論的,而是要人人自求多福的。
這恰恰如同佛家所說的命,並非另外有個主宰,早早為你定構一生命運的模式。佛家所謂現有的命與過去、未來的因果關係,都是唯心自造,既非因緣也非自然,其中奧妙,一般人實在很難理解。所以佛家有幾句名言:
欲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生事 今生作者是
今生我們所受到的一切,都是前生的業力習性帶來,很難改變;若問來生如何,就看今生做了些什麼。在佛家的唯識學中,生命中帶來的過去的業力,名為種子,「種子起現行」,由種子發起現在的行為;「現行熏種子」,由現在一生行為的結果,又成了未來的種子。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就是三世因緣生法的道理,是佛法的透澈之處,真是天衣無縫。
我的理解也許還不到家,但我研究各宗教的哲學,都沒有辦法超越因緣所生法的原則。
但是,孟子所說的,只是現行的命,想要將我們這個現行的命改變,是可以做到的,不過必須行大善、至善,做到去惡為善,止於至善。這談何容易啊!有的人在某件事情上,雖然出了錢或出了力,但那是做給別人看的,不是真正行善;真正的行善,是不為人知的,也不一定能得到別人的了解,可能還被他人毀謗辱罵。對於這種情況,學佛的人就會想到《金剛經》上的話:「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就是說自我反省觀察過去生所造的惡業,到這生餘業未了,雖做好事,仍然得不到別人的首肯與讚賞。所以反而要感謝那些責罵、毀謗自己的人,因為他們的責罵與毀謗,使你的餘業果報早些消除了斷。
另有人懷疑,一件好事未做的人,還做了若干壞事,卻生活得那麼富裕康樂,這又是什麼道理?司馬遷在寫〈伯夷列傳〉中,也曾提出一個疑點:「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又說「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不過他寫這篇文章,對這類的困惑不作答案,只提一個問題,讓讀他
文章的人自己去思索。佛家的答覆很簡單:某人現世是壞人,但他之所以有如此好的境遇,是因為他前生善業所得的善報還沒有完;他現生所做的壞事,等到惡貫滿盈時自會結算。在我個人的人生經驗,佛法說的是對的,我看到許多人一生的經歷,報應非常快,好像比電腦計算還要快。其實許多人就是現世報,但是受報的人自己並不明白。所以中國社會,普通流行的有四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這是大家都愛說的。
以上內容節錄自《孟子與盡心篇》南懷瑾◎講述.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9869058827.pdf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孟子與盡心篇的圖書 |
 |
孟子與盡心篇 作者:南懷瑾講述 出版社: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2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2 |
二手中文書 |
$ 253 |
中國當代思潮 |
$ 253 |
社會哲思 |
$ 253 |
📌哲學79折起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中國哲學 |
$ 288 |
中國/東方哲學 |
$ 28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孟子與盡心篇
◎全球首次發行,南懷瑾老師最新談《孟子》重要著作。
◎講述旁徵博引,為南懷瑾老師集儒、道、釋思想大成的重要著作。
◎從「盡心知性談起」,進而論及領導、全民福利、教育、戰爭,乃至民本制度……等在現代社會之重要議題,重新審思傳統文化的意義與內涵。
〈盡心篇〉是《孟子》七篇中最後一篇,也是孟子思想的精髓。其中闡述了不少孟子學說的要義。以仁道論說,孟子認為仁道即是人道,人道則以心為中心,故盡其心即是整個仁道的本質;談到性與命,則說命功是由修養可得,性功需要識見透澈,將性命雙修的道理解釋地十分具體;同時更強調了內聖外王的儒者思想。
南懷瑾老師以他道貫古今的淵博學識,詮釋孟子學說,從基本的「動心忍性」,到「盡心知性」談起,進而論及現代社會十分重視的議題,如:管理問題、全民福利、教育、戰爭,乃至民本制度……等,更啟發人們重新省思傳統文化的內涵與意義。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
http://www.pressstore.com.tw/freereading/9789869058827.pdf
作者簡介:
南懷瑾 先生
一九一八年生於浙江省樂清縣,幼承庭訓,少習諸子百家。一生行跡奇特,常情莫測;四處奔波,化育無數。出版有儒、釋、道等各家五十多種著述,以其獨到的方式,引領新世代的人們植入文化的核心智慧,讓讀者更樂於瞭解歷史人文的博大精深。
先生二O一二年辭世,享年九十五歲。
章節試閱
十六字心傳
現在我們討論《孟子》最後一章〈盡心〉,這是孟子整個學術思想的中心,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孔孟心傳,是構成中國文化中心思想之一。這一貫的中心思想,絕對是中國的,是遠從五千年前,一直流傳到現在的,沒有絲毫外來的學說思想成份。所以後世特別提出,中國聖人之道就是「內聖外王」之道的心傳。歷史上有根據的記載,是在《尚書‧大禹謨》上,其中有舜傳給大禹的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一兩千年之後,到了唐宋的階段,就有所謂的「傳心法要」;這是佛學進入中國之前的一千多年,儒道兩家還沒有...
現在我們討論《孟子》最後一章〈盡心〉,這是孟子整個學術思想的中心,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孔孟心傳,是構成中國文化中心思想之一。這一貫的中心思想,絕對是中國的,是遠從五千年前,一直流傳到現在的,沒有絲毫外來的學說思想成份。所以後世特別提出,中國聖人之道就是「內聖外王」之道的心傳。歷史上有根據的記載,是在《尚書‧大禹謨》上,其中有舜傳給大禹的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一兩千年之後,到了唐宋的階段,就有所謂的「傳心法要」;這是佛學進入中國之前的一千多年,儒道兩家還沒有...
»看全部
作者序
【推薦序】
《孟子》的〈盡心〉篇,是全書的最後一篇,也是全部《孟子》的結論,更是《孟子》的重要中心思想。
孟子認為,仁道就是人道,而人道是以心為中心的,所以盡其心就是這個道。
孟子講到性與命的問題,命功是由修養可得;而性功則要識見透澈,屬於智慧方面的成就。
孟子將性與命雙修的道理,解釋得十分具體,十分透澈;更將內聖外王之學,表達得充分無遺。
在這一篇中,孟子更說到民主的問題,所謂的「民為貴」,並不是民為主;孟子的思想,是以民主為基礎,而以君主制度,實施民主精神的管理。
孟子這種想法,似乎是以民為本的,...
《孟子》的〈盡心〉篇,是全書的最後一篇,也是全部《孟子》的結論,更是《孟子》的重要中心思想。
孟子認為,仁道就是人道,而人道是以心為中心的,所以盡其心就是這個道。
孟子講到性與命的問題,命功是由修養可得;而性功則要識見透澈,屬於智慧方面的成就。
孟子將性與命雙修的道理,解釋得十分具體,十分透澈;更將內聖外王之學,表達得充分無遺。
在這一篇中,孟子更說到民主的問題,所謂的「民為貴」,並不是民為主;孟子的思想,是以民主為基礎,而以君主制度,實施民主精神的管理。
孟子這種想法,似乎是以民為本的,...
»看全部
目錄
出版說明
十六字心傳
盡心 動心 知性 忍性
佛法儒化 儒學佛化
孟子教修身
什麼是正命
你想得樂嗎
誰有慚愧心
賢君賢士最平凡
先窮後達的那個人
有我 無我
凡民與豪傑的區別
誰是好領導
人性的良知良能
人的等別
君子有三樂
養老與全民福利
傳統農業稅的問題
孔子登山 孟子觀水
王與賊 自利與利他
關於子莫執中
成功與成名不同
王道與霸道
歷史記錄的果報
尸位素餐
居仁由義之道
環境的影響 君子的愛心
兩個故事 三個論點
孟子的教學方法
何謂尊師重道
進步快 退步更快
關於服喪
聖賢事業
歷史難讀
且看剃頭者 人亦剃其頭
民為貴...
十六字心傳
盡心 動心 知性 忍性
佛法儒化 儒學佛化
孟子教修身
什麼是正命
你想得樂嗎
誰有慚愧心
賢君賢士最平凡
先窮後達的那個人
有我 無我
凡民與豪傑的區別
誰是好領導
人性的良知良能
人的等別
君子有三樂
養老與全民福利
傳統農業稅的問題
孔子登山 孟子觀水
王與賊 自利與利他
關於子莫執中
成功與成名不同
王道與霸道
歷史記錄的果報
尸位素餐
居仁由義之道
環境的影響 君子的愛心
兩個故事 三個論點
孟子的教學方法
何謂尊師重道
進步快 退步更快
關於服喪
聖賢事業
歷史難讀
且看剃頭者 人亦剃其頭
民為貴...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南懷瑾講述
- 出版社: 南懷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5-22 ISBN/ISSN:978986905882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92頁 開數:菊16開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