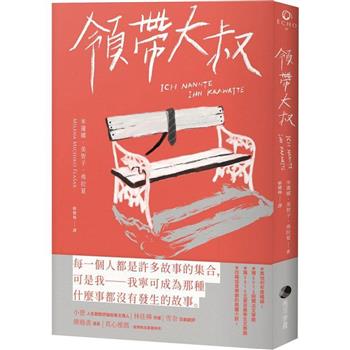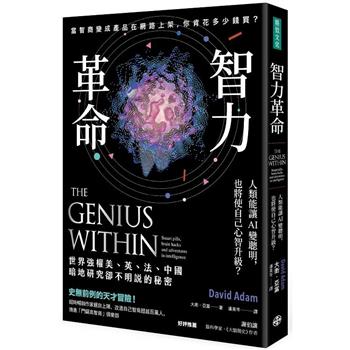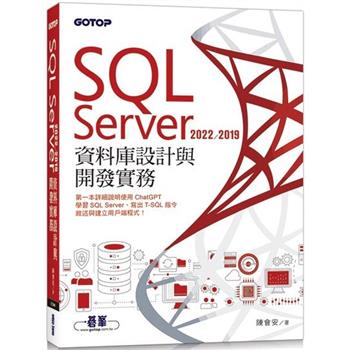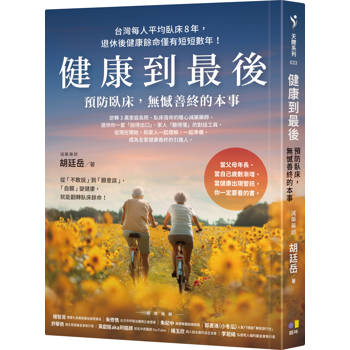林道生是花蓮重要音樂教育家和作曲家,他深入原住民部落採集傳統歌謠,並以此為基底,創作室內樂、協奏曲等曲式。2012年林道生獲頒花蓮縣文化薪傳獎特別貢獻獎,肯定他對原住民文化保存、傳承與弘揚的付出。
本書以林道生之生命史研究,試圖理解這位後山不平凡的音樂家,如何透過自學,踏上音樂創作之路。由歷史脈絡下觀察,「戰爭期世代」的作曲家,在不同生命階段,個人採取的適應策略,進而確立自我創作風格。
本研究認為,1950年代以來,林道生的創作核心由民族精神的反共愛國歌曲,隨現代主義移入後的無調性現代音樂,逐漸轉為中國文化圈下的民族音樂,最後發展出關注臺灣為主體的愛鄉歌曲。這幾段時期依序相互疊合、扣連,並互為影響。
林道生之作曲強調各族群之文化內涵,以音樂語言傳達對臺灣的關懷。她的創作歷程,記述臺灣音樂史的流變,其多元豐富的作品風格,更為臺灣音樂史譜下不朽的樂章。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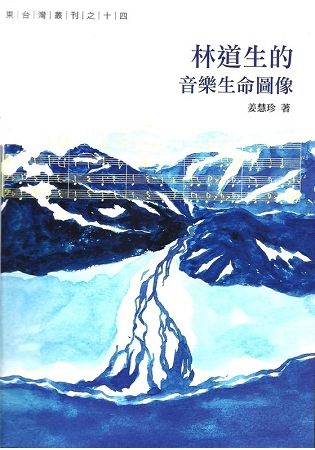 |
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 作者:姜慧珍 出版社: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 出版日期:2018-07-3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69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全彩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
內容簡介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後山移民音樂家的傳奇人生
第二節 探向生命的路徑
第三節 文獻回顧
第四節 章節架構與研究限制
第二章 兩個國族教育的思想啟蒙
第一節 皇民化的童年與國民學校
第二節 去日本化與花蓮師範學校時期
第三節 美崙溪畔的教學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愛國歌曲和現代音樂創作
第一節 軍中文藝初試啼聲
第二節 「飽命」與「保命」的創作
第三節 亞洲作曲家聯盟與現代化衝擊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民族音樂中的他者與自我
第一節 原住民音樂與神話寫作
第二節 音樂與文學的交會
第三節 音樂著述建構的創作脈絡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一:林道生之大事記年表
附錄二:林道生音樂作曲年表
第一節 後山移民音樂家的傳奇人生
第二節 探向生命的路徑
第三節 文獻回顧
第四節 章節架構與研究限制
第二章 兩個國族教育的思想啟蒙
第一節 皇民化的童年與國民學校
第二節 去日本化與花蓮師範學校時期
第三節 美崙溪畔的教學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愛國歌曲和現代音樂創作
第一節 軍中文藝初試啼聲
第二節 「飽命」與「保命」的創作
第三節 亞洲作曲家聯盟與現代化衝擊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民族音樂中的他者與自我
第一節 原住民音樂與神話寫作
第二節 音樂與文學的交會
第三節 音樂著述建構的創作脈絡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一:林道生之大事記年表
附錄二:林道生音樂作曲年表
序
推薦序
潘繼道
撰寫人物的生命史很難,因為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包括家庭、社會、國家及個人的生境遇,會給予不同的經驗。而其自身心路歷程的轉變,有時也不一定會跟隨著代而走。然而如果要書寫跨越時代,且又是創作、著作等身的音樂作曲家兼教育家,則又更難下筆。因為其人生經歷不同政權的教育,有著不同的被統治經驗,其創作的歷程與豐富的作品,使得生命史更是不容易去探索。
本專書的主角林道生老師,雖然不是出身於後山花蓮,但從他跟隨父母親由彰化搬到花蓮之後,從此他鄉變故鄉,接觸到花蓮的多族群與多元文化,並慢慢地展開他的音樂創作旅程。2012年為肯定他對原住民文化保留、傳承與弘揚地付出,花蓮縣文化局更頒發「花蓮縣文化薪傳獎特別貢獻獎」。
林老師接受過日治時期皇民化的初等教育,與戰後國民黨中國化、去日本化、反共抗俄的精神教育,兩種截然不同的國族主義教育體制,使他必須趕緊自我調整以因應變化。
除了家裡給予的教育與薰陶之外,其並未受過完整的音樂訓練,在花蓮師範學校就學期間,慢慢地發現自己有音樂的天分;而在接觸到張人魔老師之後,初步參與臺灣原住民音樂的採集,而這樣的經驗其後在玉山神學院任教時更加地被他發揚光大。在他田野調查及閱讀相關文獻之後,因為對原住民文化、生命哲學有更深一層認識,及自身對原住民文化的尊重,林老師在創作時,更能將原住民歷史文化等元素融合在歌曲當中。
軍中服役的經歷與面對戒嚴時期胞弟無端遭羅織思想罪名入獄,在「飽命」與「保命」的現實考量下,林老師創作了非常多的愛國歌曲,逐漸打開知名度;「曲盟」則對他提供自學、觀摩和發表的機會,也醞釀他深邃且自由的樂曲芬芳。2000年後,林老師更與花蓮在地的文人合作,使他的作品呈現更加多元。他的作品也關注時事、結合時事,且將父親林存本互動的好友賴和的作品加以編劇,完成《賴和詩作歌曲集》。
林老師的人生經歷豐富,其創作、著作又非常多元,除非與他建立一定的信賴關係,並能細心聆聽、整理其口述歷史,耙梳其紙本創作者,才能較接近地呈現這位花蓮在地的音樂家,而慧珍就是以她對文字掌握的敏感度、細膩流暢的書寫功力,加上她在碩士班就學期間的歷史專業訓練,將林老師的生命史放在臺灣整體的大歷史中作對話,以〈兩個國族教育的思想啟蒙〉、〈愛國歌曲和現代音樂創作〉、〈民族音樂中的他者與自我〉等章節,並藉由與林老師共同參與研究的方式,使不同時期、不同階段林老師生命史的發展、形貌,儘可能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慧珍撰寫時考證用心,文字極為順暢,引述不少林老師的訪談記錄,其生動的敘述,彷彿林老師就站在眼前跟我們談他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
慧珍是我在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班指導的研究生,第一次接觸到她的名字,是協助花蓮縣文化局審查她所主筆、編輯的《花蓮縣2014全國古蹟日導覽手冊──時光旅行》時,當時覺得她的文筆流暢優美,能將田野、口述的資料與文獻作結合,透過圖像與文字使作品完美地呈現出來。接著,慧珍申請入學,成為系上的研究生。上課期間,慧珍非常認真,對於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的相關課程都有修讀,遇到疑問時會打破沙鍋問到底,不只是上課時間會把握機會討論,下課後回到家也會寫信來詢問,以獲得解答。
在指導她寫作論文期間,她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又要照顧一對子女,課業、家庭、工作要同時兼顧,非常的辛苦。還記得花蓮縣文化局《花蓮縣2015全國古蹟日導覽手冊──走街串巷老花蓮》,又由慧珍工作的公司承接撰寫的任務,期間她的女兒生病住院,蠟燭多頭燒,跟我約好時間要訪談日治時期花蓮港廳的官營移民村、新城神社相關發展歷史時,累得睡過頭了而急忙跑來,她是個非常負責任卻又容易緊張的人,到達的時候連忙道歉;我只是擔心她累壞了,要她放輕鬆,因為一邊工作、一邊唸書,又遇到家人病倒需要照顧時,心中的煎熬是可以體諒的。
臺灣的歷史,絕不是只有政治人物或是政治發展的記錄,臺灣各個在地音樂作曲者、教育者、臺籍日本兵、工藝家、企業家、運動員……,他們的生命史將可充實我們對臺灣史如實的認識,因為這些在地人物的境遇,因應大環境的身心調適,更貼近人民對臺灣這塊土地的記憶。
慧珍的碩士學位論文獲得東台灣研究會出版審查通過,並得到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獎助出版,為人師者的喜悅莫過於此。其實,慧珍撰寫的過程中我獲益更多,更能從她的論文中以不同的視野理解、學習臺灣史。
我個人專長不是音樂史,幸運地系上相關專長的老師能適時予以協助,使慧珍論文撰寫時能夠更加嚴謹。當然,提供文獻與口述資料、共同參與研究與慧珍「視域融合」的林道生老師是最大的貢獻者,因為林老師的信任、無私地提供各項資料,使慧珍的研究成為可能,並最後撰寫完成及出版。原先希望由林老師撰寫推薦序,因為他才是真正的功勞者,又是音樂界、教育界的前輩,我只不過是修改文字錯誤、提醒慧珍注意史料的正誤與論文的格式而已,但林老師非常客氣謙虛的說:「還沒看過自己推薦自己的文章,怪怪地。」因而由我代為寫這篇推薦序。
《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一書即將出版問世,對於記錄東臺灣歷史、記錄東臺灣在地音樂家的生命史,可說是極有意義之事。希望這是慧珍階段性研究的結成與再出發,期盼她對東臺灣的研究繼續著力,對臺灣史研究與臺灣奉獻心力,企盼不久的將來也能見到更多的研究出版。
潘繼道
2018.5.5
作者序
姜慧珍
第一次採訪林道生老師,主題是童年的美崙溪印象,他提到就讀明治國民學校,在美崙溪上游泳課、同學抓溪裡的小魚塞進嘴裡當零食的趣事;北濱街小孩偷挖日本人種的地瓜被發現,大家急忙跑向臨港線鐵路橋,從橋上撲通撲通跳進美崙溪逃跑。他的談吐風趣,我笑得臉都僵了,邊寫採訪稿還禁不住捧腹大笑。事後我厚著臉皮徵詢林老師:我有榮幸為您寫回憶錄嗎?
拜工作之賜,我很幸運的能聆聽不同的人生故事。採訪常是短短二小時不到,隨著受訪者步履,經歷他們分享和述說的生命風景,笑中帶淚,受益最多的往往是我。
生命史研究無異是最貼近另一個生命的經驗,而我再次幸運的,與花蓮知名的音樂家林道生老師重新走過日治後期到21世紀的今天,穿越八十多年,以他的視角認識故鄉過往。
二年多的研究過程,承蒙林老師撥冗協助進行口訪,以及對我的高度信 任,提供寶貴的一手史料,並時常主動e-mail文稿、照片和突然想起來的重要事件。甚至審閱論文初稿時,直接改好電子檔回傳,對於年逾八旬的長者如此付出,令後學感激萬分。
感謝論文口試委員李宜憲老師悉心指點錯誤,陳鴻圖老師在歷史專業和書寫結構的寶貴意見。研究所修業期間,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郭俊麟老師引導我進入學術思維,李世偉老師為人生問題解惑,郭澤寬老師在音樂和文學領域的精闢見解,以及中研院民族所黃宣衛老師指導如何建構出研究脈絡等,都讓我的研究所生涯豐富而扎實。
論文寫作過程,花蓮縣文化局圖資科楊淑梅科長、黃偲婷小姐,協助文獻查找;本系妃澤、家渝幫忙相關行政流程,學弟妹鴻瑋、芝菁、冠翰一路走來相互鼓勵。修業期間,更因任職公司負責人林景川先生的包容,使我放心完成研究。
論文指導教授潘繼道老師則是我內心安定的力量,再多挫折,只要老師一出手,都能化阻力為助力;更要感謝東台灣研究會與曹永和文教基金會,使拙作碩論有機會出版專書,內容或有諸多不足與缺漏之處,皆因我的研究和書寫火候仍有待努力。
文稿最後校對時,正好聽到周杰倫的《青花瓷》,歌詞有一句「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想必我和林老師,以及指導老師們,應是累積幾世的緣,因緣具足了,才得以成就這本書的出版。
潘繼道
撰寫人物的生命史很難,因為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包括家庭、社會、國家及個人的生境遇,會給予不同的經驗。而其自身心路歷程的轉變,有時也不一定會跟隨著代而走。然而如果要書寫跨越時代,且又是創作、著作等身的音樂作曲家兼教育家,則又更難下筆。因為其人生經歷不同政權的教育,有著不同的被統治經驗,其創作的歷程與豐富的作品,使得生命史更是不容易去探索。
本專書的主角林道生老師,雖然不是出身於後山花蓮,但從他跟隨父母親由彰化搬到花蓮之後,從此他鄉變故鄉,接觸到花蓮的多族群與多元文化,並慢慢地展開他的音樂創作旅程。2012年為肯定他對原住民文化保留、傳承與弘揚地付出,花蓮縣文化局更頒發「花蓮縣文化薪傳獎特別貢獻獎」。
林老師接受過日治時期皇民化的初等教育,與戰後國民黨中國化、去日本化、反共抗俄的精神教育,兩種截然不同的國族主義教育體制,使他必須趕緊自我調整以因應變化。
除了家裡給予的教育與薰陶之外,其並未受過完整的音樂訓練,在花蓮師範學校就學期間,慢慢地發現自己有音樂的天分;而在接觸到張人魔老師之後,初步參與臺灣原住民音樂的採集,而這樣的經驗其後在玉山神學院任教時更加地被他發揚光大。在他田野調查及閱讀相關文獻之後,因為對原住民文化、生命哲學有更深一層認識,及自身對原住民文化的尊重,林老師在創作時,更能將原住民歷史文化等元素融合在歌曲當中。
軍中服役的經歷與面對戒嚴時期胞弟無端遭羅織思想罪名入獄,在「飽命」與「保命」的現實考量下,林老師創作了非常多的愛國歌曲,逐漸打開知名度;「曲盟」則對他提供自學、觀摩和發表的機會,也醞釀他深邃且自由的樂曲芬芳。2000年後,林老師更與花蓮在地的文人合作,使他的作品呈現更加多元。他的作品也關注時事、結合時事,且將父親林存本互動的好友賴和的作品加以編劇,完成《賴和詩作歌曲集》。
林老師的人生經歷豐富,其創作、著作又非常多元,除非與他建立一定的信賴關係,並能細心聆聽、整理其口述歷史,耙梳其紙本創作者,才能較接近地呈現這位花蓮在地的音樂家,而慧珍就是以她對文字掌握的敏感度、細膩流暢的書寫功力,加上她在碩士班就學期間的歷史專業訓練,將林老師的生命史放在臺灣整體的大歷史中作對話,以〈兩個國族教育的思想啟蒙〉、〈愛國歌曲和現代音樂創作〉、〈民族音樂中的他者與自我〉等章節,並藉由與林老師共同參與研究的方式,使不同時期、不同階段林老師生命史的發展、形貌,儘可能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慧珍撰寫時考證用心,文字極為順暢,引述不少林老師的訪談記錄,其生動的敘述,彷彿林老師就站在眼前跟我們談他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
慧珍是我在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班指導的研究生,第一次接觸到她的名字,是協助花蓮縣文化局審查她所主筆、編輯的《花蓮縣2014全國古蹟日導覽手冊──時光旅行》時,當時覺得她的文筆流暢優美,能將田野、口述的資料與文獻作結合,透過圖像與文字使作品完美地呈現出來。接著,慧珍申請入學,成為系上的研究生。上課期間,慧珍非常認真,對於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的相關課程都有修讀,遇到疑問時會打破沙鍋問到底,不只是上課時間會把握機會討論,下課後回到家也會寫信來詢問,以獲得解答。
在指導她寫作論文期間,她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又要照顧一對子女,課業、家庭、工作要同時兼顧,非常的辛苦。還記得花蓮縣文化局《花蓮縣2015全國古蹟日導覽手冊──走街串巷老花蓮》,又由慧珍工作的公司承接撰寫的任務,期間她的女兒生病住院,蠟燭多頭燒,跟我約好時間要訪談日治時期花蓮港廳的官營移民村、新城神社相關發展歷史時,累得睡過頭了而急忙跑來,她是個非常負責任卻又容易緊張的人,到達的時候連忙道歉;我只是擔心她累壞了,要她放輕鬆,因為一邊工作、一邊唸書,又遇到家人病倒需要照顧時,心中的煎熬是可以體諒的。
臺灣的歷史,絕不是只有政治人物或是政治發展的記錄,臺灣各個在地音樂作曲者、教育者、臺籍日本兵、工藝家、企業家、運動員……,他們的生命史將可充實我們對臺灣史如實的認識,因為這些在地人物的境遇,因應大環境的身心調適,更貼近人民對臺灣這塊土地的記憶。
慧珍的碩士學位論文獲得東台灣研究會出版審查通過,並得到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獎助出版,為人師者的喜悅莫過於此。其實,慧珍撰寫的過程中我獲益更多,更能從她的論文中以不同的視野理解、學習臺灣史。
我個人專長不是音樂史,幸運地系上相關專長的老師能適時予以協助,使慧珍論文撰寫時能夠更加嚴謹。當然,提供文獻與口述資料、共同參與研究與慧珍「視域融合」的林道生老師是最大的貢獻者,因為林老師的信任、無私地提供各項資料,使慧珍的研究成為可能,並最後撰寫完成及出版。原先希望由林老師撰寫推薦序,因為他才是真正的功勞者,又是音樂界、教育界的前輩,我只不過是修改文字錯誤、提醒慧珍注意史料的正誤與論文的格式而已,但林老師非常客氣謙虛的說:「還沒看過自己推薦自己的文章,怪怪地。」因而由我代為寫這篇推薦序。
《林道生的音樂生命圖像》一書即將出版問世,對於記錄東臺灣歷史、記錄東臺灣在地音樂家的生命史,可說是極有意義之事。希望這是慧珍階段性研究的結成與再出發,期盼她對東臺灣的研究繼續著力,對臺灣史研究與臺灣奉獻心力,企盼不久的將來也能見到更多的研究出版。
潘繼道
2018.5.5
作者序
姜慧珍
第一次採訪林道生老師,主題是童年的美崙溪印象,他提到就讀明治國民學校,在美崙溪上游泳課、同學抓溪裡的小魚塞進嘴裡當零食的趣事;北濱街小孩偷挖日本人種的地瓜被發現,大家急忙跑向臨港線鐵路橋,從橋上撲通撲通跳進美崙溪逃跑。他的談吐風趣,我笑得臉都僵了,邊寫採訪稿還禁不住捧腹大笑。事後我厚著臉皮徵詢林老師:我有榮幸為您寫回憶錄嗎?
拜工作之賜,我很幸運的能聆聽不同的人生故事。採訪常是短短二小時不到,隨著受訪者步履,經歷他們分享和述說的生命風景,笑中帶淚,受益最多的往往是我。
生命史研究無異是最貼近另一個生命的經驗,而我再次幸運的,與花蓮知名的音樂家林道生老師重新走過日治後期到21世紀的今天,穿越八十多年,以他的視角認識故鄉過往。
二年多的研究過程,承蒙林老師撥冗協助進行口訪,以及對我的高度信 任,提供寶貴的一手史料,並時常主動e-mail文稿、照片和突然想起來的重要事件。甚至審閱論文初稿時,直接改好電子檔回傳,對於年逾八旬的長者如此付出,令後學感激萬分。
感謝論文口試委員李宜憲老師悉心指點錯誤,陳鴻圖老師在歷史專業和書寫結構的寶貴意見。研究所修業期間,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郭俊麟老師引導我進入學術思維,李世偉老師為人生問題解惑,郭澤寬老師在音樂和文學領域的精闢見解,以及中研院民族所黃宣衛老師指導如何建構出研究脈絡等,都讓我的研究所生涯豐富而扎實。
論文寫作過程,花蓮縣文化局圖資科楊淑梅科長、黃偲婷小姐,協助文獻查找;本系妃澤、家渝幫忙相關行政流程,學弟妹鴻瑋、芝菁、冠翰一路走來相互鼓勵。修業期間,更因任職公司負責人林景川先生的包容,使我放心完成研究。
論文指導教授潘繼道老師則是我內心安定的力量,再多挫折,只要老師一出手,都能化阻力為助力;更要感謝東台灣研究會與曹永和文教基金會,使拙作碩論有機會出版專書,內容或有諸多不足與缺漏之處,皆因我的研究和書寫火候仍有待努力。
文稿最後校對時,正好聽到周杰倫的《青花瓷》,歌詞有一句「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想必我和林老師,以及指導老師們,應是累積幾世的緣,因緣具足了,才得以成就這本書的出版。
姜慧珍 謹識
2018.05.06
2018.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