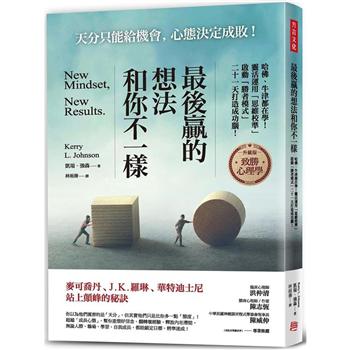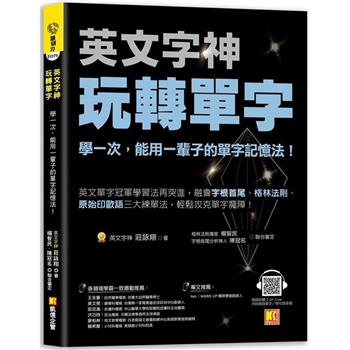是誰說過,男人最招架不住的,
不是成熟女人的魅力和手段,而是女人不經意表露的天真。
不是成熟女人的魅力和手段,而是女人不經意表露的天真。
經歷離婚的巨浪,為了重新找回自己的價值,毅然決然回到出生地的曉蕾,在與初戀情人重逢的當下,勾起藏在心底深處的已然涸竭愛戀之心……
「一夜情之後,妳要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好朋友──與她的丈夫?」
集美麗與優雅於一身的曉蕾,在經歷過風風雨雨後,是否能夠緊緊抓住企圖逃離她的愛人……
有著女人成熟嫵媚的迷人外表的曉蕾,同時擁有著女孩天真爛漫的心思。外表光鮮亮麗人人稱羨的她,內心的孤獨,卻只有電話另一端的人知道。
和暗戀已久的男人結婚,步入家庭相夫教子的芝芝,原以為所追求的不過是平凡幸福的生活,直到曉蕾再次出現,才開始明白所渴求的「安定」不過是自己過度理想化。
蔣瓊安,看似擁有普世人們夢寐以求的生活,然而她知道,這一切的一切看似平衡,卻是如履薄冰。僅有利用手段達成所要的成就,才能彌補缺失的心靈角落。
三個女人,交織出美麗的網,既強韌又脆弱。
愛情在她們心中的看法不同,卻又相似的讓人心疼。
寂寞,是因為孤獨所以存在,還是因為所愛之人無法回應同等的愛?
──我好像一直生活在夢裡,現在才看到,現實原來不是那麼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