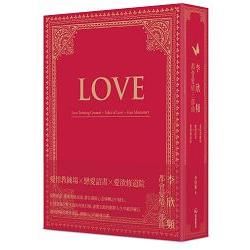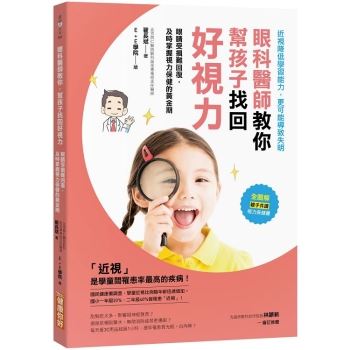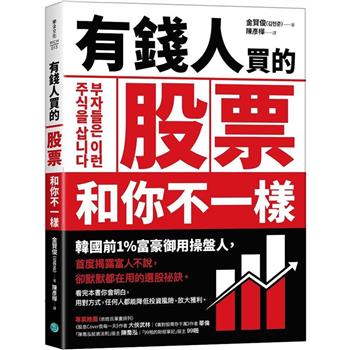《戀愛詔書》推薦序之一
三十單身的極至異想
看到欣頻這本結集自報紙、雜誌的書寫文字,我彷彿更深刻地看見了這個時代裡,某一個年齡層的都會女人面貌。
當然,欣頻無疑是她們更極致的放大——藉著她過人的聰慧,她彷彿全身毛細孔全開的敏銳觀察與感受力,她大女人的本質中同時存在的小女人的幽默與戲謔,以及她操控得如此自在寫意的文字書寫能力。
透過這些,欣頻淋漓盡致地寫出生活在這個時代,一個「三十單身」都會女子的生活、想法和心情:她狂戀旅遊,借著向世界出發的行程,尋找未知或未識的自己;她在都會裡耽欲並且修行,在人世與出世裡,隨心情自在變換遊移;她逆轉女人在愛欲世界裡的柔弱被動,如女王般頒下戀愛詔書,欽點各種不同功能的情人,同時也對現代男人做一番揶揄與嘲諷……
看著這些文字,我想起多年前當《荒人手記》出版時與朱天文的訪談。她談及自己的一個觀察與思索:原本物種的天性是在成年後就要走進孕育下一代的階段——開始將時間、金錢、精力花費在養育下一代上面。但是當這些人少了這一塊,於是便將這些時間、精力、金錢拋擲在「耽美」之上……
在某個層面來說,「三十單身」的現代女人不也是如此?
經濟獨立,又不需要照顧一個新的家庭或者小孩的她們,開始擁有一段延長了的單身時間。於是,向內,她們探尋潛藏的、未識的自己;向外,她們延展生活的各種可能性,例如欣頻的氣功課、中醫課、自我設定的一日角色扮演遊戲。她們「耽美」、「耽生活」,同時也「耽自己」——無論向內向外,她們其實都是在拉長了的與自己獨處的時間裡,企圖尋找真實的自己,並與自己深刻對話。
已經離開了「三十單身」的我,有時不免還是會羡慕起這些姐妹的無盡自由和無限的可能性,尤其是像欣頻這樣,羽翼未剪,甚至越來越強壯延展,就是一片無盡的人生新風景。不過還好有文字,透過這個奇妙的媒介,欣頻記錄下她眼前腦中變幻莫測的世界,也讓我們得以窺視分享這個外冷內熱的女獅子豐富奇異的異想世界。
胡慧嫚(雜誌總編輯)
《戀愛詔書》推薦序之二
戀愛語言解碼器
要有多大的學問才可以寫辭彙?要有多少毅力才能在年輕時就已出版數十本創作?
從李欣頻的第一本著作《誠品副作用》到現在,她一直給我們撲朔迷離,創造力十足,幻想豐富的文字風貌。其中有愛、有恨,充分展現了文字的魅力。細讀她的作品,不難體會一位文采豐富的創作者,其中的艱辛折騰歷程。尤其對於愛情的描述,精闢入埋,有時文字格調的脫俗與扭轉,令人忍不住捏把冷汗。這是上天對我們的恩寵,讓我們閱讀,滿足對文字瘋狂的慾望。李欣頻也不負眾望的經常給讀者驚奇。現在沒有血淚,修道院關門,料理已賣光,詔書已典藏起來,奉上一本《戀人常用辭彙160句》,請君翻閱,資格不限。
要瞭解李欣頻的作品,就要先瞭解她的愛情觀。
她是極為聰慧的都會女子,有夢想也有愛情。但更有所堅持與執著。
【我們去看夜景!】
所有浪漫的城市愛情故事,都是去看夜景,然後看到流星後,開始做夢的……我有外套,我有臂膀,我有體溫幫你取暖。你已經被我載到無人的深山上,你要轉身叫計程車回家可就沒那麼容易!
有時讀完她的作品,情緒會翻滾好久。就如同戀愛給人的震撼,如癡如狂,卻也是椎心刺骨。即使我們都知道愛情的迷人之處,在於它的真與透明,但卻經常為愛情所騙,所苦。虛偽構不成愛情,但現在卻流行這種多面貌的愛情,炫目耀眼,曲折詭譎。這些虛偽愛情的共犯包括了貧瘠的語辭,走音的語言,扭曲的影像。作者在書裡提供了一套愛情照妖鏡,讓我們收妖收驚,能安心的繼續戀愛。
愛情成了多情境的組合與轉換,任何場景、道具、服飾、角色對白均可以給人完全不同的詮釋角度。也因此在戀人之間除了驚心動魄的愛情之外,亦不時充斥著懷疑、猜忌、自虐、欺騙,或者陷於不可自拔之迷戀深淵。到最後的結局,戀人所求的不過是一種自我安慰的解脫,自圓其說的自尊而已。中間過程的語言、情緒、表像反覆的回到記憶的腦海裡,一直反問自己:「為什麼?」他們錯過了愛情列車,也等不到下班車。時空停頓在那瞬間,既是甜蜜的回憶,又是紮心的疼痛。他們忘了攜帶李欣頻的《戀人常用辭彙160句》上車,流落在失戀鐵軌上。
【我害怕愛……】我不是怕愛,是怕做完愛後你要我負責任……
她的書揭露了活在當下的愛情生存之道,由她細膩的分類,及深入內心的剖析與反諷,世間男女更容易學會解讀現代愛情密碼,知道如何進退,如何在戀愛叢林戰火中生存。雖然茱麗葉早就提醒我們,不要相信對著月亮發誓的愛情,但仍有很多人在花前月下自我陶醉,失去籌碼,種下輸局的敗根。
【你是我的公主……】
如果他很老,他的意思是:他是你床上專制的國王,你得好好伺候他;如果他很年輕,表示他是王子,而且自認為是可以娶你的白馬王子。
套句李欣頻的《情慾料理》的一句話:愛是古老的咒語,是比文明更古老的慾望,應驗千年。只不過這次,作者不再以文字戀挑動讀者的神經,卻是以輕鬆反諷的筆觸,為現代的愛情語言下注解。未經解碼的愛情語言,有如童話裡被詛咒的女孩,每次只要張開口,就會蹦出一隻癩蛤蟆。無味的愛情語言就如同一對戀人光著腳丫走在撒哈拉沙漠上。如果你可以將【你是我的靈魂伴侶……】解讀為【因為他還有身體伴侶】,愛情還是如同羅密歐說的:「愛情是最智慧的瘋狂,有鯁喉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蜜糖。」
愛情原本是盲目的,它的趣味性就是在盲目中摸索探險。只是有些愛情智障者,還沒弄清楚這些慾望城市裡的遊戲規則,就已應聲倒地。現在讀這本書就好像已經執行死刑以後才收到的赦免狀。
無論你是否已成愛情烈士,看完《戀人常用辭彙160句》,你還會有復活的機會。
奕真
《愛欲修道院》推薦序之一
情書.備忘錄
在當代中文書信體小說中,李欣頻所著的《愛欲修道院》(2002)是第九本獨白式的單音(monophonic)書信體小說。
繼七等生《譚郎的書信》(1985)、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1986)、楊青矗《給台灣的情書》(1986)、陳輝龍《不婚夫婦愛戀情事》(1990)、楊照《天堂書簡》(1994)、李黎《浮世書簡》(1994)、徐台英《給恩英修女的六封書信》(1995)與李歐梵《范柳原懺情錄》(1998)之後,《愛欲修道院》在形式上與前八本獨白式的單音書信體小說相同,都只有一個書信作者在獨自發言,對方的回信在書中完全付之闕如。
就書信本質而言,單音書信體小說是違反書信契約的,是一種矛盾。因為所有的書信往來都是以交換為原則,研究書信敘事的學者艾特曼(Janet Altman)以「書信契約」解釋這個交換原則說:「書信敘事與日記敘事的區別在於交換的慾望。在書信敘事中,信件的讀者(收信人)被要求以書信對來信做一種回應,他/她的回信因此對書信敘事有貢獻,成為敘事整體的一部分……這就是書信契約──要求某個特定的讀者對自己所寄發的資訊有所回應。」
當書信作者在寫信時,他/她一方面在履行書信契約,另一方面也在使收信人成為立書信契約的另一個契約人,因為做為收信人的讀者在回信時轉而成為寄信人的作者。
在內容上,《愛欲修道院》則獨樹一幟,自覺地面對單音書信體小說的這種書信矛盾。在第一章《初識與確認》中,《愛欲修道院》就開宗明義地首先點明書信作者的獨語是以一種「詭異的方式」來「透過你的眼神看到我自己」。「你」是「我永遠說話的對象」。正如巴克定(Mikhail M.Bakhtin,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的《對話論》(Dialogism)所指出,獨語實即為變相的對話,書信作者「我」的獨語其實就是她與「你」之間的「虛擬對話」,而書信的對話形式在先決條件上滿足了這種需求:「我來不及抓穩自己所以我抓著你……然後我居然開始依賴你的信」、「我得有個對象進行如自言自語般的說話儀式」。
而為什麼「我」與「你」不在現實生活中對話?這是因為「我們」在現實中的相處「很難自在」,又因為透過想像所寫就的情書比較接近真實,比較接近內心的靈魂:「我不忍讓生活中的言不及義隨便填補我們好不容易挖開的靈魂出口,更何況見面。那都是皮相。在心中的、看不到的感覺才是真的」。捨棄口語而就文字,在有別於「真實世界」的「網路空間」(cyberspace)中,信件書寫的「連接」塑造了「我」的時間空間以及她與「你」的溝通模式:「在沒有電腦的期間、等公車的空檔,餐廳裡、旅途中、捷運上,我都對著手機邊走邊寫情書彷彿卿卿如晤24小時招供般地在發資訊給你」。
「我」如此依靠信件來抒發自己對「你」的感情,使得她的(書信)愛情成為一種「書寫效果」(Writing effect):「我卻是一直耗盡心神地寫書給你……你有我這個作家情人,你是我的原生讀者」、「即使你根本不在,我還在為你死命守貞著你建構的真空世界」。
她的情書成為一種文字建構的「產品」(production),遠大於反映兩人之間真實關係的「再現」(representation):「我把你給我的信加上我的虛擬對話變成自我取閱的情節」。而全書十部情書再三不斷引用諸多電影、文學、音樂來比喻當下所處的情境,更證明了她/他之間的(書信)的交互指涉過程中已然極度「文本化」(textualized):「我看到電影《古巴等公車》中……《英倫情人》裡……我和你之間可以避開生活的腐敗直接進入電影般的精彩,因為腦中已有太多的劇情、對白、場景可以借用參考,模擬交手」;「你」成為「我」寫作創造的「新隱喻」。做為現實世界中的「真實讀者」(real reader),我們不要忘了我們認識到書信作者「我」把「我和你的關係當成電影《似曾相識》在進行」的這個文本化的現象,是「我」刻意告訴讀者(包括書中的「你」)的,而不是讀者在閱讀後自行分析、歸納出來的結論。
在書寫十部情書的整個過程中,「我」都一直保持著這種高度自覺,一直不斷回顧、省思自己的信件書寫行為(the act of letter writing)本身:「我不知道這樣的信我能寫多久……我還要繼續嗎?」、「如今我已無法書寫其他主題的文字,我只能寫愛情」。當「我」越寫越多越一發不可收拾之時,當「我」的自覺在以文字陳述、整理、解析自己的感情而漸漸達到清澈透明的境地之時,發現「原來我和自己在戀愛」是一個邏輯的必然。正如《葡萄牙修女的情書》(Letters Portugaises,1669)中的書信作者瑪麗安娜稱呼她的收信對象為「我的愛」(而不是「我的愛人」)一樣,《愛欲修道院》中的「我」所愛戀的對象「你」其實就是自己,「你」是「我」的心靈所投射的影像,而十部情書的「唯一的讀者」只是自己。「我」與「你」之間、「自我」(the self)與「他我」(the other)之間的界線模糊消逝,正如德希達(Jecques Derrida)在《明信片:從蘇格拉底到佛洛依德及其之外》(The Post Card: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1987)中所寫到:「當我稱你為我的愛時,我的愛,我是在呼喚你或我的愛?你,我的愛……與我傾談的是你嗎?」
《愛欲修道院》至此已經完成正反兩層辨證:從辯解書信作者「我」的獨語為「我」與「你」的對語,到發現對語終究只是虛擬的個人獨語。這些轉折變化又與十項愛情修煉功課(十部情書)並行漸進,每一部情書都代表一種情境、一個階段、一部戀愛與書寫情書的備忘錄。
在〈第十部:神話與創造〉與〈寫給你的最後一封信〉之後,多變的書信作者仍戀戀不捨地再寫一封〈寫在情書之後〉,當讀者感覺書信作者的情書綿綿不絕之時,卻發現「我」企圖更進一步瓦解全書的書寫行為、出版事實:「一個連寫信對象都不確定,到後來連對象根本就消失的情書,書寫的熱情還正熾烈地燒高溫不降,但情書還成立嗎?這本書還需要出版嗎?」當然,這樣的疑問純粹只是修辭。因為當讀者讀到這些疑問字句時,這本私密的情書必然已經公開,已經出版,讀者意見「自行招領」這本「寄信人不詳」的情書。
這是第一本中文後設情書小說,一本關於情書的情書,一本情書備忘錄。
胡錦媛(政大英國語文學系教授)
《愛欲修道院》推薦序之二
愛情私語裡自有一座永恆的聖殿
我按著滑鼠,像前人一字圈點一字那樣,讀著你的情書。
我不知道你寫給誰。
這是窺探的意識作祟吧,使得我們閱讀他人的情書時,充滿了激動與驚異。他為什麼這樣對待她?她為什麼始終看不清真相呢?她跟他的關係原來早在這些滿紙心酸與苦澀中,早就預埋了線索。啊!我們多麼幸運,扮演了裁判,絲毫不放過兩人感情帳冊上點點滴滴的計較。
我們也是不幸的。當多了裁判,就漸漸模糊了當演員的樂趣。愛情世界,裁判永遠在場邊,聲音再大,姿勢再美,對不起,都不是主角。要當愛情主角,就要冒苦痛、挫敗、猶疑的風險,唯有經歷這些探險,戀人才能如春蠶吐絲,無限旖旎,吐出愛情私語,來構築世人連綿不絕的仰望城堡。
讀你的情書,我再次陷落意識的底層,飄忽一夜。
多麼傷感呀,我們註定要在「戀情不再」的隱喻下,春蠶吐絲而後飽滿隱去,隱入這輩子的終結,等待下輩子的輪迴。
我明白你「寫給得不到的戀人」的這系列文字。它們在游標浮動下,刺痛了我的雙眼,像那些甜蜜過往,刺痛你一一記下的靈魂一般。我不肯停下來,讀一顆抖顫的魂魄,不專注是很不道德的。就像你不肯停下按鍵,執意要在書寫中重溫愛戀一樣,遺忘以前先緊緊記住,先再次刺傷流血,而後默默遺忘。
為什麼我們總要對一位「不存在的戀人」,才能嘔心瀝血地訴說心曲?這是愛情弔詭之處。得到的,只能生活;失去的,才能想念。愛情私語款款深情,但禁不起「不承諾」的粗暴。愛情私語也幾乎不能對話,對話期待回應,回應不明確不具體,就了無意義。愛情私語最動聽者,莫過於夜鶯啼唱,唱給有心人聽,卻不求有心人非得回報不可。不求回報,讓一個人的愛情私語,感天動地,夜驚鬼神。
我按著滑鼠,滑進你搭起的私語殿堂,我仰望曾經恢弘的柱宇,撫拭上面浮雕的花飾,甚至蹲下來,在衰敗傾頹的走道上撿拾彷彿你們一手推倒的磚瓦。我靜靜讀著,電腦標準字體,掩飾了你在書寫它們時流動的情緒。這樣很好,真的,戀人私語不需要說給那些一心揣摩你秘密的人聽,也不需要那些試著想安撫你的人伸出的臂膀。你要的人,是能在文字的點滴工程間,讀出你準備遺忘,準備把記憶刻在心底而後若無其事繼續活下去的那些人。他們才能走進你的私語殿堂,懂得遺忘前夕必要的回顧。
我該怎麼歌頌你的私語呢,那裡洋溢著「光與熱」,我想到了,我在《你給我天堂也給我地獄》裡這樣說:「有光有熱的愛情,足可支撐生命的荒蕪,生活的貧乏。我們百思不得其解戀人的愚蠢,那是我們站在外邊,自以為理性地分析了光的要素、熱的成分,然後像導師一樣去評斷戀人的情緒,卻終究觸摸不到光貼近心靈的輕柔,熱溫暖靈魂的感動。在堅毅的戀人面前,我們最好閉嘴,除非我們能感受那光,與熱。」
我抬起頭,前方那座矗立的殿堂大門前,「愛欲修道院」的蒼勁題字,在夕陽下,熠熠生輝。每個隱世的傳奇,都飽含了愛。
蔡詩萍
《愛情教練場》自序
在慾望城市裡的愛情教練場
告別我的舊愛情
這本《愛情教練場》,是我在台灣《ELLE》、《Men's Uno》、《皇冠》、大陸《女友》雜誌的專欄集結,也代表著我2004年、34歲以前冷眼觀察的愛情觀點,且深受美國熱門影集《慾望城市》的影響。
就在2005年初,收看完了《慾望城市》的完結篇後,深感失落,那是一個陪我渡過幾次重大愛情事件的影集。我每看完一集,就有新靈感、新觀點寫出一篇新專欄文章;每次愛情挫敗沮喪的心情,也因在影集中看到雷同的故事而釋懷許多。我也經常把自己錯置成影片中女專欄作家凱莉,彷彿我與凱莉共生著虛實交錯的戲夢人生,而她與其他三位姐妹淘的麻辣愛情觀,也影響著當時的我對情人的態度。
2005年我從印度閉關靈修回來之後(請見《心靈蛻變之旅》),我開始學會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學會好好愛自己。一如奧修曾說過:「一個無法愛自己的人永遠無法愛任何人⋯⋯愛一旦成為執著,就淪為一種關係;愛一旦成為索求,就形同一座監獄,這樣的愛已經摧毀了你的自由」。八年之後,2013年的我以更清醒且有智慧的角度寫了一本《愛情覺醒地圖》,但目前還在愛情苦海裡載浮載沉的年輕讀者無法一下子隨書跳上岸,所以我還是把當年的舊作重新出版,算是把已沉沒在智慧之海裡的階梯重新再浮出來,讓大家能回顧我以前愛情觀的青澀軌跡,證明我也曾經載浮載沉、試圖努力捱過那些因愛而痛不欲生的日子,絕非一步登岸。
於是決定把這本《愛情教練場》重新改版上市,算是告別了那個受《慾望城市》影響很深、在愛恨情仇裡翻滾過的我,也算是在《愛情覺醒地圖》之前的重要里程碑。
我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自信、自愛、勇敢、獨立、無懼。
突然覺得自己不是在寫自序,而是幫過去的我寫序。
《戀愛詔書》自序:
關於2014 年新版的《戀愛詔書》
2013年初,我寫了一本《愛情覺醒地圖》,以清醒的角度剖析愛情重症患者的病因,找出運作在社會集體潛意識裡的愛情木馬程式,有些讀者覺得那是一本不大入世的書,太清醒到了一般人很難做到,所以我將過去出版過的愛情書,也代表我所走過的愛情歷程重新出版,這樣就能看出我登岸的軌跡。
這本2014年新改版的《戀愛詔書》,一次收納了《我和我的戀愛詔書》(集結我在聯合報、自由時報、廣告雜誌、ELLE、MEN’S UNO、香港ZIP雜誌的專欄文章,2002年初版)、《戀人常用辭彙160句》(2003年初版)、《愛情採購指南》(2003年初版)三本舊作,真實呈現出三十歲的我的戀愛觀。現在已44歲的我重新回顧與整理這些文字,還是很感謝十多年前那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自己,沒有她,也就沒有現在清澈版的自己!
《愛欲修道院》初版自序
愛的《罪與罰》
日本作家北川透的《罪與罰》文集中,列出一條書寫罪:「毫無理由的書寫者先斷一手……被切斷一隻手後還寫的,再切斷另一隻手。這樣還繼續寫的,挖掉眼睛;如此還不死心繼續寫的,割掉耳朵。還寫,就切掉雙腳。依然不停止者,嘴巴裡塞泥土。仍然書寫者,剁碎身體。還要寫的,燒成灰。還是不死心,就讓他寫,寫個不停,當永遠的書寫機器,一直到太陽不再升起為止。」(林永福譯)。
愛情的精神虐待刺激了病態的書寫慾,像薩德無人能擋地用酒用血用排泄物寫滿身體衣褲床單與牆壁,像美國知名廣告文案Ed McCabe,靈感一來就在地鐵趁旁邊老婦人不注意時,從她的購物袋撕一角來寫、或是用樹枝用石塊在人行道地板上寫、或是在濕答答的雞尾酒會餐巾上寫,或是在廁所的牆壁上寫、或是在路人的衣服上寫、或是在情人的皮膚上寫……。我的確犯了對書寫無可救藥的癮,我連穿睡衣,胸前一定還是掛著一支筆。如果忘了帶筆而無人可借,我會用口紅、眉筆或是用指甲在紙上刮字以記下思緒的源源不絕;如果不讓我寫,我會很焦慮。
寫到四肢全無,只留下一座《愛欲修道院》。
這是我出書以來,最深沉,也是最剖析我靈魂的文本。整整書寫一整年,修改一整年,寫到要排版前的最後一刻,還一直不肯將它定稿交出去,總覺得還有什麼話沒說,還有事沒交代。我不知道是因為我把《愛欲修道院》當成告白同時告別的離情書,還是當成我三十歲的遺作般的慎重,筆一直不肯停也就很難截稿出版,十分不捨放手。
就如同我在文中所說,我人際很少,牽連很深,每次分手都像生離死別,駭怕再見後就再也見不到面。雖然我篤信前世今生輪迴,但我還要等多少回漫漫生死之際,才能等到彼此的轉世?
一年來斷斷續續的書寫,我在整理書信札記文件期間只聽〈Circles of Life〉,一卷生命輪迴的音樂,我以repeat的輪迴方式播出,然後寫著我的輪迴、我情愛的重蹈覆轍。這是我三十歲之刻最重要的書寫。在歷經許多創作的千迴百轉、抱未癒的病在充滿燉中藥味的房子裡,心疼地看著過去傷痕累累的自己,然後冷眼冷靜地刮骨呈現種種文字證據的觸目驚心,情緒一再被勾起崩潰但終將冷酷地寫出來以徹底斷念。我必須真心謝謝自己三十歲前如此認真不懈的創作無悔,也對不起我日夜在電腦前高度耗損的年輕身靈。
《愛欲修道院》已落成,近八萬的文字規模,讓愛情孤戀的負債,變成蔓延書市的思念資產,然後我將離走。我要先警告,它很重,很深,很黏膩,是不太可口的愛情。
我對美術編輯說:我要一本極簡的圖文書。我的愛欲文字很華麗,所以我需要一張乾淨有質地的紙來承載它。
這本書選擇這種規格,一打開剛好是兩個人可以相摟齊看的寬度。
寫的時候我很孤獨,我不希望讀的人孤獨,我要你們進入《愛欲修道院》時都能有個心領神會的愛人在身邊,輕聲地議論著裡面的細節種種就好。
於2001年12月31日10:13pm
《愛欲修道院》再版序
這本原於2002年2月出版的《愛欲修道院》,隔了13年後終於有機會再版。這是一本我至今最摯愛,也是書寫時間最長的一本書,以真摯的情書體建構的這部小說,算是我的第一次嘗試。
自2002年至今,我的人生已經變化非常多,當初小說裡那位我暗戀的男子,我也已經不復記憶,他的真實細節早已被我的情節想像塗抹掉了,只留下這本沒有主角但有濃烈情愛的文字殿堂。
《愛欲修道院》是我收到最多讀者來信的一本,但因為原作者已經走出文本,換了新的靈魂樣貌過全新的生活,徒留讀者與文本獨自對話。
目前自己正在書寫第二本長篇小說,文字規模與劇情將遠遠大過這部《愛欲修道院》。每隔14年寫一本小說的進度,算是高速運轉多軌道的我,最珍重細琢的一個創作項目,終極是要將這些故事搬上大螢幕,這就是此生最大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