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彼此相愛的人,一顆子彈,一間無出路的囚牢。
只要死掉一個人,另一個人就能自由;
你會選擇殺掉對方,還是認命地接受:
這次輪到你了?
只要死掉一個人,另一個人就能自由;
你會選擇殺掉對方,還是認命地接受:
這次輪到你了?
一名半死不活的女孩從樹林裡出現。
她說出了一段令人難以置信、卻千真萬確的經歷。
她與男友被人迷昏,醒來後發現身處一個無法逃出的廢棄泳池,
綁匪提供一把槍與一顆子彈,告訴她:
只要死掉一人,另一人就能獲釋。
沒有燈光,沒有食物,沒有飲水,沒有遮蔽。
幾天後,他們啃指甲、吸血水、舔瓷磚上的附著物,
在無法遮掩的情況下如廁,終於……
警探海倫‧葛瑞絲接到報案,對女孩的說詞半信半疑,
但幾天之後,另一宗案件傳來:兩個一起出差的同事失蹤。
凶手特殊的犯案模式開始浮現:
綁架兩個人,要他們自相殘殺,決定何者該死,何者可活。
海倫開始追查這個隱在幕後的神祕凶手,
綁架案件與犧牲者仍持續增加;
海倫很快地發現危機開始觸及自己關心的對象以及自己不為人知的癖好,
這個凶手,似乎開始衝著她來……
作者豐富的電視影集製作經驗,巧妙地控制懸疑的節奏;
有某種黑暗性格但作風強悍的女性探長令讀者產生好奇及共鳴,
類似電影《奪魂鋸》的驚悚情節則令人神經緊張,
殺人與被殺的人性掙扎,更讓人全神貫注於故事的每個轉折發展;
你不得不思索生存與生命的意義,因為你不會知道:
這次輪到你,但你該怎麼做?
國內外名家與媒體推薦
※《週日泰晤士報》平裝本小說暢銷第五名!
◎「這本書會令你停不下來,一面害怕地咬著指甲一面追讀進度,直到天色破曉。」──理查與茱蒂閱讀俱樂部
◎「以純真與罪咎、對與錯等常見的概念開始一路翻轉,你幾乎不知道接下來會看到什麼。事實上,亞歷基幾乎到結局之前都還讓我一直猜測誰才是真凶……對我而言,這幾乎沒發生過!」──Booksellers New Zealand's blog
◎「海倫‧葛瑞絲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女主角。她替人心補上黑暗,並將它們編成令人冷到骨子裡的織綿。」──《每日郵報》
◎「亞歷基以如電影般的高度張力,緊緊扼住讀者的咽喉。」──《Barry Forshaw Crimetime》
◎「那些從一個被害者角度描寫的簡短片段,揭示了這是個哀傷的故事。一切的罪惡,都可以歸結到事件扭曲、翻轉、被陰謀掩蓋的源頭。」──Australia & New Zealand Crime Fiction Revi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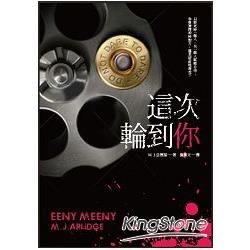
 2016/04/17
2016/04/17 2015/01/29
2015/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