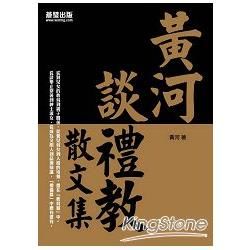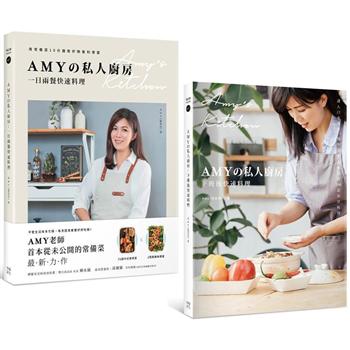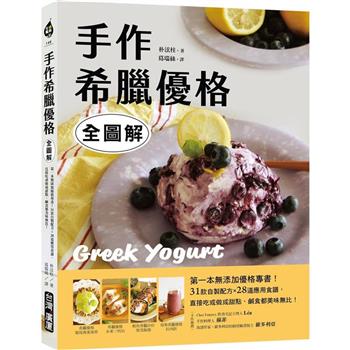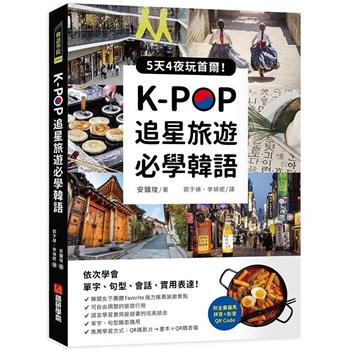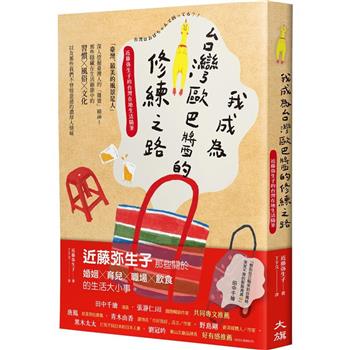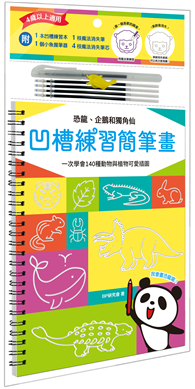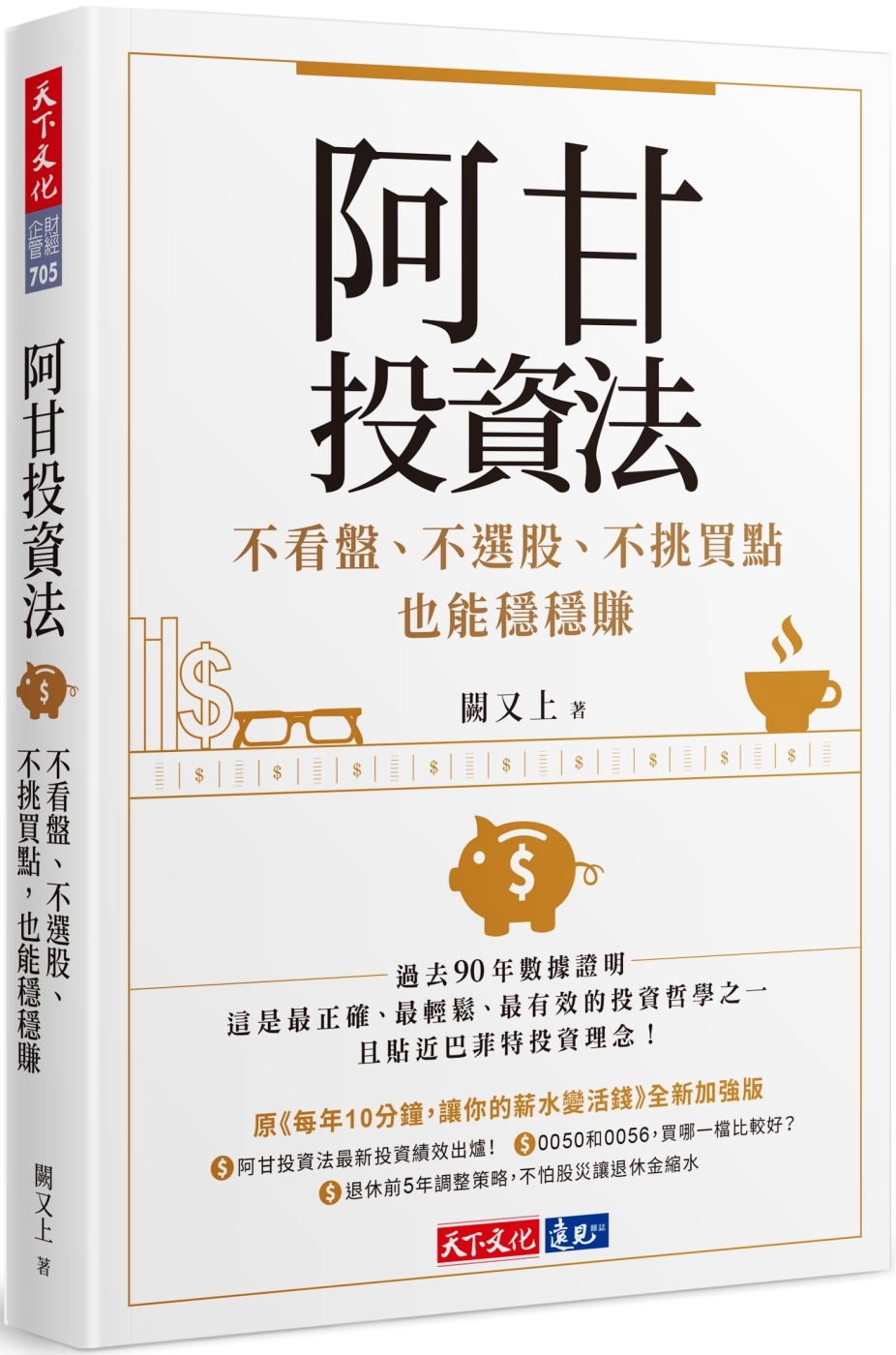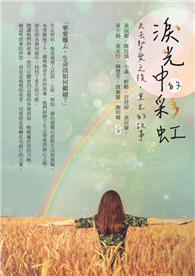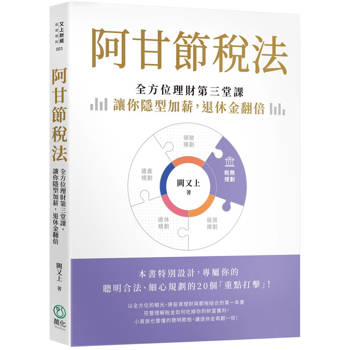兒女的教育(上)
本來想寫《如何教育兒女》。後來自省,我哪有資格談「如何」?只好改變主題,換成《兒女的教育》。
為人父母,誰不關心這主題?
這主題從大兒子有了主觀意識,會表達他的意見,就開始持續困擾著我。
我自認很有說服力,課堂上常講得學生感動不已,但是碰上自己的兒子,卻好像雞同鴨講,有時連最基本的溝通都有點困難。
似乎,兒子的存在就是為了反叛──父母說東,他們就西;父母說西,他們就東。
真如此也算幸運──我想要他住東,就說西;可惜,事情沒那麼簡單。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教育兒女。到今天,當了十九年的父親,擁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老大今年考進大學,小女兒讀小五,就算再沒資格,也該有點心得。
不過,這篇文章的內容未必正確。我只是將自己實際的經驗說出來,提供各位參考。
我要舉老大的例子。老大今年(2009)考進大學,應該對他的人生做個小結。
老大小名龍龍(龍年出生),個頭原本就高大,由於生在十月,和次年的孩子同學齡,因而更是顯得高大。小學和國中時站在隊伍之中,比同學足足高出一個頭,用「從小鶴立雞群」來形容絕不誇張。
人高馬大對小學生的地位十分重要。由於他個性活潑外向,很容易成為學校的風雲人物。從國小到高中都是運動健將,無論跳遠或跑步,只要參加,幾乎穩拿校運金牌。進入高中以後更成為社團的風雲人物,什麼吉他社社長、社聯會副主席、畢聯會主席……,社團活動已經占據他大部分的時間,又喜歡畫畫,常常擔任班級或校際活動的美術設計。
聽起來是一個優秀的學生,然而講到考試成績,就令為人父母者慚愧啦!
我和老婆對許多事情都有不同的意見,唯獨對子女的教育幾乎有志一同。
同什麼呢?
講好聽是自由發展,其實是完全不管!
不管到什麼程度?
許多父母會「叮嚀、陪同、教導」子女做功課,這種事從不曾發生在我們家。
說「從不曾」也不對。龍龍國中時我曾經教過他一次數學,唯一的一次。我口沫橫飛說了半天,他始終拿「你在說什麼啊」的眼神看著我。
至於他的課業,我最多問一句「功課做了沒」、「考得怎麼樣」,絕不會因他回答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情。
舉一個例子便可明白我家的教育是何等的自由。
小學畢業,龍龍擁有無限上網的個人電腦。剛開始是迷遊戲,後來是聊天室、自製網頁、動畫、擔任遊戲版主……,管他什麼,反正都和課業無關。他經常玩到徹夜不睡。我講過幾次,不外溫言詢問:「明天要上學,不應該早一點睡嗎?」他虛應幾聲,沒明顯改變,我也就不再管他。
國中三年、高中三年,我和老婆全都沒有限制他們上網的時間。
高一的時候不巧,他和我的姪女(大哥的女兒)同校同班。第一學期結束,年夜飯時我趁他離開,悄聲問姪女:龍龍在學校是不是經常睡覺?
沒想到,姪女還來不及回答,大嫂已忍不住拍了下桌子,一副「看不下去」地說:「今天你不問,我不講;既然你問到了,老實告訴你,龍龍在學校從頭到尾都在睡覺!」
我會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因為他在家幾乎通宵達旦忙著上網,第二天怎麼可能有精神上課?
之所以問,只是想進一步確認。
確認以後又怎麼樣?
沒怎麼樣。甚至連講都沒講,只是放在心底,難過在心裡。
小學的時候龍龍偶爾考全班第一名,平均在第三至第五名。國中退到第五至第十名。高中考入桃園聯招第二志願(桃園高中),自此便以「同學都經過洮汰,具備一定水準」,而名正言順地墊底。月考經常是全班倒數前幾名,少數幾科甚至差到全校倒數前幾名。
全校倒數前幾名──天啦,這是那個小學時候偶爾考第一名的小孩嗎?
我不擔心?
當然擔心。
我不曾試圖管過他?
當然管過。
可是,我發覺他的自主性很強。假如我過分強勢,只會造成我們父子間的衝突。
和別人爆發衝突,我可能堅持到底。碰上自己的兒子,經過再三考慮……,我只有嘆口氣,暗自決定退讓。
不過,我真的很迷惑,也常問自己:退讓是對的嗎?
我讀過許多文章,作者描述兒時父親是如何嚴厲,而這些嚴厲日後又對他產生什麼樣的正面影響。
例如後面這篇《她們這一家人》,是名作家劉墉的著作。
《她們這一家人》
在我唸研究所的最後一年,日文課班上突然出現了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太太。當她正襟危坐,擠在一群二、三十歲年輕人之間,跟著教授朗讀的時候,實在很有意思。
起初我以為她只是排遣時間的旁聽生,後來看她也緊張兮兮地應付考試,才確定是正式的研究生。
她從不缺席,筆記又寫得好,所以翹課的人都找她幫忙,我們稱她為趙太太。直到畢業,才知道她就是趙小蘭的母親──朱木蘭女士。
我今天提到趙小蘭,並不想強調她是華裔在美國政府職位最高的人;也不想討論她的白宮學者、花旗銀行傲人的學經歷;而是希望讀者能了解一下趙小蘭的家庭生活。
因為我相信,沒有那樣好的家庭教育,很難有趙小蘭今天的成就。
最起碼趙小蘭今天立身華府高階層,那帶有適度矜持與華裔尊榮的氣質,必然來自她那特殊的家庭教育。
我用「特殊」兩字形容是絕不為過的,因為在美國的中國家庭,能有她家那樣完整而嚴格訓練的已經太少了,即使在中國,相信也不多。
看過《真善美》那部電影的人,大概會記得茱麗安德魯絲初去當家教的時候,父親一吹哨子,孩子就由大到小,列隊出現的畫面。
這種情景,幾乎也能在趙小蘭的家裡看到。
趙小蘭的父親趙錫成博士很好客,每有客人來,六個女兒只要在家,一定出來招呼。
她們以非常恭敬的態度為客人奉茶,臉上總是帶著真誠的笑容。
尤其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以前當趙家宴客,幾個女兒不但出席上桌,而且是守在客人身後,為大家上菜、斟酒!
當我不解地問朱木蘭女士時,她說:「不錯!我們是教她們做Waitress,但那何嘗不是一種訓練?我的先生常對女兒說,人生做事好像開車,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時候必須左轉右轉。不要把伺候客人當做辛苦的事,當你們讀書讀累了,招呼招呼客人,不也是一種休息嗎?何況在這當中,可以學到許多待人處世的道理。」
也就因此,他們家雖有管家,孩子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掃房間。
大人的道理簡單:「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管家是請來幫助父母的,不是幫助孩子。年輕人理當管自己的事,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否則很難學會獨立。」
不僅料理自己的內務,每天上鬧鐘起床,小時候趕校車上學,回家由姊姊帶頭,自動自發念書。
而且她們家的六個女兒,還分擔家務。
每天早晨,她們要出去檢查游泳池的設備、撈掉水上的髒東西。
到了周末,則要整理占地兩英畝的院子,把雜草和蒲公英拔掉。
趙小蘭最小的妹妹,現在十六歲的趙安吉,已經負責處理家裡的帳單、將耶誕卡的郵寄名單輸入電腦,並接聽晚上的電話。
尤其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趙小蘭家門前長達一百二十英尺車道的柏油路面,竟然是幾個姊妹,在父親的指揮之下自己鋪成的。
趙小蘭曾在《我的事業與人生》的文章裡說:「那時我們不見得喜歡,如今想來,大家一起工作、一起交談,很能領會父親良苦的用心了。」
「家園!家園!這個園地是一家人的,每個人都有責任!」朱木蘭女士說。
正由於她們對家庭貢獻出自己的心力,所以尤其會愛家;覺得自己是家的一份子,家是屬於自己的。
特別是在一家人共同的工作中,更能體會榮辱與共、同心協力,而產生共同意識。
趙錫成博士夫婦的身教也是極成功的。他們家在晚餐後極少開電視,做父母的也以身作則,不在電視前花太多時間。母親跟著孩子一起讀書,父親則處理未完的公務。
從事航運工作的趙錫成博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
他這種對事業專注的態度,相信也對趙小蘭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不論多麼忙,與子女的溝通還是不能忽略的。
每個星期天,他們一定全家去做禮拜。午餐後點心時間,則舉行每週一次的家庭會議,大夥高談闊論。每個孩子說出自己的新想法、收穫,提出計畫,並徵詢父母的意見。
所以當外人驚訝於趙家姊妹的紀律與服從時,要知道那是經由親子之間充分溝通,所獲得的共識。
當她們為家庭付出時,不是想到父母命令自己做,而是心裡的責任感。
家是一個「共榮圈」,當每個成員都這麼有向心力時,家庭當然會興旺。
我們確實看到朱木蘭女士,一九六二年帶著趙小蘭和兩個更小的女兒,坐船來美國。從孩子們半句英文不通,必須由父親熬夜逐字教導。艱苦奮鬥到今天,已經有四個分別從哈佛、哥倫比亞、維州大學等名校的研究所畢業。連朱木蘭女士,都以兩全勤的紀錄,修得碩士學位。當然,趙錫成博士更成為美國航運財經界的名人。
但是趙家儘管富裕,孩子卻多半進公立高中,在外面的花費,不論大小,都要拿收據回家報帳。
趙小蘭唸大學的學費,還向政府貸款,靠著暑假打工還錢。
這不表示趙錫成夫婦小器,而是因為要求子女獨立、負責,把錢花在當用的地方。
他們對孩子說:「我們雖然儉省,但是你們如果要學東西,絕對不省!只是既然要學,就有責任學好!」
所以趙小蘭和她的五個妹妹,不但功課好,而且各有才藝。
趙小蘭能打高爾夫球、騎馬、溜冰、更彈得一手好琴。從前家住紐約長島時,還經常出去演奏。
此外,他們每年在暑假和耶誕節,分別安排一次全家遠遊。
從選擇地點、訂旅館房間,乃至吃飯的餐館,完全由孩子負責。
所以,這旅行一方面是全家同樂,一方面成為孩子們組織、分工的訓練。
由以上所舉的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知道,趙小蘭姊妹的成功,與她們所受的家庭教育有絕對密切關係。
無怪老布希總統在白宮接見趙錫成博士一家時,都特別強調這一點。
還對太太芭芭拉說,應該向朱木蘭女士學學怎麼管孩子!
怎麼管?
答案應該是……
中國傳統的孝悌忠信與西方社會的組織管理方法結合,既培養個人的獨立性,更要求每個人對家庭的參與,透過溝通後產生家庭共同意識,達成彼此希望的目標。
據我所知,在今年六月十七日美國父親節時,趙小蘭特別暫時放下交通部副部長的繁忙工作,由華府趕回紐約的家中,為趙錫成博士過節。
請問,在國內有幾個身在外地、位居要津的子女,能在父親節時趕回家,並誠摯地送上一份禮物與祝福?
兒女的教育(下)
看完《她們這一家人》,你有什麼想法?
坦白說,每當我想到這篇文章的內容,就感到萬分慚愧。和趙小蘭的父親相比,我是不負責到了極點。
可是,同一時間,我又想到我自己。
講句有點自吹自擂的話──我對今天的自己,十分滿意;不單是滿意目前的生活,更滿意擁有獨立的個性和自主能力。
假如能把龍龍教育成我目前的個性,我會很滿意。
於是,我開始思考我的成長環境。
我們這一代(三、四、五年級生),父母對我們的付出,幾乎就是把兒女「養大」。
講起來好像有點無情,然而是事實。在物質貧乏的年代,兄弟姊妹的人口又多,父母能把兒女養大已然不易。
除了養大,父母很少管我什麼、告誡我什麼。
即使有告誡我什麼,可能也沒放在心裡,因而不記得。
我在自由自在的環境中成長。學生時代,父母絕少問我考試的成績。初中(振聲私立中學)、高中、五專、軍校聯招,全都是我單槍匹馬前往應考。
聯考都如此,其他事可想而知。
生活方面,父母也很少管我。原因之一是父親在軍中,一個月見不了幾面,想管恐怕也無從管起。至於母親,這輩子都忙於填飽我們兄弟姊妹四張口,偶爾有點空閒,常也忙於教會的工作。
直到今天,我都自由自在慣了,非常討厭別人在我耳邊嘮嘮叨叨。也因此,我從很小就認清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除了我自己,誰也不能為我負責,誰也無法左右我。
而我也相信,真正的人生是要自己親身走過才算數,別人怎麼教都有限!
不是嗎?許多事情我們之所以有深刻的體會,是因為我們碰過、體驗過。至於體驗出的那個道理,不早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就聽別人講過?
聽完,左耳進、右耳出,沒發揮任何效果。
父母應該如何訓練兒女?
讓孩子自己去處理、面對、體會他的人生。孩子能有所心得,因而成就某些功業,是他的福分;否則,也是他的命。
所以,對於兒女的教育,我決定給他們充分的自由,讓他們認清「自己的人生要自己面對、自己負責」。
其次,我還相信「收斂到極限就是發散,發散到極限就是收斂」。
再講白一點,就是「物極必反」。
當你任由孩子自由自在發展,你以為他們會自由到什麼程度?
許多時候人們之所以渴望,是因為他們無法完全擁有。
例如每個人都喜歡吃龍蝦。但是,假如天天吃、餐餐吃,誰還喜歡吃?
又好比,當你富裕到花錢無所顧忌,花錢還可能帶給你快樂?
有個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小時候有一次過年,他和弟弟為了搶喝汽水而大打出手。他父親看到了,一句話沒講,出去買了一打汽水,回家強迫兄弟二人各喝六瓶。
他父親的管教方式令我印象深刻。
後來面對兩個兒子天天迷上網,我採取類同的方法。有一天把兩兄弟找來,誠懇地說,如果他們真喜歡上網,喜歡到遠遠超過讀書,只要他們同意,我願意到學校幫他們辦休學。先在家澈底玩個一年,再決定要不要上學。
他們沒敢說好。
我敢保證,假如他們說好,第二天我就到學校幫他們辦休學。
不要不信,我就是這樣的父母。
也因為我連辦休學都敢,他們在家熬夜不睡,到學校睡覺的行為,我也視若無睹,從此不再規勸什麼。
對於兒女,父母不必,也不應擔心太多。從小什麼事都照顧得密不透風,長大以後必缺乏獨立的精神。
每當參加學校舉辦的家長會,對那些「啥事都管」父母所提出的問題感到自嘆不如。例如,某次參加小兒子的家長會,一位家長情緒激動地反對學校選的英文教材。一開始我還沒聽懂,後來才曉得,實施教改以後,學校可以從教育部審定的眾多教材之中,選定某一本當成學生的教材。
那位家長氣憤填膺地說,全桃園縣的國中都選甲教材,為什麼唯獨本校選乙教材?
聽完那位家長的意見,我甘拜下風。我壓根不關心兒子讀什麼教材,不僅沒問過、看過,更不可能去打聽別的學校選什麼教材。他還能把全縣國中的教材都打聽清楚,能不令人佩服?
這種家長能教育出什麼獨立個性的兒女,我實在懷疑。
看到這,可能讀者想問:倘若放任兒女自由發展,父母的責任又是什麼?
我覺得父母的責任是以身作則,提供兒女一個溫暖、和諧、無憂無慮的成長環境。
肯定要以身作則,因為兒女在不知不覺中會模仿父母的行為。
例如我看書寫作時喜歡聽輕音樂,偶爾還要喝一杯不放糖的咖啡。我那看似叛逆的龍龍,國中就開始喝不放糖的咖啡,屋裡也經常播放音樂。
至於提供一個溫暖、和諧、無憂無慮的環境,是希望他能把家當成一個休息站,一個他累了就想回去的地方。
某些父母沉迷於麻將,晚餐就拿幾百元叫兒女到外面自己吃。
某些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沒事還吵到要離婚。
某些父母沒事便坐在電視機前,看連續劇就流淚,看叩應節目就跟著大罵。
某些父母不務正業,盡幹一些偷雞摸狗、違法亂紀的勾當。
這種父母,不管如何管教小孩,又能教出什麼名堂?
所幸,我和老婆大致做到我心目中父母的責任。我們家的小孩在家裡幾乎沒有任何壓力,不僅不會有離家出走的念頭,龍龍還經常帶同學回家,三、四個算是少的,偶爾有十幾個留下過夜。
這樣全然自由的環境中,龍龍有什麼表現?
最明顯的是從國小、國中,到高中,成績越來越差──講來好丟人,是不是?
成績不可能不變差。國小的時候大家都不太讀書,所以偶爾可以考第一名。國中以後部分同學補習,成績便開始下滑。高中的時候幾乎全都補習,而他拒絕補習,成績自然殿後。
更可笑的是,別人考前都熬夜通宵,他越到考試卻睡得越多。
為什麼睡得越多?
因為接近大考時玩得不安心,可是又讀不下書,只好埋頭睡大覺。
我不為龍龍的前途憂心嗎?
當然憂心!
可是,我又堅信,他終究有開竅的一天。而且,他的課業雖然日漸下滑,但是日子過得很快樂、個性善良、沒有不良嗜好、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又精通吉他、美術、電腦。即使考不上一流大學,未來到社會也應有不錯的工作機會。
樂觀進取的生活態度遠比一紙文憑要來得重要。
堅信歸堅信,私底下我也惶恐,並暗自祈禱,希望龍龍能早點開竅。
半年前他學測考得不太理想,似乎受到刺激,突然發憤圖強。每天在圖書館苦讀到九點,回到家吃飯、洗澡,再上網一、兩個小時,多半能在凌晨左右入睡。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半年的努力有了結果。七月一日參加大學聯招,在第一類組五萬餘名考生中考到第三千名左右!
天啦,全班倒數前幾名畢業,大學聯招竟考到全班前幾名,能不令人意外?
也因為這意外,讓我起了寫這篇文章的衝動。
如何教育兒女?
答案是「不要教」!提供他溫暖的成長環境,給予他充分的自由,讓他明白讀書是為自己而讀,人生要對自己負責。
再進一步地說,父母說什麼都是多餘的,身教重於言教。
兒女和你天天生活在一起,距離如此之近,你講一套、做一套,他會看不清楚?
與其你坐不正,不如不要教;教了,反而有反效果。
假如你坐得正,即使不教,他耳濡目染,終究會有樣學樣。
龍龍大專聯考意外地優異,考上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受邀回桃中演講。老師希望他對學弟妹說些「不管你現在成績多爛,永遠不要放棄」之類的鼓勵話。
猜猜看,結果他說了什麼?
我問他這問題。他很得意地說:我勸他們讀累了、煩躁的時候就不要讀。與其坐在那兒打瞌睡、浪費時間,不如出去盡情玩一玩;等玩到自己心虛,再回來讀書,效果反而更好。
最近又看到劉墉寫的《不發火一切都美妙》,同樣談到兒女教育的問題。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黃河談禮教:散文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0 |
人文史地 |
$ 221 |
親子教育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現代散文 |
$ 252 |
散文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黃河談禮教:散文集
從對兒女的教育到親子關係,從養兒育女到人格的培養,盡在本書的「教育篇」中。
從談舉止穿著到紳士淑女,從成為文明人到品酒知識,本書的「禮儀篇」中應有盡有。
作者簡介:
黃河,左營海軍官校1980年班,美國波士頓大學碩士,兩度赴美海軍基地接受專業訓練;歷任艦艇基層軍官,海軍總部武獲室專案參謀、兵器處水兵科科長,中華民國海軍第一艘二代艦──成功艦首任副艦長,獵雷艦永嘉艦艦長,以及成功級張騫艦首任艦長。
黃河具備現代化海軍軍官之背景,學經歷多采多姿,1994年意外寫了第一本小說《一九九七知本風暴》,從此愛上小說創作,因而於2000年退伍成為專職作家。2006年成立「黃河渡」網站,以每週乙篇散文之創作速度談論自己的人生經驗,期望讀者吸收他的人生經驗,使能在工作中少花一點力氣,行為上少犯幾個錯誤,思想上改掉一些偏激的想法,進而讓讀者自己的人生更愉快。
章節試閱
兒女的教育(上)
本來想寫《如何教育兒女》。後來自省,我哪有資格談「如何」?只好改變主題,換成《兒女的教育》。
為人父母,誰不關心這主題?
這主題從大兒子有了主觀意識,會表達他的意見,就開始持續困擾著我。
我自認很有說服力,課堂上常講得學生感動不已,但是碰上自己的兒子,卻好像雞同鴨講,有時連最基本的溝通都有點困難。
似乎,兒子的存在就是為了反叛──父母說東,他們就西;父母說西,他們就東。
真如此也算幸運──我想要他住東,就說西;可惜,事情沒那麼簡單。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教育兒女。到今天,當了十九年的...
本來想寫《如何教育兒女》。後來自省,我哪有資格談「如何」?只好改變主題,換成《兒女的教育》。
為人父母,誰不關心這主題?
這主題從大兒子有了主觀意識,會表達他的意見,就開始持續困擾著我。
我自認很有說服力,課堂上常講得學生感動不已,但是碰上自己的兒子,卻好像雞同鴨講,有時連最基本的溝通都有點困難。
似乎,兒子的存在就是為了反叛──父母說東,他們就西;父母說西,他們就東。
真如此也算幸運──我想要他住東,就說西;可惜,事情沒那麼簡單。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教育兒女。到今天,當了十九年的...
»看全部
目錄
教育篇
兒女的教育(上)
兒女的教育(下)
天生我才必有用
放手讓孩子自己走
饒了孩子吧
放對位置
中國人好聰明啊!
中國人為什麼缺乏創造力
兒女應學的四堂課
親子關係(一)
親子關係(二)
親子關係(三)
親子關係(四)
我是老大
螞蟻或棉羊
個性決定命運
三歲看到大?
什麼是天才
創作的靈感
給新手父母的建言
禮儀篇
人要衣裝
輕手輕腳,細聲細語
淑女與紳士(上)
淑女與紳士(中)
淑女與紳士(下)
用餐禮儀入門
談吐應對入門
守時
小費
西裝
差別待遇
文明人
再談文明人
文明與法律(上)
文...
兒女的教育(上)
兒女的教育(下)
天生我才必有用
放手讓孩子自己走
饒了孩子吧
放對位置
中國人好聰明啊!
中國人為什麼缺乏創造力
兒女應學的四堂課
親子關係(一)
親子關係(二)
親子關係(三)
親子關係(四)
我是老大
螞蟻或棉羊
個性決定命運
三歲看到大?
什麼是天才
創作的靈感
給新手父母的建言
禮儀篇
人要衣裝
輕手輕腳,細聲細語
淑女與紳士(上)
淑女與紳士(中)
淑女與紳士(下)
用餐禮儀入門
談吐應對入門
守時
小費
西裝
差別待遇
文明人
再談文明人
文明與法律(上)
文...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河
- 出版社: 蒼璧出版 出版日期:2014-10-20 ISBN/ISSN:978986910697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開數:18開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