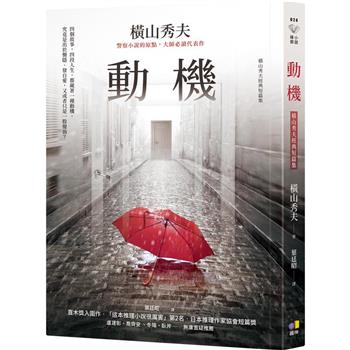1.光的行進
賦恩緩慢的沿著階梯走進空盪的觀眾席,仔細的掃視花了整個下午排置定位的舞台空間,空氣裡少了聲息的支撐,連隨著軟厚的橡膠鞋底落下的腳步聲,都足以透澈出清晰的音頻,眼神一下落定在舞臺的觀眾席第四排中央,坐著那位明天就要以被譽為最年輕就能展開世界巡演的亞洲天才魔術師的身影。
賦恩叮嚀著自己收斂最輕的腳步,安靜的站定離他的座位有些距離的斜後方,在他思考的時候他絕對不會出聲破壞,讓這個把意念昇華為實境的昂貴時刻出現裂縫。
他從後側看著他輕闔雙眼,放鬆的交疊雙腳,難得重獲閒暇的十指,交縫相扣的安歇在唇間,順成圓滑弧度的髮絲,布幕似的落下切割光源的陰影,覆蓋他洗練的側臉,他總是攜帶著高昂及絕對實踐信念的沸揚情緒,在此刻似乎和他失聯,僅剩最純粹的軀殼,和與心靈深層共振的單純人性。
他為魔術殉身,魔術亦為他著迷。
真實就像魔術方塊被他隨意解構,只有他自己可以重組回原型的脈絡,軸心是最單純的創作意念,構成程式的點,手法的線和充滿藝術價值整籌成完整的面,經過精準的統合來構成幻覺的實質量感。
他將所有和現實脫焦的矛盾跟對立,都以最近的距離號召於觀眾面前,大膽而無畏的和一切的常理冒犯衝突,揭開一場如萬花筒般璀璨的鏡象盛宴,下達一個可以解除所有對幻境饑渴的暗示而沒有休止的海市蜃樓。
「我們的眼睛最會欺騙自己。」
他說這句話的表情,像極了一個從一而終只棲居在現實邊緣的孩子。
「都忙了一天了,你不是該去休息了嗎?」他微微的睜開眼睛,微捲的睫毛甦醒似的恢復了呼吸。
「剛剛打電話去你房裡沒人接,也沒有人知道你去了哪裡。」
賦恩回應,邊大方的走下樓梯,將安靜攏靠在手臂上的的靛藍西裝外套遞到他面前「你又把外套放在飯店的酒吧裡了,酒吧的人剛剛通知我去領回來,我檢查過,皮包跟手機都還在裡面。」他的口氣平寂慣性的像在敘述每日都必須跟他報告的工作行程。
「是哪,我現在才想起來我有穿外套出門。」他就像找到父母藏在庭院角落的復活節彩蛋一樣欣喜,賦恩從鼻腔裡輕抿了一口氣,實在搞不懂這個對工作細節的要求總是可以壓縮到緊緊接縫每個小細節、鞏固所有條件都能嚴謹掌控、如此重視自我制約的人,生活秩序為啥可以散漫的似乎可以在無意間把自己都丟了?
就是如此極端的檯面與私底下的冷熱反差,讓他一年之內換了四組助理,賦恩是目前為止,還能安穩的為他基座不穩的日常生活,架上補助支杵的助理達到一年以上的唯一一個,
在這段沒有任何空隙的相處時間裡,賦恩感覺他的生活只充滿了隨著一刻不得閒的行程,一站遷徒到一站的緊湊,意念的構成、煽動創意的醒覺、架構編譯執行的可行性、製作輔助的道具,層層堆疊的反覆演練,要將所有可能的錯誤都勒緊到窒息的檢討,
表演只是被這些背後的細節,車縫交織出的最後質感,是被打著聚光燈唯一明朗的一小部份,讓人無法揭密背後真實而忙亂的戰場。
沒有穿戴著奇幻魔術的其他時候,關於他的自身只是破碎的零件、閒暇之餘才能重新組裝,偶爾享樂於輝煌成就的光采聚焦,和現實關聯的螺絲依舊拴的很緊。
短暫縱容回歸自我的片刻,內部其實和普通人一樣會自我揣測、因為壓力而鬆動自信,被孤寂迫害的心靈種植著大片茂盛的空虛,會用掉淚寬恕自己,在普通不過的一個人。
他時常會對著鏡子演練,偶爾,對著鏡中的自己發呆,彷彿鏡子裡的自己就是幻境的實體,他們互相睥睨著對方,試探彼此的驕傲,鏡裡鏡外都能牽制對方最後的成象,用鏡象反射為途徑互相辨識、認證自己,一如他親手捏製的魔術就是他鏡中的隱喻,是他帶著謎底最終的自我展現。
「坐啊,幹嘛杵在那裡?」他拍拍身旁的座椅,食指上摟空細雕花的銀戒閃著透澈的光感。
賦恩坐到他身旁,看著明天就要盛大揭演這場以他為首的個人魔術秀「鏡象盛宴」,而裝飾起整個舞臺的華麗輪廓,所埋藏的機關,讓演出可以循著完美計畫的機制,在這麼近的眼前,卻能讓真相變的如此疏離的驚奇瞬間,就是以這個龐大的執行架構和身邊這個深具獨創思維的人為原點。
邊撐著下巴這麼想著的賦恩,從黃褐色的小羊皮揹袋裡,拿出一個溢滿黃芥末微酸香氣的熱狗堡「我想你應該也不記得你一整天到現在只有吃了早餐而已。」
身邊這個天才魔術師只是默許似的傻笑接過,像褒獎般的摸摸他的頭,賦恩只是回應了他一個白眼,看著他拿起本來安穩靜置在盒裡的熱狗堡大口的咬下,乳黃色黏稠的芥末沾染了他的嘴角和指尖,賦恩馬上從已經拿在手上、只要隨側在他身邊就要多備個幾包的面紙裡抽出一張。
慶幸自己是家裡五個弟妹的兄長,才能讓自己慣於照顧這個小自己兩歲、從來就只有被照顧的命的獨生子,而不會感覺被貶低或彆扭。
幫他用面紙輕抹去嘴角的芥末,他一付理所當然的保持快速用餐的準則咀嚼著食物,一邊將眼神緊鎖著這個屬於他的舞臺,用宛若極度渴望成為這一切旁觀者的語氣說;
「我從來沒有用這個角度看過台上的自己,那是什麼樣子?」
「就是一個技術高超、讓人驚嘆的偉大魔術師。」
賦恩挑選最官方的奉承來回答,畢竟總不能把”但私底下根本就是個宅男兼生活白癡”這句真心話,說給眼前這個目前唯一的衣食父母聽。
「你知道法國有位精神分析巨擘拉崗提出的「鏡象階段」(the mirror stage)理論嗎?」
他接過賦恩手上的面紙,邊擦拭嘴角邊把手上不到五分鐘就解決的晚餐空盒蓋好,感覺他進食只是為了身體需求的溫飽,並沒有在其中獲得任何留戀的滋味和滿足。
「嗯,你在這次表演提案的企劃書裡有稍微提過。他提出鏡子裡的自己並不是真實的,只是我們想要看到的自己的幻境殘影。」
賦恩知道他們之間的話題絕對不會離開探討或研論魔術超過三分鐘,他只是像被老師點起來發問的學生般正經八百的回答。
「最近我忍不住會想,台上的我就像這樣吧?在這裡的"我"竟然要靠臺上的自己才能塑型辨認出完整的"我",我似乎,漸漸的分不清楚,到底哪個是真的我了?」
「牧典老師?」
賦恩輕抿眉心,有些擔心的看著他,他不止一次看過他這樣,通常是在臨場壓力極大的上台前,似乎在和內部的自己交戰摩擦,想用各種隱喻藏匿自己的不完全,連煮沸不安都變的過於謹慎,只能在這一瞬間對著怯懦的溫熱取暖,似乎在此刻只要照亮自己其實是這麼的真實平凡,就能夠取悅自信再度披上戰袍。
賦恩看著他有些流失清晰血色的面容,只是緘默的保持凝視,他不打攪和用安慰侵害,期望對此刻的他而言已然成為過重的超載。
但是,老師,其實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你創造的鏡象,是多少人冀望能爭相目睹一秒鐘的美夢,就算明知那是最高尚的騙術組裝起的優雅幻覺,讓我們能享受被拋擲到現實之外的一瞬間。
你不明白我有多麼渴望,能在鏡中看見你,
我多麼希望能夠成為你。
空間裡本該恆常的暖意逐漸失溫,賦恩感覺自己漸漸被寒意覆蓋,因為連續好幾天忙亂到沒有按時進食的腸胃,還互相翻攪著刺痛,讓他難受的從讓體溫低迷著維持最基本供需狀態的沉眠裡清醒。
一拉開迷離聚焦的眼睛,先收印眼底的,就是慣性放在飯店床頭燈櫃上的手錶時間,分針秒針已經安然的交疊在正午時分,他睜圓了雙眼,腦袋像瞬間被電極一樣轟然清醒。
「中午了?已經中午了?為啥飯店沒有給我morning call?老師!糟了啦!上午的排演?」
他慌亂的跳起來,懊惱的搔抓著一頭捲翹的亂髮失聲大叫,一回頭,看著昨晚因為風雪的攪局,打亂了訂房的交接時間,而不得不精簡最低訂房數,湊合著一起住的隔壁床上的人影,已經掀開被角徒留一陣空盪。
「別緊張,早上風雪太大,積雪壓垮了表演場地的水管線,現在正在修復,今天的排演都臨時取消了。」
姿態好整以暇的牧典,穿著鬆垮的浴袍還厚裹著白淨的被單,勾著腳坐在飯店的古棕色木質書桌前,鼻樑架著墨黑色的粗框眼鏡,隨性的在指間旋繞著極細的鋼珠原子筆,專注的對著眼前已經寫滿構思的記事本,語氣安撫的說。
隨即抬起頭,看向把自己嚇的手足無措的賦恩,用掌心輕拍胸口,毫無節制的喘了一口大氣,弓起的背脊瞬間癱軟模樣,爽朗的笑出聲來。
「終於偷到一天閒可以好好的休息了,都要感謝這場大到嚇死人的風雪。」
抓緊包覆在身上的被單走向窗邊,期望觸碰窗外那片將所有事物的存在,都凝結成安寧靜止的雪白似的拉開卡鎖,將攀爬著銀亮結晶的窗戶推開,像第一次接觸到沒有定義的單純美好的孩子一般的伸出手。
「你看。」
氣息催化成白霧,他在只能讓人俯首的純粹之美面前順從的微笑,指腹和掌心瞬間安歇著無數的雪白結晶,他看著手中完美成型、優雅的六角晶體,雖然沒有任何色彩,卻能在嚴寒裡鍊成如此純淨的存在,他忍不住驚嘆。
「這才是真正的魔術!我多希望能用自己的表演傳達出這種最簡單的感動!」
「老師!」整個室內都一下被零下的嚴寒掠奪了所有的溫度,賦恩滿臉受不了的縮緊身體,拿起自己的被單走到窗邊把他像蟬繭一樣緊緊包住,
「拜託你別這樣!你可不能在這種節骨眼感冒!」他冷的直打哆嗦,四肢都開始僵硬不聽使喚,上下排的牙齒都打架似的不停碰撞。
「你…。」被包裹的只有一張臉探出被單的牧典,狡黠的笑彎了眼睛「真是個好人耶。」
「我到底要被你發幾次好人卡?」
賦恩不停下意識的抖動身體,牙齒忍不住淩亂的卡卡打顫,雪花成群結隊的打到臉上,冰冽的刺痛讓他眼睛都快睜不開,而始作庸者卻只顧著笑。
終於他肯罷手的將窗戶鎖緊,賦恩想脫困似的將他帶離窗邊的瞬間,感覺他渾身濃厚的酒氣,下意識的問「你喝酒了嗎?」
那他現在毫無邏輯的行徑就有憑證可循,這個人酒量爛的出名,在任何慶功宴上大家都有心照不宣的默契,絕不遞酒到他手上,免的酒精就像催眠一樣對他下達各種無厘頭的指令,
他的形象也是整個團隊的基座,他身邊圍繞著隨時準備撕咬他弱點的豺狼,咬下他一塊殘缺,就貪婪的動用網路的脈絡武裝真相,對著全世界大聲嚎叫,弒血的謀害他奉獻一切所有奠定的價值,他們渴望看見他降服戰敗的執著近乎執狂的迷戀,一刻都大意不得。
「拜託你別再做些會消耗心神的事,就趁這個機會好好休息吧?」
賦恩將他拉到床邊,壓緊他的肩膀讓他順勢坐下,搓著手走到牆邊的空調控制面板前,看著室內溫度驟降到只剩十度,忍不住全身顫抖。
「真是的,暖氣不能再開的強一點嗎?」
他急躁的按著調整溫度按鍵,只要在這個人身邊就無法和這種麻煩事絕緣, 一回頭,看見那個麻煩用被單把自己緊緊包覆,屈著膝蓋坐在床中央,不需要持有工作時必備的寫實工整,此時的他看起來僅有不按牌理呈列的本質,像一杯只順著日常光線引位、移動折射的光源,卻在杯中靜止不動的清水。
賦恩學他將被單纏捲在身上,坐到他身旁,像哄著想要衝進泥地裡大滾一場的小孩一樣語氣柔軟的說「忍耐一下,我已經調高溫度了,等溫度上升就會比較舒服了。」
牧典只是沉默的稍微傾倒身體,將整個重心依附在他身上,賦恩隨即反射的僵直背脊,謹慎的將他撐托住,沒有規律散落在肩頭的髮絲,飄散出和自己一樣的飯店洗髮精,廉價的甜膩馨香,閉著眼睛像安枕自己在沒有意識起伏的最底層。
「最近我常常在想,我都會在什麼時後被人想起?」
「可以說清楚一點嗎?」他的思維總是像不知何時會瞬間點燃炸開的火藥一般,充滿臨時而毫無連續性的曖昧,賦恩覺得無論過多久,他都還是沒辦法銜接上他完全沒有規律節奏的想法。
「譬如說。」他將頭往上仰,尋找和他對視的角度,「你在想起"情人"的時候,腦子就會自然出現你愛戀的人,想起"家人"的時候,就會出現思念的父母親,這種需要依靠一個捷徑符號對應的連繫,懂了嗎?假設你哪一天不再是我的魔術助理了,你在想到什麼時後會想起我?」
「忙到胃發炎的時候。」
賦恩快速的從"最磨人的老闆"、"頭號麻煩人物"、"沒有基本生活能力的人"這些選項裡撿出最沒有殺傷力的一個來回答。
「好─沒─創─意。」他像把員工加班一星期的血汗企畫書,駁回的丟在桌上的鐵血上司般不滿的抱怨。
「那老師呢?你該不會是在回憶"被我發最多好人卡的人"的時候才會想起我吧?」賦恩邊說邊稍微的挪動已經有些痠麻的肩膀。
「這個嘛…。」他邊想邊將身體喬到一個最舒適的角度,
「大概就是這種覺得很溫暖的時候吧?」
說完他就沒有再丟擲出任何言語,慢慢的調頻呼吸接近安睡的頻率,賦恩只是溫順的充當他盡職的靠枕,因為他非常明白他已經好幾個月都沒能好好睡一覺了。
也非常明白,你在一睜開眼,就要率軍征討充滿煙硝瀰漫的戰場,必須將部分的自己不露痕跡的殉葬在陰暗土壤裡,但孤寂卻是其中唯一仍然瀰漫著腐敗氣味,繼續生長倖存的東西。
在被無數目光和唯一凝聚視界的聚光燈包圍下的你,台下所有的人都是在你之外的旁觀者,而你始終只有一個人。
其實你真的,非常寂寞。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在萬花筒裡失眠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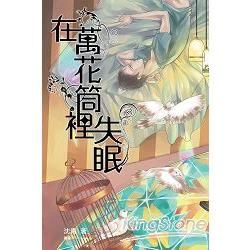 |
在萬花筒裡失眠 作者:沈青 出版社: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2-04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4 |
言情小說 |
$ 198 |
中文書 |
$ 198 |
同志文學/小說 |
$ 198 |
大眾文學 |
$ 19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在萬花筒裡失眠
「假設你哪一天不再是我的魔術助理了,你會在什麼時候想起我?」
一開始,只是想要成為他。
仰望著這個站在魔術界頂端的魔術師,創造出萬花筒一樣璀麗的鏡象盛宴,承擔著魔術師的原罪,只能一個人獨行黑夜,在這片黑暗裡穿越鏡子的另一端,讓鏡子外全然相反的世界,繼續揣摩裡頭顛倒的真相。
在朝夕的陪伴、貼近他的內心之後,明白了在被無數目光和唯一凝聚視界的聚光燈包圍下的他,台下所有的人都是充滿距離的旁觀者,他始終只有一個人。
才發現自己從一開始就不是執迷於他瞬燃的光,而是他純粹性格的真實原色,於是我再也不在乎是否能成為他了,我想拿起他的手背放到唇邊,說我願意,我願意把你的一切承擔起來,我願意走入你的暗處,試著去理解,愛情如何在我們一起穿行過黑夜之後燃起新的黎明……。
作者簡介:
沈青,1983年8月生,信仰完美主義的處女座,31歲,現為平面設計師。
曾獲幾個文學獎。
創作是我忠誠溫柔的伴侶。
無暇和文字獨處的時候,我把自己蓋印在平庸的生活紙面上,他就靜默不語的在角落等我,靜靜的發芽結株,繁茂的叢生,靜落成綠蔭幽微的樹林,無葉也無根,我輕碰觸他時花苞就紛落,我在日常時把自己稀釋的足以透光,沒有自己的語言,一日復一日像稍縱即逝的默片,承擔過於安適的重量。
章節試閱
1.光的行進
賦恩緩慢的沿著階梯走進空盪的觀眾席,仔細的掃視花了整個下午排置定位的舞台空間,空氣裡少了聲息的支撐,連隨著軟厚的橡膠鞋底落下的腳步聲,都足以透澈出清晰的音頻,眼神一下落定在舞臺的觀眾席第四排中央,坐著那位明天就要以被譽為最年輕就能展開世界巡演的亞洲天才魔術師的身影。
賦恩叮嚀著自己收斂最輕的腳步,安靜的站定離他的座位有些距離的斜後方,在他思考的時候他絕對不會出聲破壞,讓這個把意念昇華為實境的昂貴時刻出現裂縫。
他從後側看著他輕闔雙眼,放鬆的交疊雙腳,難得重獲閒暇的十指,交縫相扣的安...
賦恩緩慢的沿著階梯走進空盪的觀眾席,仔細的掃視花了整個下午排置定位的舞台空間,空氣裡少了聲息的支撐,連隨著軟厚的橡膠鞋底落下的腳步聲,都足以透澈出清晰的音頻,眼神一下落定在舞臺的觀眾席第四排中央,坐著那位明天就要以被譽為最年輕就能展開世界巡演的亞洲天才魔術師的身影。
賦恩叮嚀著自己收斂最輕的腳步,安靜的站定離他的座位有些距離的斜後方,在他思考的時候他絕對不會出聲破壞,讓這個把意念昇華為實境的昂貴時刻出現裂縫。
他從後側看著他輕闔雙眼,放鬆的交疊雙腳,難得重獲閒暇的十指,交縫相扣的安...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沈青
- 出版社: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2-06 ISBN/ISSN:978986911173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72頁 開數:12.7*19cm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大眾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