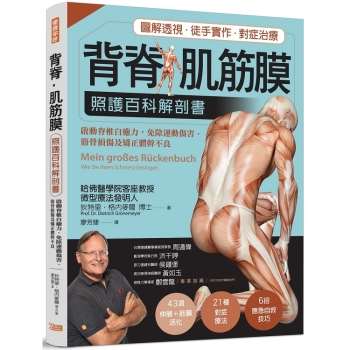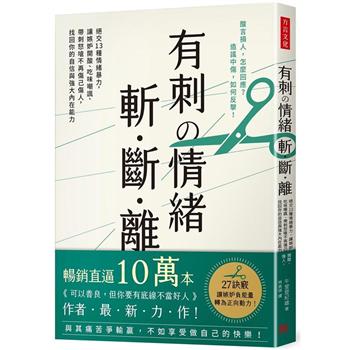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說客遊戲原是夢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5 |
二手中文書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政治 |
$ 225 |
政治評論 |
$ 225 |
國際關係 |
$ 225 |
文學作品 |
$ 225 |
政治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說客遊戲原是夢
內容簡介
在驚滔駭浪中登上總統寶座的李登輝,採取類台獨路線以及金錢外交策略,另一方面,國民黨的黨產管理委員會主任劉泰英聘請了卡西迪公關公司對美國政府施壓,引爆了95/96年的台海危機。美國行政部門切斷了與台灣駐美機構的聯絡管道,並派遣密使來台試圖與國民黨管委會接觸。作者受人之託,安排美國密使來台行程,並成功引薦密使密道頓與劉泰英會晤,不料,卻在無意中捲進日後亞洲週刊所謂的台灣對美政治獻金風暴。書中揭露了這段外交秘辛,並記述了20年來兩岸政經與國際外交情勢翻轉的種種。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朝平
1954年,生於台灣的「半山」(或稱之為芋頭番薯),巨蟹座。自認頗有文化創意的基因,但從未被證實。
就讀建中時,不情不願地加入國民黨,催化了他叛逆的性格。政大外交系畢業,服預官役時,因緣際會分發到金門101兩棲偵查營,擔任政戰官,得以反思國民黨的反共教育,開啟了他與兩岸關係的命運鏈接。
退伍後回母校攻讀政治研究所期間,連續三屆獲得時報雜誌評論文徵文的首獎,評審團的評語說他:「對社會不公不平事件,反應強烈。」徵文得獎,啟動了他投身大眾傳媒的通關密語。他曾經任職聯合報系、中國時報系,成績不俗;創辦過第一本報導海峽兩岸財經動態的雜誌,也曾經擔任過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的理事長,卻皆以挫折收場。
過去1/4個世紀裡,他參與了海峽兩岸文化經貿交流、台灣電信與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的過程,也親眼見證了兩岸政經實力的消長
陳朝平
1954年,生於台灣的「半山」(或稱之為芋頭番薯),巨蟹座。自認頗有文化創意的基因,但從未被證實。
就讀建中時,不情不願地加入國民黨,催化了他叛逆的性格。政大外交系畢業,服預官役時,因緣際會分發到金門101兩棲偵查營,擔任政戰官,得以反思國民黨的反共教育,開啟了他與兩岸關係的命運鏈接。
退伍後回母校攻讀政治研究所期間,連續三屆獲得時報雜誌評論文徵文的首獎,評審團的評語說他:「對社會不公不平事件,反應強烈。」徵文得獎,啟動了他投身大眾傳媒的通關密語。他曾經任職聯合報系、中國時報系,成績不俗;創辦過第一本報導海峽兩岸財經動態的雜誌,也曾經擔任過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的理事長,卻皆以挫折收場。
過去1/4個世紀裡,他參與了海峽兩岸文化經貿交流、台灣電信與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的過程,也親眼見證了兩岸政經實力的消長
目錄
中共軍演威嚇中總統大選的前哨戰開打 95
遠東飯店撞見二胡一密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99
暴風雨來襲前的寧靜 105
捲起千堆雪 政治獻金疑雲悄然擴散 108
──去年4月間首度來台 未見劉泰英會晤饒穎奇
──去年7月第二度來台 與企業界餐敘並晤林洋港
──8月1日會見劉泰英 密道頓表示負募款任務
──劉9月赴美晤柯林頓 展開中美高層接觸管道
亞洲週刊點燃了政治獻金疑案的引信 115
──四度赴台晤政商名人
──劉泰英證實晤密道頓
──美軍母艦護台有價
──密道頓聞捐款喜出望外
一步步踏入風暴圈裡 122
──冷眼旁觀政客與媒體的演出
──且看政府高層如何操縱媒體報導
──看穿了高層官員的烏賊戰術
李登輝:這個問題絕對沒有! 136
劉泰英的聲明疑點重重 141
──總統府高層越幫越亂 劉泰英選擇性失憶?
正面迎戰公開對質 試圖嚇阻追殺 147
──婉拒了趙少康、李濤專訪的邀約
──比對各家媒體報導 設法找出矛盾點
──擬定A計畫 先求不敗再求緩轉
什麼原因導致溝通管道全面關閉? 163
消極怯戰 何如以戰止戰? 169
──公開對質?赴美作證?來者不拒
記者會後效發酵 美國展開調查行動 177
──在場的關鍵第四人浮出水面
──克明兄發表三點聲明
究竟是政治顧問、公關,還是掮客? 188
──接受國際媒體採訪 遂行內銷轉外銷戰略
原是夢
──接受NBC首席特派員安卓麗.米雪爾的訪問
台灣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淪為政治打手? 199
提告同時,威京小沈捎來和解的訊息 204
石齊平與施智謀臨門一腳,我走上和解之路 209
──和曾宗廷、羅明通大律師的第一次接觸
──陳長文、范光群都拒絕代理我
──開庭前穿梭在兩陣營之間
我和劉泰英的律師團在法庭內展開攻防戰 223
第一次開庭後國內外輿論如何反應 227
邁向和解之路 231
──那天下午,我們和解了!
為何劉泰英、密道頓將我從記憶庫裡刪除? 236
從三外交個案對照1500萬美金政治獻金的真假 241
──先談巴紐建交案
──與巴國往來 我砸重金
──又是李登輝!
政治獻金疑案人物誌 249
──鳥盡弓藏、天命終究難觀─側寫劉泰英
──宦海浮沉終不悔的外交幹才─夏立言
──知識青年革命尚未成功,丁守中奮鬥不懈
──從哈佛回歸到中國道統與經典─李克明
──洞悉時事、經世致用的經濟學家石齊平
尾聲 278
附錄 282
遠東飯店撞見二胡一密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99
暴風雨來襲前的寧靜 105
捲起千堆雪 政治獻金疑雲悄然擴散 108
──去年4月間首度來台 未見劉泰英會晤饒穎奇
──去年7月第二度來台 與企業界餐敘並晤林洋港
──8月1日會見劉泰英 密道頓表示負募款任務
──劉9月赴美晤柯林頓 展開中美高層接觸管道
亞洲週刊點燃了政治獻金疑案的引信 115
──四度赴台晤政商名人
──劉泰英證實晤密道頓
──美軍母艦護台有價
──密道頓聞捐款喜出望外
一步步踏入風暴圈裡 122
──冷眼旁觀政客與媒體的演出
──且看政府高層如何操縱媒體報導
──看穿了高層官員的烏賊戰術
李登輝:這個問題絕對沒有! 136
劉泰英的聲明疑點重重 141
──總統府高層越幫越亂 劉泰英選擇性失憶?
正面迎戰公開對質 試圖嚇阻追殺 147
──婉拒了趙少康、李濤專訪的邀約
──比對各家媒體報導 設法找出矛盾點
──擬定A計畫 先求不敗再求緩轉
什麼原因導致溝通管道全面關閉? 163
消極怯戰 何如以戰止戰? 169
──公開對質?赴美作證?來者不拒
記者會後效發酵 美國展開調查行動 177
──在場的關鍵第四人浮出水面
──克明兄發表三點聲明
究竟是政治顧問、公關,還是掮客? 188
──接受國際媒體採訪 遂行內銷轉外銷戰略
原是夢
──接受NBC首席特派員安卓麗.米雪爾的訪問
台灣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淪為政治打手? 199
提告同時,威京小沈捎來和解的訊息 204
石齊平與施智謀臨門一腳,我走上和解之路 209
──和曾宗廷、羅明通大律師的第一次接觸
──陳長文、范光群都拒絕代理我
──開庭前穿梭在兩陣營之間
我和劉泰英的律師團在法庭內展開攻防戰 223
第一次開庭後國內外輿論如何反應 227
邁向和解之路 231
──那天下午,我們和解了!
為何劉泰英、密道頓將我從記憶庫裡刪除? 236
從三外交個案對照1500萬美金政治獻金的真假 241
──先談巴紐建交案
──與巴國往來 我砸重金
──又是李登輝!
政治獻金疑案人物誌 249
──鳥盡弓藏、天命終究難觀─側寫劉泰英
──宦海浮沉終不悔的外交幹才─夏立言
──知識青年革命尚未成功,丁守中奮鬥不懈
──從哈佛回歸到中國道統與經典─李克明
──洞悉時事、經世致用的經濟學家石齊平
尾聲 278
附錄 282
序
序
光輝的10月過後,還有11月12日的國父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12月25日的行憲紀念日,以及1月1日元旦。這些假日,從街頭到媒體,照例充斥著與國父孫中山、蔣氏家族以及國民黨有關的政治圖騰、符號與歌曲。對學生而言,這些國定假日,只不過又是一個個不必上課的日子,在排山倒海而來升學壓力下,我們近似麻痹地、默默地接納這些反共的政治符號。
是的,我們這一代就是這樣度過了青澀的青少年時代,反共、愛國、領袖、團結,這些價值觀念已經內化到我們青春的熱血裡,另一方面,我們懵懵懂懂的腦海裡,卻也開始質疑這些從小到大、視為當然的價值觀,開始懷疑反攻大陸的真實性與可行性。不過這些質疑、懷疑,都只能潛藏在心靈最幽暗的角落裡,我們,噤若寒蟬,匍匐在一旁角落,遠遠地、靜靜地,等待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學校閱報欄上的中央日報成篇累牘的刊登著珠江口漂流出來的浮屍照片,紅衛兵押著黑五類分子遊街、被鬥爭的男女,頭戴著紙糊的高帽,舉步維艱……到了夜裡,一張張新聞照片,化作一幕幕的夢魘,夾雜著父親三更半夜哭喊祖母的嗚咽,如夢似真,鐵幕裡的神州大陸,共產黨群眾大會鬥爭的猙獰面貌……揮之不去。
那年秋天,我進了高中,下課後,除了流連在南昌街彈子房外,遠遠看著獨臂球王穩穩地敲進每一顆球外,便是漫步在牯嶺街的舊書攤,偷偷翻閱著一本本泛黃的禁書,「自
由中國」雜誌、魯迅的《吶喊》、巴金的《寒夜》、《金瓶梅》,夾雜駐台美軍留下的「Playboy」,似懂非懂。接著,又瘋狂地迷上了西洋歌曲,聽黑膠唱片、收聽收音機裡美軍電台的流行音樂排行榜、模仿外國歌星的身體語言,甚至在建中書包畫上了帶有嬉皮風的圖案……高中三年,為賦新辭強說愁的那顆少年心裡,叛逆與懷疑的種子,越發地茁壯了。
原是夢
悲壯地宣布退出聯合國,引發斷交的骨牌效應。在這種情勢下,考進外交系,多少有些反諷的意味。
政治大學的前身是國民黨在南京所創辦的中央政治學校,素有黨校之稱,儘管如此,我在政大遇見的師長,極多學識淵博、風骨嶙峋者。大一政治學的授課教授是政治學方法論的權威──易君博師;教授經濟學的夏道平教授,曾經翻譯政治經濟學大師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夏師與雷震、殷海光並稱「自由中國」半月刊三大主筆;大三教我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教席,則是台灣政治思想史的泰斗朱堅章教授。在三位恩師和其他老師的引領下,四年大學生涯,我真正體會到了論語所說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我學會了思辨之道,學會了不盲從權威,學會了透過理性辯論去挑戰權威。
當然啦,從1971年發酵的中華民國外交危機,以及接踵而來的越戰情勢逆轉、美國爆發的反戰風潮、西貢淪陷、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漂流海上……一波波與冷戰有關、和國際共產陣線擴張有關的新聞,在我大學四年的日子裡,持續地衝擊著台灣這小島,衝擊著我們徬徨不安的心靈。「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依然是多數青年學子的夢。
1975年4月,清明節凌晨,「民族救星」、「一代偉人」總統蔣公崩逝,是晚,雷電交加,風雨如晦。第二天清早,市容瞬間由彩色轉為黑白,人人面露哀戚之色,二、三十年來習以為常的世界,頓時崩解,三軍將士進入一級警備狀態,防止共軍蠢動。觀看著電視裡如喪考妣的群眾,在烈日下大排長龍,等著瞻仰著蔣介石的遺體,我有著莫名的感動,卻又混和著不以為然的荒謬──蔣家王朝的舊時權威消失了,一個新的權威即將誕生!
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發生芮氏規模7.8的大地震,唐山頃刻間夷為平地,死傷30餘萬人。電視整點新聞反覆地播放著地震災後慘狀的畫面,忽然間,心裡興起「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情懷,就在那一刻,人道的關懷飛越了意識形態的藩籬。8月,我入伍服預官役。
9月9日,中國大陸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遽逝,台灣海峽情勢變得極度緊張,預官受訓的成功嶺營區裡,瀰漫著一股焦躁與不安的情緒。
1977年4月中旬,剛剛受階為預官少尉的我,扛著草綠色的帆布軍用大背包,迷迷糊糊地踏上了金門料羅灣炙熱的海灘,又迷迷糊糊地被挑選到陸軍101兩棲偵察營,擔任政戰官。
兩棲偵察營又稱海龍部隊,也就是俗稱的蛙人部隊。在兩岸對峙的年代裡,蛙人部隊是金門全島唯一可以親近海灘、下海進行游泳、操舟訓練的部隊。人在金門,距離大陸如此的近,再加上蛙人部隊常會出海緝拿越界的大陸漁船,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有機會直接目擊、接觸「大陸同胞」以及他們海上的日常生活。可以這麼說,蝸居金門兩棲偵察營碉堡一年多的日子裡,正是我思辨兩岸關係與統獨問題的起始點。
1978年,我回到母校政治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是年12月,美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斷然宣布與美斷交,兩岸關係轉進一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1982年,時報雜誌舉辦第三屆評論文徵文比賽,我以「最艱鉅的政治工程──論中國統一問題的看法」一文,榮獲首獎。從那時起,身為博士班學生,我嘗試用不同的理論,去推論兩岸關係的可能演變;而做為一個媒體工作者,也因徵文得獎,有更多的機緣參與統獨辯證。儘管如此,廁身媒體前後12年的我,從沒有機會到大陸從事採訪工作,直到離開媒體、投身商海後,才有機會親炙神州大陸這塊土地。
1992年,我公司為華康科技籌辦第一屆全球中文造字比賽,比賽結果出爐,第二、三名獲獎者都是大陸印刷廠的造字師傅,我們決定到北京去舉行頒獎典禮。
金秋時節,初履大陸,黃昏時刻,落霞絢麗,飛機即將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俯瞰一望無垠的神州大地,內心深處泛起了無比的悸動,卻還帶著一絲絲陌生與不安。
原是夢
秋天的北京,晚霞倏忽隱去,踏進海關時,老舊的首都機場更顯昏暗,機場裡遇到的男男女女,臉龐上盡刻畫著苦難歲月的痕跡,不見笑容,隱隱帶著一股狐疑與肅殺。
北京的第一夜,我在下榻的中苑賓館仰望一輪明月,忽地憶起服役金門時,料羅灣上空的那輪明月,又忽地憶起白居易「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的詩句。千百年來,這輪明月,看盡世間戰亂與和平,看盡人間生離死別,逝者已矣,我輩青年,難道不能為兩岸和平、為世世代代中國人幸福,稍盡綿薄?當晚,思潮洶湧,輾轉難眠,於是發願,果有機會為兩岸和平貢獻一己,定當竭盡所能。
機緣來了!1995年春,李登輝的類台獨路線和國民黨的金錢外交,將海峽兩岸關係導入1949年以來最嚴峻的態勢,戰爭一觸即發。當時,解鈴,既不能寄望於繫鈴人,只能寄望華盛頓當局恢復與台灣溝通的管道。打開溝通管道的鑰匙,剛巧交到了我手上,我毫不遲疑的接下了這把鑰匙。密道頓、劉泰英以及政治獻金疑案爆發後,很多人質疑我的忠貞,質疑我的立場,我從未辯駁,也不打算辯駁。如今,我願意說──「我們這一代最愛台灣,因為,我們生於斯、長於斯,台灣是哺育我們這一代的沃土,也是我們這一代棲風避雨的所在。我們這一代,最是渴望和平安寧、渴望安定繁榮,因為,我們的父執輩和我們這一代,都飽受戰爭的恐懼,都沒有免於飢餓的自由,沒有免於匱乏的自由。我們這一代,最痛恨獨裁專制,但面對獨裁專制,我們寧取改革,怯懦於革命,儘管,我們知道改革比革命更難,但我們深知,革命是千萬人頭落地的事業,是獨裁專制惡性循環的開端。我們這一代,有根深柢固的民族意識,因為,我們飽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荼毒,我們明白中國的命運、中國的分裂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密不可分。我們這一代的價值體系,和某些人是格格不入的,我們未見得鍾愛統一,但我們確信台獨不可能帶來和平,我們同情228事件以及所有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與家屬,但是,我們卻只能默默地吞下屬於我們這一代的悲哀、痛苦與共業……。」
2009年,齊邦媛教授出版了巨流河一書,我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將全書讀完,深受啟發。我覺得,我有義務、也有權利,將1995/1996年間國民黨對美政治獻金疑雲的秘辛披露出來,警惕來者。2010年春,我辭去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職務,開始構思本書。期間,雜事纏身、進度遲緩,直到2013年夏天,才加快了寫作的速度。2014年終,初稿完成,幾經修飾訂正,又因搬家,校正工作延宕,直到2015年9月才與世界日報洽妥代為印刷出版事宜。
《說客遊戲原是夢》一書,忠實地記錄了密道頓兩度來台、與劉泰英密會、亞洲週刊報導所謂政治獻金醜聞、以及我如何捲入此一轟天大案的的過程,也夾議夾敘地回溯了這20年來,我親眼目睹海峽兩岸政經變化以及繁榮翻轉的點點滴滴。
曾經是媒體工作者的一員,又是事件的當事人,我盡其可能、客觀地追述當年那些曾經發生過、而讀者諸君有所不知道的秘辛。天底下,沒有真正的客觀,所謂客觀,是指交互主觀,是許多主觀交叉辯證所得、是比較上的客觀。書中陳述的主觀部分,多係我個人親身經歷者,讀者無從證明其真假,只能信賴我的誠實。
本書內容,可說是一個退役媒體工作者、一個曾經是資深政治遊說者的回憶錄,也可視為一個穿梭兩岸四分之一世紀的小商人,對過往這些年兩岸歷史發展的喟嘆。
一轉眼,密道頓與政治獻金疑案已過了20年,20年來,我常在想:
假如,我沒有答應夏立言學長的請託;
假如,我拒絕接待密道頓和崔雅琳;
假如,李登輝沒有回訪母校康乃爾;
假如,李登輝去了康乃爾,但沒發表「我心長在」的演講;
假如,密道頓沒有見到劉泰英;
假如,劉泰英沒有參加柯林頓的募款餐會;
假如,亞洲週刊沒有持續追蹤台海危機期間美軍派遣航母
原是夢
巡弋台灣海峽;
假如,我沒有在遠東飯店撞見胡定吾、胡志強與密道頓;
假如……太多、太多的假如發生時,1995到1996年,這段歷史會不會因此改寫?我個人的機遇會不會因而改觀?今日兩岸情勢又將如何?或者,這一切、一切,根本就是宿命?在歷史的長河裡,個人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塵埃,換了其他人上陣,場景依舊,故事依然要發生?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海峽兩岸,最終,還是難逃歷史鐵律?試問,歷史長河裡,您,又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
2015年10月8日寫於新店溪畔
光輝的10月過後,還有11月12日的國父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12月25日的行憲紀念日,以及1月1日元旦。這些假日,從街頭到媒體,照例充斥著與國父孫中山、蔣氏家族以及國民黨有關的政治圖騰、符號與歌曲。對學生而言,這些國定假日,只不過又是一個個不必上課的日子,在排山倒海而來升學壓力下,我們近似麻痹地、默默地接納這些反共的政治符號。
是的,我們這一代就是這樣度過了青澀的青少年時代,反共、愛國、領袖、團結,這些價值觀念已經內化到我們青春的熱血裡,另一方面,我們懵懵懂懂的腦海裡,卻也開始質疑這些從小到大、視為當然的價值觀,開始懷疑反攻大陸的真實性與可行性。不過這些質疑、懷疑,都只能潛藏在心靈最幽暗的角落裡,我們,噤若寒蟬,匍匐在一旁角落,遠遠地、靜靜地,等待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學校閱報欄上的中央日報成篇累牘的刊登著珠江口漂流出來的浮屍照片,紅衛兵押著黑五類分子遊街、被鬥爭的男女,頭戴著紙糊的高帽,舉步維艱……到了夜裡,一張張新聞照片,化作一幕幕的夢魘,夾雜著父親三更半夜哭喊祖母的嗚咽,如夢似真,鐵幕裡的神州大陸,共產黨群眾大會鬥爭的猙獰面貌……揮之不去。
那年秋天,我進了高中,下課後,除了流連在南昌街彈子房外,遠遠看著獨臂球王穩穩地敲進每一顆球外,便是漫步在牯嶺街的舊書攤,偷偷翻閱著一本本泛黃的禁書,「自
由中國」雜誌、魯迅的《吶喊》、巴金的《寒夜》、《金瓶梅》,夾雜駐台美軍留下的「Playboy」,似懂非懂。接著,又瘋狂地迷上了西洋歌曲,聽黑膠唱片、收聽收音機裡美軍電台的流行音樂排行榜、模仿外國歌星的身體語言,甚至在建中書包畫上了帶有嬉皮風的圖案……高中三年,為賦新辭強說愁的那顆少年心裡,叛逆與懷疑的種子,越發地茁壯了。
原是夢
悲壯地宣布退出聯合國,引發斷交的骨牌效應。在這種情勢下,考進外交系,多少有些反諷的意味。
政治大學的前身是國民黨在南京所創辦的中央政治學校,素有黨校之稱,儘管如此,我在政大遇見的師長,極多學識淵博、風骨嶙峋者。大一政治學的授課教授是政治學方法論的權威──易君博師;教授經濟學的夏道平教授,曾經翻譯政治經濟學大師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夏師與雷震、殷海光並稱「自由中國」半月刊三大主筆;大三教我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教席,則是台灣政治思想史的泰斗朱堅章教授。在三位恩師和其他老師的引領下,四年大學生涯,我真正體會到了論語所說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我學會了思辨之道,學會了不盲從權威,學會了透過理性辯論去挑戰權威。
當然啦,從1971年發酵的中華民國外交危機,以及接踵而來的越戰情勢逆轉、美國爆發的反戰風潮、西貢淪陷、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漂流海上……一波波與冷戰有關、和國際共產陣線擴張有關的新聞,在我大學四年的日子裡,持續地衝擊著台灣這小島,衝擊著我們徬徨不安的心靈。「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依然是多數青年學子的夢。
1975年4月,清明節凌晨,「民族救星」、「一代偉人」總統蔣公崩逝,是晚,雷電交加,風雨如晦。第二天清早,市容瞬間由彩色轉為黑白,人人面露哀戚之色,二、三十年來習以為常的世界,頓時崩解,三軍將士進入一級警備狀態,防止共軍蠢動。觀看著電視裡如喪考妣的群眾,在烈日下大排長龍,等著瞻仰著蔣介石的遺體,我有著莫名的感動,卻又混和著不以為然的荒謬──蔣家王朝的舊時權威消失了,一個新的權威即將誕生!
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發生芮氏規模7.8的大地震,唐山頃刻間夷為平地,死傷30餘萬人。電視整點新聞反覆地播放著地震災後慘狀的畫面,忽然間,心裡興起「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情懷,就在那一刻,人道的關懷飛越了意識形態的藩籬。8月,我入伍服預官役。
9月9日,中國大陸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遽逝,台灣海峽情勢變得極度緊張,預官受訓的成功嶺營區裡,瀰漫著一股焦躁與不安的情緒。
1977年4月中旬,剛剛受階為預官少尉的我,扛著草綠色的帆布軍用大背包,迷迷糊糊地踏上了金門料羅灣炙熱的海灘,又迷迷糊糊地被挑選到陸軍101兩棲偵察營,擔任政戰官。
兩棲偵察營又稱海龍部隊,也就是俗稱的蛙人部隊。在兩岸對峙的年代裡,蛙人部隊是金門全島唯一可以親近海灘、下海進行游泳、操舟訓練的部隊。人在金門,距離大陸如此的近,再加上蛙人部隊常會出海緝拿越界的大陸漁船,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有機會直接目擊、接觸「大陸同胞」以及他們海上的日常生活。可以這麼說,蝸居金門兩棲偵察營碉堡一年多的日子裡,正是我思辨兩岸關係與統獨問題的起始點。
1978年,我回到母校政治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是年12月,美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斷然宣布與美斷交,兩岸關係轉進一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1982年,時報雜誌舉辦第三屆評論文徵文比賽,我以「最艱鉅的政治工程──論中國統一問題的看法」一文,榮獲首獎。從那時起,身為博士班學生,我嘗試用不同的理論,去推論兩岸關係的可能演變;而做為一個媒體工作者,也因徵文得獎,有更多的機緣參與統獨辯證。儘管如此,廁身媒體前後12年的我,從沒有機會到大陸從事採訪工作,直到離開媒體、投身商海後,才有機會親炙神州大陸這塊土地。
1992年,我公司為華康科技籌辦第一屆全球中文造字比賽,比賽結果出爐,第二、三名獲獎者都是大陸印刷廠的造字師傅,我們決定到北京去舉行頒獎典禮。
金秋時節,初履大陸,黃昏時刻,落霞絢麗,飛機即將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俯瞰一望無垠的神州大地,內心深處泛起了無比的悸動,卻還帶著一絲絲陌生與不安。
原是夢
秋天的北京,晚霞倏忽隱去,踏進海關時,老舊的首都機場更顯昏暗,機場裡遇到的男男女女,臉龐上盡刻畫著苦難歲月的痕跡,不見笑容,隱隱帶著一股狐疑與肅殺。
北京的第一夜,我在下榻的中苑賓館仰望一輪明月,忽地憶起服役金門時,料羅灣上空的那輪明月,又忽地憶起白居易「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的詩句。千百年來,這輪明月,看盡世間戰亂與和平,看盡人間生離死別,逝者已矣,我輩青年,難道不能為兩岸和平、為世世代代中國人幸福,稍盡綿薄?當晚,思潮洶湧,輾轉難眠,於是發願,果有機會為兩岸和平貢獻一己,定當竭盡所能。
機緣來了!1995年春,李登輝的類台獨路線和國民黨的金錢外交,將海峽兩岸關係導入1949年以來最嚴峻的態勢,戰爭一觸即發。當時,解鈴,既不能寄望於繫鈴人,只能寄望華盛頓當局恢復與台灣溝通的管道。打開溝通管道的鑰匙,剛巧交到了我手上,我毫不遲疑的接下了這把鑰匙。密道頓、劉泰英以及政治獻金疑案爆發後,很多人質疑我的忠貞,質疑我的立場,我從未辯駁,也不打算辯駁。如今,我願意說──「我們這一代最愛台灣,因為,我們生於斯、長於斯,台灣是哺育我們這一代的沃土,也是我們這一代棲風避雨的所在。我們這一代,最是渴望和平安寧、渴望安定繁榮,因為,我們的父執輩和我們這一代,都飽受戰爭的恐懼,都沒有免於飢餓的自由,沒有免於匱乏的自由。我們這一代,最痛恨獨裁專制,但面對獨裁專制,我們寧取改革,怯懦於革命,儘管,我們知道改革比革命更難,但我們深知,革命是千萬人頭落地的事業,是獨裁專制惡性循環的開端。我們這一代,有根深柢固的民族意識,因為,我們飽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荼毒,我們明白中國的命運、中國的分裂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密不可分。我們這一代的價值體系,和某些人是格格不入的,我們未見得鍾愛統一,但我們確信台獨不可能帶來和平,我們同情228事件以及所有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與家屬,但是,我們卻只能默默地吞下屬於我們這一代的悲哀、痛苦與共業……。」
2009年,齊邦媛教授出版了巨流河一書,我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將全書讀完,深受啟發。我覺得,我有義務、也有權利,將1995/1996年間國民黨對美政治獻金疑雲的秘辛披露出來,警惕來者。2010年春,我辭去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理事長職務,開始構思本書。期間,雜事纏身、進度遲緩,直到2013年夏天,才加快了寫作的速度。2014年終,初稿完成,幾經修飾訂正,又因搬家,校正工作延宕,直到2015年9月才與世界日報洽妥代為印刷出版事宜。
《說客遊戲原是夢》一書,忠實地記錄了密道頓兩度來台、與劉泰英密會、亞洲週刊報導所謂政治獻金醜聞、以及我如何捲入此一轟天大案的的過程,也夾議夾敘地回溯了這20年來,我親眼目睹海峽兩岸政經變化以及繁榮翻轉的點點滴滴。
曾經是媒體工作者的一員,又是事件的當事人,我盡其可能、客觀地追述當年那些曾經發生過、而讀者諸君有所不知道的秘辛。天底下,沒有真正的客觀,所謂客觀,是指交互主觀,是許多主觀交叉辯證所得、是比較上的客觀。書中陳述的主觀部分,多係我個人親身經歷者,讀者無從證明其真假,只能信賴我的誠實。
本書內容,可說是一個退役媒體工作者、一個曾經是資深政治遊說者的回憶錄,也可視為一個穿梭兩岸四分之一世紀的小商人,對過往這些年兩岸歷史發展的喟嘆。
一轉眼,密道頓與政治獻金疑案已過了20年,20年來,我常在想:
假如,我沒有答應夏立言學長的請託;
假如,我拒絕接待密道頓和崔雅琳;
假如,李登輝沒有回訪母校康乃爾;
假如,李登輝去了康乃爾,但沒發表「我心長在」的演講;
假如,密道頓沒有見到劉泰英;
假如,劉泰英沒有參加柯林頓的募款餐會;
假如,亞洲週刊沒有持續追蹤台海危機期間美軍派遣航母
原是夢
巡弋台灣海峽;
假如,我沒有在遠東飯店撞見胡定吾、胡志強與密道頓;
假如……太多、太多的假如發生時,1995到1996年,這段歷史會不會因此改寫?我個人的機遇會不會因而改觀?今日兩岸情勢又將如何?或者,這一切、一切,根本就是宿命?在歷史的長河裡,個人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塵埃,換了其他人上陣,場景依舊,故事依然要發生?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海峽兩岸,最終,還是難逃歷史鐵律?試問,歷史長河裡,您,又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
2015年10月8日寫於新店溪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