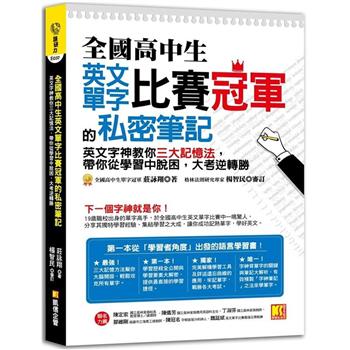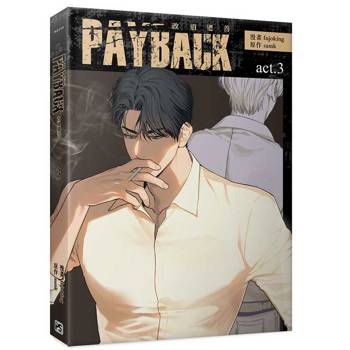藝術.啟蒙.黑暗.愛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瑪斯.曼一生最鍾愛作品
遲到近七十年的經典,台灣首度翻譯出版!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瑪斯.曼一生最鍾愛作品
遲到近七十年的經典,台灣首度翻譯出版!
附蘇珊.桑塔格回憶十四歲拜見托瑪斯.曼之〈朝聖〉
翻譯家彭淮棟「夢魘」之譯作,譯者導論兩萬字,譯注三萬五千字
有人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人可以獲得兩次諾貝爾文學獎,此人便是托瑪斯.曼;第一次可以憑《魔山》得獎,第二次則可憑《浮士德博士》。
「這本書於我十分珍貴。它是我一生的總結,是我所親歷的這個時代之總結,同時也是我有生以來所能給出的最為個人的東西,其坦率近乎瘋狂。」――托瑪斯.曼
德國大文豪托瑪斯.曼最後一部偉大小說,首次發表於1947年,是德國浮士德傳說的現代版,即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的故事。本書為托瑪斯.曼晚年最令人揪心和震撼的鴻篇巨著,作者本人也對其異常重視,視其為「一生的懺悔」、「最大膽和最陰森的作品」。在生前最後一次接受採訪中,托瑪斯.曼非常明確地表示這本藝術家小說是他的最愛:「這部浮士德小說於我珍貴之極……它花費了我最多的心血……沒有哪一部作品像它那樣令我依戀。誰不喜歡它,我立刻就不喜歡誰。誰對它承受的精神高壓有所理解,誰就贏得我的由衷感謝。」
小說主角為作曲家阿德里安,其原型為德國哲學家尼采。少年時即顯露出天資聰穎、才華橫溢、孤傲自賞、野心勃勃的姿態,是一位有音樂天賦,前程似錦的年輕人,但他不滿足於現狀並追求「真正偉大的成功」,因此與魔鬼交易,換取24年音樂靈感與創造力。他激進的新音樂,如同危險的遊戲,在不可能的邊緣地帶操弄。作為對24年無與倫比的音樂成就之回報,他交換他的靈魂與他愛人的能力,在此期間,他的靈魂歸魔鬼所有,而且不可以愛人。
就在他的藝術不斷提升時,周圍環境卻不斷出現道德墮落的危機現象,他本人也開始違背不許愛人的禁令;他身邊開始不斷有人死亡,熟人自殺,他的同性戀男友被有夫之婦槍殺,阿德里安悲憤欲絕,猛然覺醒,他要對他的一生懺悔……
本書不但是是托瑪斯.曼最深沉的藝術表達,阿德里安的生平也是個輝煌的寓言,暗喻納粹德國的崛起,以及德國人民摒棄人性、擁抱野心與虛無主義。這也是托瑪斯.曼對德國天才與真正偉大的藝術家,對他們可怕的責任最深刻的沉思。
本書特色
1. 托瑪斯.曼晚年最重要作品,有書評認為他憑此書可以再得一次諾貝爾文學獎。
2. 本書翻譯難度甚高,知識淵博、文筆優美、技巧高超,更勝托瑪斯.曼另一代表作《魔山》,但小說情節仍然具有吸引力與可讀性。
3. 1947年出版以來,台灣從未有中文翻譯,翻譯家彭淮棟學養深厚,尤其熟悉古典音樂知識,卻仍需費時兩年半嘔心瀝血,翻譯過程稱之為「夢魘」。
4. 隨書附導讀譯注本,收錄蘇珊.桑塔格回憶十四歲時與朋友拜訪托瑪斯.曼之散文〈朝聖〉,文長一萬五千字。
5. 譯者導論兩萬字,翔實譯注三萬五千字,幫助讀者全盤理解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