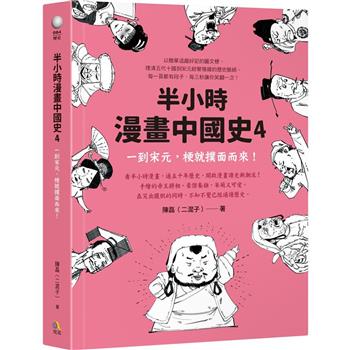譯者序
去向身體殿堂的更深處
科學院裡的性愛
2000年10月5日下午,座落在布達佩斯多瑙河畔鏈子橋佩斯一側橋頭的匈牙利科學院大禮堂裡座無虛席,四壁輝煌,氣氛莊重,文藝界精英濟濟一堂,參加納道詩.彼得院士的就職典禮。按常規,入選塞切尼文學與藝術學院院士後,一年內就要搞就職典禮,作家講演,畫家辦展,音樂家舉行音樂會,但是納道詩先生由於入選院士一個月後就心臟病突發,因此一拖就拖到了千禧年。在炫耀著歷史輝煌的大禮堂內,所有人都像在歌劇院裡一樣著正裝,穿禮服,端坐,輕咳,越過人頭用含蓄的微笑相互打招呼,耐心地等待大作家出場。
之前的兩天,納道詩曾在一次媒體採訪中透露說,他的就職講演將是朗讀幾十頁正在寫的作品,至於什麼內容,作家守口如瓶,只是說,他在朗讀時會留意聽眾的反應;如果喜歡,他們會高興地鼓掌,也許不喜歡,他們會一聲不響地摔門而去,「通常誰都不會談論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我可以開一扇小門,人們能從這裡進來一下,不過我很快會把門關上……我想做某種調查,這也屬於我工作的一部分。」納道詩的這段話,早已吊足了來賓的胃口。
掌聲中,納道詩西裝革履地走上演講台。他個子不高,面皮白淨,氣質儒雅,舒眉悅目,鏡片後不露鋒芒的眼神裡既有長者的智睿,也有孩子的狡黠。他拿著一疊書稿走到麥克風後,沒有過度地朗讀起來,聲調不高,音色豐富,節奏沉著,吐字清晰,隨著他繪聲繪色的朗讀,大堂裡變得鴉雀無聲,寂靜也發生著微妙的改變,空氣變得粘稠,凍結,不少聽眾的面色變得越來越不自在,越來越僵硬,呼吸或急促,或停滯……就連譯過不少納道詩作品的羅馬尼亞翻譯家安娜瑪麗婭•帕普也驚得張大了嘴巴,坐在他身邊的作家艾斯特哈茲•彼得開玩笑地提醒:「嘿,把嘴閉上,小心蒼蠅飛進去。」
納道詩讀完了,離開麥克風,台下始終沒有反應,沒有交頭接耳,也沒有延遲的掌聲。事後,納道詩像做了一個自己也覺得有點過分的惡作劇的孩子解釋說,「我把我自己也嚇了一跳」。那天他到底讀了什麼?其實也沒什麼,只是讀了他當時正在寫的一部書中的一個片段……在匈牙利科學院官網有關院士就職演講的網頁上可以查到,納道詩讀的是《平行故事》第一部《喑啞地帶》的最後一章:〈心寧神靜的緣由〉。
納道詩說,阿古什特和珺吉薇爾那場長達120頁的性愛他寫了整整兩年,幾乎每天寫,每天改。他也承認,在那樣一個一本正經的地方讀這樣一個情節,確實有點離經叛道。「不過,文字本身是無辜的」他解釋說,「當我在寫這個做愛的情節時心想,在大詩人奧朗尼當過秘書長的科學院裡讀這段文字,肯定不會有問題。後來我在讀的時候發現,並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受不了那個大聲朗讀的自己,聽眾們則受不了我。一片死寂。陽光投射進來,沒燒暖氣。但最後我還是我,這是我的作品。」
現在,讀者現在手裡捧的就是這本書,這本書的第一部,相信你們也會讀得心驚肉跳,膛目結舌。納道詩將帶著你們進入一座座身體的殿堂,進入人與人之間迷宮一般的複雜關係,進入20世紀最黑暗的記憶。
平行線的隱祕交叉
納道詩.彼得,是匈牙利當代作家、劇作家、散文家和攝影家,1942年10月14日出生在布達佩斯一個中產階級的猶太家庭,父親納道詩.拉斯洛(Nádas László)是電話技術員,母親塔烏貝爾.克拉拉(Tauber Klára)是一位工廠女工。
1944年3月,匈牙利的納粹黨「箭十字黨」掌權後,積極配合德國人加快了對本國猶太人的迫害。納道詩•拉斯洛和幾位親友一起躲在多瑙河邊一個用磚封死的地窖裡印刷傳單,偽造證件,救了不少的猶太同胞。1944年10月,母親則帶著年僅兩歲的小彼得,憑一份假造的身份證明逃離匈牙利,到塞爾維亞的諾威薩德市躲了兩個月,年底剛剛返家,蘇聯紅軍就包圍了布達佩斯,與德國和匈牙利的守軍展開了血腥的圍城戰。戰役期間,小彼得跟母親一起躲到一位親戚家,那裡還藏有別的幾個憑假證件僥倖逃過納粹獵捕的猶太孩子。一枚炸彈擊中了他們藏身的樓房……小彼得最初的人生記憶,除了驚懼的面孔,就是恐怖的爆炸聲和發瘋的哭叫。
布達佩斯解放後,一家人搬回了位於波若尼大街的公寓。在《平行故事》中,作者將精神分析師塞姆澤夫人的家就設在了那條大街上,那裡也是前面提到的那120頁性愛描寫的事發現場。小說裡,塞姆澤夫人是布達佩斯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師,她的職業角色是個觀察者,而她本人也是內心埋著恐怖記憶的大屠殺倖存者,她從波若尼大街那套舊公寓裡觀察別人,也觀察自己。我想這個角色上,曾熱衷於佛洛德和榮格理論的作者勢必投上了自己的影子。
二戰結束後,父親當上了維修工廠局的總工程師;母親參政,任匈牙利婦女民主聯合會布達佩斯委員會秘書長。1948年,小彼得的弟弟出生,父母為新生兒安排了基督教洗禮,想放棄猶太教以更匈牙利化的身份開始新生活。同年,小彼得開始讀小學,當上郵政部處級官員的父親在布達山上分到一套大公寓。
好景不長,納道詩家在50年代連遭不幸。先是父親被人指控盜用公款,雖因證據不足沒被判刑,但還是受到了降級處理,隨後母親于55年病逝。同年,小彼得染上了腦膜炎,搶救了一年才保住性命。1956年,14歲的小彼得進入一家化學技術中專讀書。同年10月,匈牙利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人民起義,首都陷入了無政府狀態,納道詩•拉斯洛被臨時成立的工人委員會毫無道理地開除公職,並接連接到威脅他們的匿名電話,於是,男人帶著兒子們逃離布達山上的公寓,重又搬回到波若尼大街的舊房子。《平行故事》裡有一個類似的細節,塞姆澤夫人在歐爾班山上別墅先被收為國有,後被高官佔有,於是搬回到了波若尼大街。1958年4月15日,就在終於接到能證明自己清白的法院判決書的幾天之後,男人看破紅塵,丟下兩個未成年的兒子絕望地自殺。
成了孤兒的小彼得兄弟被送到一個親戚家寄養,住在當時列寧環路邊上一套公寓裡。在《平行故事》第一部的「大公寓」中,作者在花了整整一個章描寫的那幢由建築師德曼.紹穆設計建造、「能望到朦朧、灰暗的奧克托宮」、「 有著八十年歷史、中規中矩、比例協調的公寓樓」就坐落在這裡。當年叫列寧環路,現在叫泰蕾西婭環路。
書名叫《平行故事》,想來作家是想寫一系列平行發生、互無關聯的故事。事實上,「在這些錯綜複雜、藤蔓叢生的故事裡,存在著一些能將在相同的時間和相同的地點(另一個身體在情感裡)、在相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另一個身體在欲望裡)、在相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時間(公寓、建築、城市的記憶在身體裡)發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各種事件,以及在不同的地點和時間裡(自己的身體在記憶裡)發生在同一個人物身上的各種事件聯繫到一起的交叉樞紐。」這本書的編輯在簡介中寫道。對照作者生平,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平行線與他自身生活軌跡的隱祕交叉。可見,要想讀懂這部書,我們還要瞭解許多,關於作者,關於人性,關於20世紀歐洲的歷史。
謹慎而禮貌地保持距離
父親的自殺,給納道詩•彼得的青少年時代罩上了陰鬱的黑影,這殘酷的陰影隨時間沉積,慢慢成為作家思考的底色和出發點。就在父親離去的那年夏天,16歲的納道詩放棄了讀了一半的化學專業,改學攝影,他對人類複雜莫測、並不非黑即白的內心世界產生了興趣,他想通過感知和光影接近它,記錄它,再現它。從那之後,光影始終伴隨他的寫作。
1961年,19歲的納道詩通過了攝影專業考試,到《婦女雜誌》社當攝影記者。在那裡,他結識了比他年長幾歲的女記者紹拉蒙.瑪格達(Salamon Magda),1962年3月兩人開始同居,納道詩開始寫他的處女作《聖經》,那本書在當年耶誕節的第二天收筆。從那之後,瑪格達成了他文學生涯的見證人,他倆在相知相伴三十年後於1990年結婚,住在一個叫貢博塞格(Gombosszeg)的小村莊裡,全村人口只有40幾位村民,他住在那裡是為了能夠不受干擾地思想,寫作。所有讀他作品的人,都或多或少對他的隱私感興趣,一個什麼樣的作家能寫出這樣沉重、灰暗、另類的書?但他始終謹慎而禮貌地與人群和社會保持著距離,保持著神祕。
處女作《聖經》1967年才出版,在這期間,納道詩在布達佩斯的記者學校讀了兩年書,隨後服了兩年兵役,復員後在《佩斯週報》當記者。他曾兩次到夜校不讀高中,但兩次都中途放棄了。1965,他曾到馬列主義夜大讀了兩年哲學,但是沒參加畢業考試。他越來越意識到,他想學的東西只能從生活中感悟,文憑對他毫沒價值。
1968年夏天,納道詩搬到田園牧歌般的基什歐羅希(Kisoroszi),那是一個只有幾百人的小村莊,他辭掉記者工作,開始閉門寫書。1972年,他寫完了《一個家族故事的結束》,這本書到1977年才跟讀者見面。在這期間,他曾兩度去東柏林留學,從那之後他與德國結下了不解之緣,創作上也受到德語文學的深刻影響。前不久,我見到《平行故事》的德文版翻譯克裡斯汀娜.維拉格,她說她翻譯納道詩的書時並無障礙,因為跟德語文學的關係太密切了,有時她甚至感覺納道詩的寫作是用德語思維。
長篇小說《一個家族故事的結束》是納道詩的成名作,從一個10歲孩子的視角,觀察並講述了一個傳統家族的矛盾和破敗,無論從小說對時間的處理、敘事的技巧,還是以父子關係為核心的家族小說題材來看,都不虧為匈牙利當代文學的里程碑,奠定了作者的文學地位。近三十年來,它是被譯成語種最多的匈牙利小說之一。
迫于生計,納道詩從1974年開始在一本教育雜誌《我們的孩子們》當過幾年編輯,他在基什歐羅希買了一塊不大的葡萄園,自己動手蓋了一間12平米的小木屋,遠避塵囂,埋頭寫作。那12平米的狹小空間,仿佛是他審視世界的瞭望台,他在那裡觀察世界,也觀察自己。1978年,他獲得弗什特.米蘭文學獎金,之後再度辭掉工作,專心創作,並跟戀人紹拉蒙.瑪格達搬進布達佩斯塔爾諾克大街內的一套公寓裡。
1980年,他創作的話劇《掃除》公演,頗為成功;同年獲得米凱什•凱萊曼獎。1981年,他獲得為時一年的DAAD獎學金,這次他去了西柏林,全力以赴地寫那部已經動筆七年了的《回憶之書》。
……但他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據納道詩說,《回憶之書》他寫過兩稿,第一稿於1973年夏天動筆,一年後自己銷毀,幾個月後開始寫第二稿,那才是我們現在能讀到的這本。
1982年,納道詩從西柏林回來後,又回基什歐羅希的小木屋裡閉門筆耕;1983年,他賣掉基什歐羅希的房子,搬到了一個更偏僻的小村莊――貢博塞格,繼續寫那部長達千頁、分上下兩部的《回憶之書》,1985年最終完稿。這期間,他還寫了一本散文集《回家》。1985年,納道詩獲得尤若夫•阿蒂拉文學獎,次年獲得厄爾萊伊文學獎和年度圖書獎金。
《回憶之書》前後花了作者12年的光陰,書的題頁上了印了《約翰福音》裡的一句話:「但他(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他在這部書裡,將肉體、性與身分是被作者置於顯微鏡下,把世界描繪成一個讓人類身體相互連接的一個龐大而精密的複雜體系。想來,社會之所以可以對人們身體間的關係發生影響,因為身體就跟社會一樣,本身也是作為關係呈現的。
《回憶之書》問世後好評如潮,無論評論圈,還是讀者圈,都公認他是最具原創性、思想性和現代性的作家,甚至有人將他比作普魯斯特。在這部作品裡,納道詩將身體文學上升到了哲學層面,所有讀過它的人都會感到內心的震撼。正如匈牙利評論家考爾瑪•梅琳達所說:「這部書不僅保存了我們意識中超乎尋常的批評性和諷刺性,也將我們對隱于現實背後的存在預感的渴望進行了編輯。因此,留給我們能做的只是,一方面看到徹底同一的不可能性,另一方能在我們身上尋找能將我們朝著較為徹底同一的方向引領的形式。」
1987年2月的第一天到1988年2月的最後一天,他寫了一本《年誌-1987》,記錄了只有44位元村民的貢博塞格風景和他日日夜夜的所思所想,記錄了自己身與心的對話,記錄了那些看似什麼都沒有發生、但又確實發生了的事。
納道詩在書裡這樣寫道:「還沒有發生的事情,儘管從理論上來說可能發生,但不一定像某種可能發生的『該發生而沒發生的事』一樣地發生,想來其結果也可能跟所有那些正發生著的事情一樣同樣地明確、致命或影響深遠。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這個問題也不會引起我思考。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有什麼事情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那麼這意味著,『該發生而沒發生的事』發生了。或者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從事物的那個方面想:當我們感覺現在我們身上發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只是我們不瞭解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恰恰現在發生?為什麼沒發生在別人身上,為什麼偏偏在我身上?這時候,或許我們會置身於這樣事件的影響之下,我們既不瞭解事件中的那些角色,也不瞭解操縱他們的那些力量,然而這些陌生的力量使我們在體內感到它們的影響,也就是說,感覺到發生。」總之,《年誌》一部寫真的隨想錄。
1988年,納道詩獲得了戴利文學獎。1989年4月末,他和瑞典好友理查.施瓦茨(Richard Swartz)一起終於實現了他倆計畫已久的事,一連四天坐在答錄機旁用德語敞心長談,談文化,談災難,談混亂,談內心的法則。隨後,他根據這次談話寫了一本《對話-1989年裡的四天》於1992年出版。
1989年,他應青民盟的邀請為年輕人做了一次題為《關於天上的愛與地上的愛》的講演,談論了情愛與性愛、納西瑟斯的自戀與柏拉圖的精神之戀,之後他擴展了講演的話題,1991年以散文集出版。
東歐劇變後,納道詩曾在文學期刊《匈牙利日記》工作了兩年。1990年,納道詩獲得克魯迪文學獎,這兩年他頻繁往返于布達佩斯和柏林之間,親自參與了《回憶之書》的德文翻譯工作,這部書的德語版於1991年底問世,為他的作品走向世界鋪架了橋樑。
讓我們記起死亡的孤獨
1991年納道詩•彼得獲得奧地利頒發的歐洲文學獎。1992年,匈牙利政府向他頒發了最高國家獎――科舒特獎。1993年3月,他被選為塞切尼文學藝術學院院士,一個月後因突發心梗入院急救,正因如此,他的院士就職典禮因故推遲。正因推遲得太久,才有了開頭講述的那一幕。試想,如果在舉行兩年,他至少還沒寫那120頁。
早就知道納道詩跟艾斯特哈茲一樣,都是出色的朗讀高手,幾天前我還參加過他的一場讀書會,朗讀他正寫的回憶錄。納道詩喜歡站著讀,一讀就是半個小時,甚至一個小時,比話劇演員還要敬業,迅速均勻,不打磕巴,由於離閱讀燈近,烤久了會熱,他偶爾掏出白手帕拭一下額頭,為了不中斷閱讀,連備好的水都很少喝。他說,他的閱讀本領是在德國練出來的,德國讀者很喜歡參加朗讀會,許多朗讀會是買票進的,感覺是看一幕獨角話劇。德國人對文學的熱衷是其他民族不能比的,這話我從凱爾泰斯嘴裡也聽到過,凱爾泰斯的原話是:「最好的讀者在德國。」
當然,這話也不是那麼絕對,別的地方也有熱情讀者。有一次跟納道詩一起吃飯,聽他講了一個比就職演說更有趣的經歷:有一次,他應邀去諾維薩德開朗讀會,他讀了當時正在寫的《回憶之書》中的一個章節,「我們坐在上帝的掌心」,裡面也有一段細膩入微的性愛描述。他攤開手稿剛開始朗讀,從外面進來一隊匈族女子學校的女學生……原來,諾維薩德是塞爾維亞境內的匈族區,只要有匈牙利作家來,匈族學校的老師們都會帶著孩子們前去參加,不僅當成學語言的機會,而且為培養民族性。總之,來了幾十位女學生;納道詩感到不妥,但已沒有選擇,因為手頭只帶了這一疊書稿,只好硬著頭皮念下去……事後講起這件事,納道詩說,尷尬雖尷尬,但不是他的錯,他的讀書會是給讀他書的讀者開的,老師在帶學生參加之前,應該知道來的是什麼樣的作家。這就是納道詩,活得很真,很自我,通情達理,但有藝術原則。事實上,他不僅活得很真,死也很真。
就在他心梗發作後的一年半中,他在幾家醫院間輾轉,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出院之後,作家回到自己的桃花源,又一頭埋進書稿裡,全力以赴地寫他早從1985年就開始動筆的鴻篇巨著《平行故事》,現在我們讀到的開篇故事,就是這一年加上去的。
90年代是納道詩•彼得的創作高峰。在這十年裡,他總共出版了10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散文集、戲劇集、文學評論集。1995年,納道詩•彼得在德國萊比錫國際書展上獲得圖書大獎。1998年獲得斯洛維尼亞作協頒發的文學獎;同年,《回憶之書》法文版獲得了法國最佳翻譯圖書獎。1999年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德國出版社推出他八卷的自選作品集。2001年榮獲索羅斯大獎。2002年,納道詩•彼得60歲生日,匈牙利和德國分別舉辦文學論壇為他祝壽。2003年,他赴布拉格領取了卡夫卡獎。2004年,納道詩出版了一本特別的書,題目叫《自己的死亡》。
「醒後我就覺得,身上有什麼不舒服,但我在城裡有許多事要辦,我進了城。那些天,天氣毫無過度地熱了起來,夏天突然到了。」這是書裡的第一句話。
「很長時間我都不敢出家門,因為要想嚴肅正視事物的現實存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我要妻子買十隻衣架,要她挑最好的、最好看的、最貴的買,然後送到醫院,找那個大個子女人。至少他們不用再找衣架了。」這是結尾的最後一句。
在這兩句話中間,作者用287頁的篇幅、配了自己163幅攝影作品。這本書的創作靈感,一是來自他連續一年每天為自家院裡的一株老梨樹拍下的照片,二是在93年他從臨床死亡島復蘇之間的三分半鐘,他在書裡記錄了那三分半鐘和前後發生的事,平和,客觀,真實,在書裡,作者試圖戰勝死亡的恐懼。我很喜歡瑞典日報一篇書評的題目――〈納道詩讓我們記起死亡的孤獨〉。
巨大失敗還是巨大成功
納道詩前後寫了18年的《平行故事》,終於在2005年出版了,厚厚三部,總共長達1500頁。第一部《喑啞地帶》,第二部《黑夜深處》,第三部《自由呼吸》,總共又分了39章,每章都有分別的標題,其中有幾章相對獨立,可以當成短篇來讀。小說裡包含了許多個線索不同、錯綜複雜、發行發展、交叉敘述的故事,故事發生的時間主要從一戰講到東歐劇變(1914-1989年),幾乎橫跨了整個20世紀。故事發生的地點也十分複雜,涉及到匈牙利的布達佩斯、莫哈奇和陶希托特村,德國的柏林、柏林的魔鬼湖、杜塞爾多夫、臨近捷克邊境的安娜伯格和一個編造出的城市――普斐蘭,另外還有些情節發生在荷蘭,小說提到的歐洲城市更是難以盡數。小說裡不同的故事並沒有分開,而是穿插到一起,發生不同時空的不同故事,並非按時間順序或情節關聯相互網織,有的情節隔了許多章才繼續講述,有的根本就無始無終,有的兩個不同時空的故事在一個章節並行發展。另外,諸多故事的主題也截然不同,如果細分的話,還可以細分為家族小說、成長小說、犯罪小說、推理小說、歷史小說、愛情小說、心理小說……因此,書的內容很難用三言兩語簡單概括。
總之,作者把彼此獨立、互無關聯的許多故事以超出想像的方式串聯到一起,這種串聯是任何現實主義的文學手段都無法達到的。書中的人物多得難以計數,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命運,每個人的身體裡都載負著不同的記憶,沒人間的關係夠通過身體展現,又遠遠不止於身體,如果非要用一句話概括的話,我會選匈文版簡介中的一句:「小說講述了人們肉體的相互影響、相互誘惑、相互渴望和相互珍存記憶的宏大故事。」
《平行故事》在匈牙利出版後,讓所有人都膛目結舌,不僅是讀者,評論家也一樣。有人抱怨根本就沒法讀,數以百計的人物和縱橫百年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有頭無尾,有的無頭無尾;有人被大尺度、大篇幅、驚人細膩、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情色描寫驚得咋舌;有人連讀幾遍,拍案叫絕,認為這是作者寫作生涯的最高峰,是關於20世紀的史詩性小說。當地評論界也分裂成兩派,老牌文史學家、評論家瑪律古奇•伊什特萬毫不掩飾內心的激憤,他宣稱「這部小說是一個失敗,一位大作家的巨大失敗」;著名詩人、評論家楚爾達什•伽博爾則不吝褒辭,稱《平行故事》是「世界文學的傑作」。
不管別人怎麼爭論,他就像從科學院大禮堂的講演台走下來時那樣,「但最後我還是我,這是我的作品。」他回到貢博塞格的家中,對著窗外那株老梨樹,繼續寫他的書,獲他的獎。2006年他獲得馬婁伊•山多爾文學獎和帕拉斯文學獎,被選為柏林藝術學院院士,還出了一本名為《六國日記》的散文集。
《平行故事》問世後的近十年來,先後被翻譯成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挪威語、斯洛伐克語、羅馬尼亞語、塞爾維亞語、斯洛維尼亞語等十幾個語言。美國作家亞當•蘭格在《紐約時報》撰文說:「這部帶有巨大的野心、令人驚歎地別出心裁、經常稠密得讓人發瘋的小說故意模糊掉歷史、地理、文學和結構的邊界。《平行故事》並沒有真地試圖講述這些故事之間如何互動。它們時而聚斂,時而發散,時而重疊,時而交錯,時而迴圈或返回到彼此,使之成為一部具有挑戰性的非線性小說,這部書試圖完成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即重現20世紀匈牙利人四分五裂、高壓之下的生活體驗。」
蘭格認為,納道詩•彼得是當代文學的超級明星,可跟托爾斯泰、湯瑪斯•曼和普魯斯特相提並論,從風格上看,他的小說則跟阿蘭.羅伯-格裡耶、安東尼.伯吉斯有相近之處。
現在看來,這部小說不僅不是「巨大失敗」,而是巨大成功,國外的評論幾乎全是一邊倒地盛讚,認為《平行故事》是國際文學迦南的重要作品。先有《回憶之書》,又有《平行故事》,更讓納道詩在近十年來,每年都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選人物。
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小說
2014年初夏,當我跟納道詩先生取得了聯繫,告訴他我開始翻譯《平行故事》。老人高興地問我:我在哪裡翻譯?在匈牙利,還是在中國?因為據他所知,韓語、丹麥語、土耳其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的翻譯們也在同時翻譯這本書,他說有這麼多的陌生人在世界各地用不同的語言為他的同一本書工作,這對他來說是一種「既奇妙又可怕的感受」,加上已經出版的外文版的翻譯,足以組成一個大家庭了。他邀請我去貢博塞格,並說很希望能有機會將大家聚在一起見一個面。隨後,我們開始了郵件往來,他對我翻譯中提出的問題一一耐心解答。沒想到,納道詩的這個心願很快得以實現。
9月28-29日,在匈牙利翻譯之家負責人、詩人兼翻譯家拉茨.彼得(Rácz Péter)的籌畫和組織下,在巴拉頓湖畔的巴拉頓弗萊德市專為《平行故事》組織了一次國際翻譯研討會,十幾位譯者從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起,對翻譯這部書時遇到的問題和作為譯者對這部書的理解進行了探討,我也做了半小時的發言。拉茨先生還請來了多位評論家、心理學家、哲學家就《平行故事》做了專題演講,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聽眾多達上百人,幾乎所有文學媒體都參與了報導。自然,研討會的高潮是納道詩先生出場,他特意從貢博塞格驅車趕來,不僅接受了公開訪談,興致勃勃地朗讀了新作,還跟我們共進晚餐,下榻在同一酒店,就像一個大家庭的家族長,跟我們聊過午夜。要不是大家擔心他的身體,催他休息,他恐怕會跟我們熬到天亮。
對譯者來講,與作者交友至關重要,能在閒談中圍繞作品瞭解許多書頁外的故事,不僅有助於對作品的理解、對語言的把握,而且更容易完成從接近到走進作者的情感過度。想來,譯者要跟作者朝夕相處地共度三年,沒有精神和情感層面的交流是很苦悶的,這也是為什麼喜歡翻譯在世作家小說的原因。每譯一本書,生活中就能多一位敬重的朋友。
在聊天中,納道詩提到,德國出版社曾想納道詩建議做一個能幫助讀者閱讀的人物表,納道詩說,他也想過,但不太可能,有些角色只在某個情節中出現,但也有名有姓有面孔。的確,這本書裡寫了上百個人物,他們之間的關係要比《紅樓夢》裡的還要複雜,如果要做人物譜也不能平面清單,需要做一個類似複雜分子式的立體模型。
我問納道詩,書裡的人物有原型嗎?他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說他為了給這本書收集素材,先後閱讀了200多本匈、德語作品,做了大量筆記,書中的許多人物、地點和歷史事件都不是憑空杜撰的,每個人物都有可信性,但不等於說這是歷史小說。納道詩一再強調,這是虛構作品,不希望讀者對號入座。
關於小說的結構,不少人讀後說「結構混亂」,「弄不清作者想講什麼」。納道詩對此有三種應對策略:一種是對付大眾的,他說「世界本身就混亂不堪,我只是記錄而已」;另一種是對付批評家的,他說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寫一本以無終無果為基本結構特徵的小說」;再有一種則對包括我們譯者在內的理性讀者的交心解釋。他說,他之所以採用這種開放結構,是想藉此展現那些人的故事,那些也許從來都沒有見過面,或僅是泛泛之交或擦肩而過,但還是對另一方的生活產生了影響的人們的故事。他說為了刻畫這樣的關係,需要搭建這樣的「混沌結構」。納道詩還說:「這種隱祕、隱性的關係在封閉的敘述結構中找不到位置。這表明,我不僅只能放棄封閉結構,而且還要回溯到古希臘最本原的混沌說。」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決意寫一部跟十九世紀小說寫作傳統決裂的小說,不是讓讀者被動地聽作者講故事,而是逼著作者去想,去想像。換句話說,讀《平行故事》,比弄清作者想講什麼更重要的,是讀者自己在閱讀的過程中想了什麼,想像到什麼。
1997年,《回憶之書》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後,蘇珊.桑塔格曾稱它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小說」,我想,這句話也可以用在《平行故事》上。實際上,可以把這兩部書看成一部書,與前者相比,後者只是往身體的殿堂裡走得更深。
凡是讀過它的人……
《平行故事》的德語譯本是2012年出版的,德國人對它的評價極高。著名女評論家伊莉絲.拉迪施說:「當下文學生活中的一部鴻篇巨著。凡是讀過它的人,都不再會是原來的自己。」我很贊同她的觀點,她這話說明瞭這本書的力量。不過,我更樂於換一個角度用另一種說法:「凡是讀過它的人,都會更接近原本的自己。」
翻譯《平行故事》,是一種文學歷險、歷史歷險和心理歷險。在我看來,譯書是讀書的最高境界,譯一本書,等於讀百遍書,並可能成為除作者之外最懂這書的人。《平行故事》裡物眾多,但每個人物都孤獨、絕望,完全沒有快樂的能力。這一點也讓一些習慣看「大團圓」的讀者難以接受,就連身集美學家、哲學家、史學家、評論家于一身拉德諾提.山多爾也忍不住調侃說:「這部小說的世界是如此缺少幽默,納道詩寫它的態度太過正經,有時他的意願變成了幽默。」不過,讓我們回顧一下20世紀的人類史,特別是中東歐歷史,其中該有多少歡樂呢?我曾翻譯過的另一位匈牙利作家、諾獎得主凱爾泰斯有一本文集,書名就是《歐洲的沉重遺產》,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祖國,家鄉,國家,不幸的20世紀〉。從時間上看,納道詩的這部巨著從20世紀初寫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這期間匈牙利經歷了一戰、二戰、冷戰,經歷了納粹大屠殺、布達佩斯圍城戰、1956年革命、蘇聯佔領和高壓專制,這近一個世紀裡,哪代人的成長是健康的?哪個人心裡沒有陰影?
身體文學是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納道詩對性愛的狂熱和虔誠,讓人相信他從中看到了一個有神的宇宙。讀他描寫的情色場面,就像讓《撒旦的探戈》的導演、以長鏡頭著稱的塔爾.貝拉來拍《情人》中的一場床戲,長得令人瘋,細得讓人狂。然而,納道詩寫身體絕不止於身體,而是我們身體對歷史、家族、經歷和關係的記憶。
總之,《平行故事》是一本絕對好看、但也絕對難讀的小說,需要逐行逐字地讀,需要我們像福爾摩斯一樣將散落在書中的蛛絲馬跡拼接成一條條平行線,需要我們耐心、細心並動用知識和各自身體的經驗尋找平行線的隱祕交叉點。在讀者還沒有讀到第三部的最後一頁的最後一行之前,我不想「劇透」;我寫這篇序,只是想跟讀者聊一下作者和讀這本書的意義,讓大家耐心地閱讀到底,好戲還在後頭,我會在翻譯完第三部《自由呼吸》後再寫一篇〈後記〉,講我知道、悟到的更多祕密……不過,即使您全部讀完了1500頁,仍會覺得作者還有2000頁沒寫,或許正在寫。兩條向無限延伸的平行線,理論上不會交叉,但會在另外的維度裡交叉,也許在書裡,也許在書外。
最後我想再講一句。有一次,納道詩先生在訪談中說,他是柏拉圖主義的孩子,同時也是啟蒙主義的孩子。
余澤民
2014年10月8日,布達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