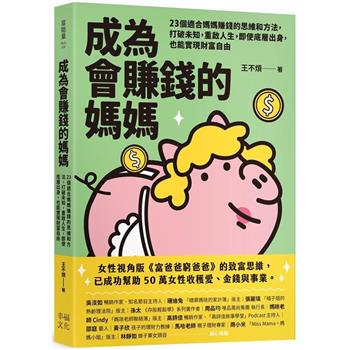本書是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得獎作品之一。作者李佩珊在內地出生和成長,深深影響她的卻是香港的流行文化,例如達明一派的歌、周耀輝的詞、周星馳的電影、李碧華的小說、麥兜的動畫……她在書中以感性的文字,記錄身邊的點點滴滴,有與至親好友的珍貴回憶、對中港台三地流行文化的看法、就讀新聞系的心路歷程和反思,也有對世情人心的觀察。
「一個時代獨有的產物,會為成長於當代的人印刻下獨有的痕跡,微妙地影響他們的一生。
成長於一九九○年代的人,其實也不過趕上了人人純粹地追求音樂、電影、文字與一切美好事物的八○年代的餘韻。達明一派的歌、周耀輝的詞、周星馳的電影、李碧華的小說……建構了一個美好而夢幻的、玫瑰色的時代。
我對那個時代的感覺,正是來自他人的記憶——畢竟二十一世紀初才是我真正身處的時代——因而註定與它隔着一條不可跨越的河流。至今二十年的人生,我缺乏經歷、乏善可陳,唯一擁有的,不過是他人的二手經驗;我的青春,不過是「復刻」的。這些二手的記憶,卻早已成為我成長過程中不可割離的部分。就像親身經歷那個時代的人們一樣,我對它同樣懷着無盡的鄉愁。
但隨着書寫本身,一切慢慢流動。你會看到敍事中分岔的小徑、繁複的枝葉;只是這一切仍舊是鴻蒙初辟之引,也是隨時隨地之在,更遙遙指向一個敍事的終點。而你,或許也已在每一頁存在。」
本書特色
三聯書店今年再度與新鴻基地產攜手舉辦「年輕作家創作比賽」,請來兩岸四地十位星級評審為年輕人作出一對一指導,協助有志者實現出書夢。兩年一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今年已來到第五屆,更首次將範圍擴大至台灣和澳門。優勝作品將出版成繁體及簡體版書,於香港、澳門、台灣及內地發行。
今屆的主題為「發現」,評審包括來自香港的朱力行、黃修平、廖偉棠;內地的毛尖、田沁鑫、鄧康延;澳門的李峻一,以及台灣的張艾嘉、黃子欽、鄒駿昇。
經過一年時間選拔及指導之後,8位作家的著作終於誕生。
另一種表達──西方圖像中的中國記憶
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我的復刻青春
疾病王國中的身體生活
世界已經變了
七年
飛魚神的信差
阿怪
人間等活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我的復刻青春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我的復刻青春
內容簡介
目錄
序一
序二
前言 狐狸、刺蝟和蛋
第一章 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
我的「復刻」青春
從周耀輝,到……
人和時代的纏綿
第二章 前中後書
前書 比我們還年輕的祖輩
中上書 骨頭的顏色
中下書 表哥
後上書 你看,那個人好像一條狗
後中書 同輩:一封信
後下書 你的歌聲將會動人,我的青春也將重生
第三章 玫瑰色的你
玫瑰色的你
做偶像
黑暗之光
慘綠青年、新聞公正和新聞理想
馬昌博:談技術的「死文科生」
第四章 年少輕狂,幸福時光
年少輕狂,幸福時光
不拋棄,不放棄
惡的善良人
KTV,與社交場域
Pop Song,與情感教育
像黃偉文一樣真
偉文,與偉文
第五章 想像兩地
香港篇(一) 從麥兜,看「我城」
香港篇(二) 從安妮寶貝,到黃碧雲
香港篇(三) 紅磡:九四,○四
香港篇(四) 奇情寫人心
台灣篇(一) 小清新之島
台灣篇(二) 紙上窺前身
後記
序二
前言 狐狸、刺蝟和蛋
第一章 那個下午你在舊居燒信
我的「復刻」青春
從周耀輝,到……
人和時代的纏綿
第二章 前中後書
前書 比我們還年輕的祖輩
中上書 骨頭的顏色
中下書 表哥
後上書 你看,那個人好像一條狗
後中書 同輩:一封信
後下書 你的歌聲將會動人,我的青春也將重生
第三章 玫瑰色的你
玫瑰色的你
做偶像
黑暗之光
慘綠青年、新聞公正和新聞理想
馬昌博:談技術的「死文科生」
第四章 年少輕狂,幸福時光
年少輕狂,幸福時光
不拋棄,不放棄
惡的善良人
KTV,與社交場域
Pop Song,與情感教育
像黃偉文一樣真
偉文,與偉文
第五章 想像兩地
香港篇(一) 從麥兜,看「我城」
香港篇(二) 從安妮寶貝,到黃碧雲
香港篇(三) 紅磡:九四,○四
香港篇(四) 奇情寫人心
台灣篇(一) 小清新之島
台灣篇(二) 紙上窺前身
後記
序
前言
狐狸、刺蝟和蛋
「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蝟則知道一件大事。」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刺蝟和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中,引用這句古希臘的詩句,借此來把寫作者分為兩種類型:「刺蝟型」與「狐狸型」。
「刺蝟型」的寫作者,往往目光專注,從一業而終之,長於精深的思索,從而提出原創性的觀點,勾連創建框架,建立新的思想譜系。「狐狸型」的寫作者,往往愛好寬泛,興之所至,筆力所及,留下一連串可以追蹤他思想歷程的足跡,卻每每眼光獨到盡得風流。
「刺蝟」註定是少的,雖在冥冥之中改變了世界,身前身後,也總要承受知音難求、寂寞如許的宿命。「狐狸」註定更受注目和歡迎,也把「刺蝟」艱深的智慧灑向了更多的人,功德無量,卻難免流於散漫,失之厚重。
不論成為「刺蝟」,還是成為「狐狸」,畢竟都需要恆久的修煉。
寫這本東西的我,尚未夠得上資格談論「是刺蝟」還是「是狐狸」。黃渤在電影裡罵得好:「九十後也那麼慫。」到底也不敢自我估量一番,是想成為「狐狸」呢,還是想成為「刺蝟」。
唯一可以自我安慰或者說是自我欺騙的是:我只有二十歲,我還年輕。蛋在孵化之前,沒有人知道裡面或許壓縮塞下了一隻恐龍,還是空空蕩蕩一無所有,所以來日方長。
正如這些年中,與大多數同齡人一樣,以蛋的姿態並列在紅旗下,蜷縮在圓殼中,舒適自得,理直氣壯。
蛋都是橢圓的,就像我們的面目,相近且模糊,帶着同一種的滿足的微笑。我們都是春天的花朵,生長在春天裡,相似和模糊,誰說不是幸福的象徵呢?
幸福者都是怠惰的。破殼而出,太費氣力,也並不能達到世俗意義上的live better。況且,殼是束縛,也是保護。
坦誠地說,直到現在,我仍在我的殼中。或許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有幾個刹那,我曾以為它出現了裂痕,但終究在這與生俱來的殼中,不自知地畫地為牢,受其操控。「人生而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先賢說道。
正如用你所反對的話語體系本身,去攻擊建造在這其上的一切事物,或許是天真,卻難逃愚蠢,掉進了陷阱之中。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時代病,激情萬丈如尼采,大聲宣佈說:「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這句話在不久前流傳一時,但當你在自己身上完全克服了這個時代的時候,你就已經完全殺死了你自己。
而「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不過是偽命題。「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黃子平先生說,歷史並不重複,但總會押韻。
試圖逃離,總歸是無效的。但並不意味着轉而全心全意地擁抱。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之前的世界也並不太好,也總有人抵抗着時代洪流選擇「減熵」 ,也總有人向着山窮水盡柳暗花明處去,他們曾經存在的事實,讓心中的希望不至於幻滅。
現在的世界也並不太壞。在彼此無限接近的灰濛濛的殼之下,總有一些內裡的閃亮,是遮不住的。正如有些鳥,是難以被籠子關住的。
於是在這些文字中,我努力把這些閃亮記錄下來。與其說是我發現了他們,不如說在一片灰暗中,我受到了他們的感召,驅動我把他們載以紙筆。至於這一切對於他人有無意義,其時的我並不在意。
減熵:王小波在《我為甚麼寫作》中介紹,熱力學中有「熵增原理」,指一個孤立系統總是自發地趨向於熵增;引伸到社會學可以理解為:順潮流而動是「熵增」,反其道而行之則是「減熵」。
我們這一代,越來越多的人,生而在水泥森林構築成的城市之中,與之相對應的,是無限接近相似的成長經歷,和統統由幾點一線構成的生活。地域的差異無限縮小,正如那些如同一個模子倒出來的無數個或大或小的城市,現世生活如些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乾癟。而「電視人」不再成為新生事物,大部分人如蜘蛛一樣掛在同一張叫Internet的網上,我們最值得嚴肅討論的生活環境,是曾經最為虛幻,現在卻最為堅實飽滿的「全媒介環境」。
很天真的想法是,作為或許在「全媒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通過自己的書寫,為這個時代,留下些許記憶的註腳。
這些文字的大半部分,試圖按照傳播學的體例排列,從大眾傳播、人際傳播、自我傳播,再到群體傳播,滑稽大過於莊重,雖然本心確實是要依靠其構建起這部書稿的體系,但顯然有些看得出的吃力。大眾文化作為所要說明的「全媒介環境」的生態構成,是一直不變的切入點,我所關心更多卻只是文化現象,一方面是水準所限難以深入;另一方面,比起文本真正所要表達的「內容」來說,陰差陽錯的「現象」,或許是我更感興趣的。
假若理直氣壯一點,把這視為我「發現」的過程的話,在這些文字中我所做的,或許不過是「東張西望,一無所長」,如萬能青年旅店在《十萬嬉皮》中所唱的那樣。唯一值得驕傲的是,或許儘量做到了不虛構現實,也不敵視遠方,也就是說,儘量真誠。
Malingcat老師評論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所定義的今日的「公共知識分子」,說道:「這些人常常非常真誠、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之時,越是真誠,或許越是愚蠢。我所說的每一句,或許也都是錯誤的,而仍有所期望的是,當有人因為一個感興趣的點,偶然翻到這些文字的時候,能在其中發現另一些他本來陌生(甚至抵觸),卻其實能夠從中發現趣味,甚至挖掘出更深意義的點,那麼在這個看似多元實則單向度的、只會越發激化刻板印象和偏見的世界裡,我便做了一點點有意義的事。
不可避免的,還是要談談寫完這些文字之後的事。
書寫的過程,歸根到底,不過仍是抵達自己的過程,這兜兜轉轉繞了一大圈的「發現」的過程,也是如此。
「認識你自己罷」,然而我仍未打定主意、下定決心,是要用餘生努力成為一隻「狐狸」呢,還是一隻「刺蝟」。
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收益,或許同樣是由一些本就感興趣的點,在梳理寫作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了另一些未曾涉足過的點,越發覺得,想要在有生之年,落於紙筆的東西,越來越多,這於我來說,彌足珍貴。
我逐漸由只對歌詞或詞人的喜愛,到不得不開始正視唱片工業的存在。也正如在《紅磡:九四,○四》中初步寫到的,我最希望的是,在我對流行音樂和文化、社會、政治有更全面的認識之後,或許能夠如張鐵志老師的《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時代的噪音》一樣,能夠對尚被文化譜系忽略的二十一世紀的搖滾或是民謠,以及兩岸三地華語音樂之間的相互影響,有所書寫。
「我願意成為一種聲音,對於那些失去聲音的人。」瑪麗‧艾倫‧馬克(Mary Ellen Mark)曾說。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裡,我所希望只是,在所有順風而呼的聲音之外,能作為另一種細微的聲音,雖然註定會淹沒在聲浪裡,但這是我唯一的使命。
狐狸、刺蝟和蛋
「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蝟則知道一件大事。」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刺蝟和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中,引用這句古希臘的詩句,借此來把寫作者分為兩種類型:「刺蝟型」與「狐狸型」。
「刺蝟型」的寫作者,往往目光專注,從一業而終之,長於精深的思索,從而提出原創性的觀點,勾連創建框架,建立新的思想譜系。「狐狸型」的寫作者,往往愛好寬泛,興之所至,筆力所及,留下一連串可以追蹤他思想歷程的足跡,卻每每眼光獨到盡得風流。
「刺蝟」註定是少的,雖在冥冥之中改變了世界,身前身後,也總要承受知音難求、寂寞如許的宿命。「狐狸」註定更受注目和歡迎,也把「刺蝟」艱深的智慧灑向了更多的人,功德無量,卻難免流於散漫,失之厚重。
不論成為「刺蝟」,還是成為「狐狸」,畢竟都需要恆久的修煉。
寫這本東西的我,尚未夠得上資格談論「是刺蝟」還是「是狐狸」。黃渤在電影裡罵得好:「九十後也那麼慫。」到底也不敢自我估量一番,是想成為「狐狸」呢,還是想成為「刺蝟」。
唯一可以自我安慰或者說是自我欺騙的是:我只有二十歲,我還年輕。蛋在孵化之前,沒有人知道裡面或許壓縮塞下了一隻恐龍,還是空空蕩蕩一無所有,所以來日方長。
正如這些年中,與大多數同齡人一樣,以蛋的姿態並列在紅旗下,蜷縮在圓殼中,舒適自得,理直氣壯。
蛋都是橢圓的,就像我們的面目,相近且模糊,帶着同一種的滿足的微笑。我們都是春天的花朵,生長在春天裡,相似和模糊,誰說不是幸福的象徵呢?
幸福者都是怠惰的。破殼而出,太費氣力,也並不能達到世俗意義上的live better。況且,殼是束縛,也是保護。
坦誠地說,直到現在,我仍在我的殼中。或許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有幾個刹那,我曾以為它出現了裂痕,但終究在這與生俱來的殼中,不自知地畫地為牢,受其操控。「人生而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先賢說道。
正如用你所反對的話語體系本身,去攻擊建造在這其上的一切事物,或許是天真,卻難逃愚蠢,掉進了陷阱之中。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時代病,激情萬丈如尼采,大聲宣佈說:「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這句話在不久前流傳一時,但當你在自己身上完全克服了這個時代的時候,你就已經完全殺死了你自己。
而「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不過是偽命題。「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黃子平先生說,歷史並不重複,但總會押韻。
試圖逃離,總歸是無效的。但並不意味着轉而全心全意地擁抱。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之前的世界也並不太好,也總有人抵抗着時代洪流選擇「減熵」 ,也總有人向着山窮水盡柳暗花明處去,他們曾經存在的事實,讓心中的希望不至於幻滅。
現在的世界也並不太壞。在彼此無限接近的灰濛濛的殼之下,總有一些內裡的閃亮,是遮不住的。正如有些鳥,是難以被籠子關住的。
於是在這些文字中,我努力把這些閃亮記錄下來。與其說是我發現了他們,不如說在一片灰暗中,我受到了他們的感召,驅動我把他們載以紙筆。至於這一切對於他人有無意義,其時的我並不在意。
減熵:王小波在《我為甚麼寫作》中介紹,熱力學中有「熵增原理」,指一個孤立系統總是自發地趨向於熵增;引伸到社會學可以理解為:順潮流而動是「熵增」,反其道而行之則是「減熵」。
我們這一代,越來越多的人,生而在水泥森林構築成的城市之中,與之相對應的,是無限接近相似的成長經歷,和統統由幾點一線構成的生活。地域的差異無限縮小,正如那些如同一個模子倒出來的無數個或大或小的城市,現世生活如些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乾癟。而「電視人」不再成為新生事物,大部分人如蜘蛛一樣掛在同一張叫Internet的網上,我們最值得嚴肅討論的生活環境,是曾經最為虛幻,現在卻最為堅實飽滿的「全媒介環境」。
很天真的想法是,作為或許在「全媒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通過自己的書寫,為這個時代,留下些許記憶的註腳。
這些文字的大半部分,試圖按照傳播學的體例排列,從大眾傳播、人際傳播、自我傳播,再到群體傳播,滑稽大過於莊重,雖然本心確實是要依靠其構建起這部書稿的體系,但顯然有些看得出的吃力。大眾文化作為所要說明的「全媒介環境」的生態構成,是一直不變的切入點,我所關心更多卻只是文化現象,一方面是水準所限難以深入;另一方面,比起文本真正所要表達的「內容」來說,陰差陽錯的「現象」,或許是我更感興趣的。
假若理直氣壯一點,把這視為我「發現」的過程的話,在這些文字中我所做的,或許不過是「東張西望,一無所長」,如萬能青年旅店在《十萬嬉皮》中所唱的那樣。唯一值得驕傲的是,或許儘量做到了不虛構現實,也不敵視遠方,也就是說,儘量真誠。
Malingcat老師評論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所定義的今日的「公共知識分子」,說道:「這些人常常非常真誠、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之時,越是真誠,或許越是愚蠢。我所說的每一句,或許也都是錯誤的,而仍有所期望的是,當有人因為一個感興趣的點,偶然翻到這些文字的時候,能在其中發現另一些他本來陌生(甚至抵觸),卻其實能夠從中發現趣味,甚至挖掘出更深意義的點,那麼在這個看似多元實則單向度的、只會越發激化刻板印象和偏見的世界裡,我便做了一點點有意義的事。
不可避免的,還是要談談寫完這些文字之後的事。
書寫的過程,歸根到底,不過仍是抵達自己的過程,這兜兜轉轉繞了一大圈的「發現」的過程,也是如此。
「認識你自己罷」,然而我仍未打定主意、下定決心,是要用餘生努力成為一隻「狐狸」呢,還是一隻「刺蝟」。
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收益,或許同樣是由一些本就感興趣的點,在梳理寫作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了另一些未曾涉足過的點,越發覺得,想要在有生之年,落於紙筆的東西,越來越多,這於我來說,彌足珍貴。
我逐漸由只對歌詞或詞人的喜愛,到不得不開始正視唱片工業的存在。也正如在《紅磡:九四,○四》中初步寫到的,我最希望的是,在我對流行音樂和文化、社會、政治有更全面的認識之後,或許能夠如張鐵志老師的《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時代的噪音》一樣,能夠對尚被文化譜系忽略的二十一世紀的搖滾或是民謠,以及兩岸三地華語音樂之間的相互影響,有所書寫。
「我願意成為一種聲音,對於那些失去聲音的人。」瑪麗‧艾倫‧馬克(Mary Ellen Mark)曾說。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裡,我所希望只是,在所有順風而呼的聲音之外,能作為另一種細微的聲音,雖然註定會淹沒在聲浪裡,但這是我唯一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