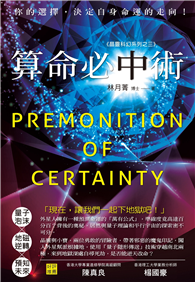在我過去二十多年的人生當中,沒有一件事比患上重症肌無力這罕見病更讓我刻骨銘心。這是一種由神經-肌肉接頭處傳遞功能障礙所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早在兩三百年前,英國已經有該病的確診記錄。但社會普遍對它瞭解較少,當時許多來探病的人甚至誤以為我和霍金一樣成了「 漸凍人」。時至今日,每兩萬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患上這個病。當我從醫生口中得知這些資料,不知可悲還是可笑,只能感歎應該早點買張彩票。
從來沒有認真關注過自己身體的我,只有從患病的一日起,才被一種史無前例的身體變化所震撼。我彷彿進入了新的世界,身邊的人事景物全部發生了變化。我在醫院裡躺了接近兩個月,急症、手術室、重症監護室(以下簡稱ICU)、病房,我在不同的科室流轉,經歷了之前從未經歷的人生。儘管病情幾度危重,但最後還是活了下來。
我的身體在時刻被監控,但我的靈魂還是自由的,也是唯一掌握在我手中的。那時,除了思考,我什麼也做不了。多次徘徊在生死邊緣、旁觀病友的生離死別、情感崩潰,使得我能深切體驗到健康和疾病兩個國度重疊下的陰影與光明。如果用人類學家阿諾德.范.蓋內普(Arnold Van Gennep)1 在進行儀式研究的話語來闡述,生病這段時間,我是處在自己人生當中的分離階段,那麼,在康復的過程中,則是進入了閾限階段,身份不明、界限模糊,在自我與社會的漩渦中掙扎。儘管我從病魔的手中逃脫,但我並未從死亡的意識中轉身。但也正是這種邊緣賦予我特殊的視野,冷靜地觀察自己的身體和疾病,分析社會的身體和苦痛。
蘇珊. 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寫道,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患者除了承受疾病的痛苦,還要蒙受其社會性的隱喻之苦。儘管極為不可能,但她依然竭力提出患者應該極力抵制這些隱喻性的思考。
當疾病加劇了身體與精神的撕裂,在康復中我開始關注身體特別是身體本身具有的性別,不再僅用眼睛關注身體,而是去感受身體傳遞的資訊。我試圖實踐桑塔格的箴言,用「 他者」的角度對身體作一次自省式田野調查:疾病是一種身體和自我世界的雙重失控,除了通過思考直面殘酷的疾病本身,沒有任何消弭本質和現象之分裂的辦法,治癒不是為了重新回歸為原有的自我,而是成為全新的一個。通過走進他者的世界來反思本土文化是人類學研究目的之一,對自身疾病的民族志描寫,也是我反思生命意義的途徑:我的背後拖著長長的陰影是因為我站在陽光之下。
另外一位激發我以身體作為田野點,最終寫下這部由疾病所引發的思考之自傳民族志(auto-ethnography) 的是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墨菲(Robert F. Murphy)。墨菲也曾身患一種令四肢麻痹並會逐漸失去知覺的慢性疾病,後來他在自傳式的作品《沉默的身體》(The Body Silent)探討了身體與文化、社會之間的關係。儘管我並無他豐富的閱歷和智識,但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來向內挖掘,發現人生的藏匿之處。
本書內容的時間維度橫跨兩年,主要在醫院中接受治療與後來康復過程中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思考。儘管在接受治療期間需要上呼吸機,不能說話進食,除了手術與休克期間,我的神志一直清醒,故此期間借由對周遭一切的觀察來打發時間,護士、醫生的日常工作,半夜的搶救、病友的故去與親人的低泣,還有植物人的生活,這一切在醫院這個宛如凝固的時空中重複上演。即使我離開了醫院,只要我還是病人的身份,這些場景都不會離我而去。身體,在學術研究領域一直都是關鍵字,也是人類長久以來思考的主體和客體。我自己的學術研究中也一直關注身體這個話題,因而本書中除了討論疾病和身體的關係,也延伸到其他與身體相關的領域。全書以身體和疾病為開篇;第二章開始討論我在患病及治療過程中的一些個人感受;第三章則是我對他人病中的觀察;第四章的討論從身體官能、表象出發,探究隱藏其中的社會隱喻;最後一章將提及技術遇到身體碰撞出的火花,中西醫學、高科技產品等介入是我主要關注的內容。
這些討論並非單一面向,而是各自聯繫,甚至是千絲萬縷的糅合在一起,它們一起共同組成了一個複雜的身體價值有機體系。對於同一個話題,我會從不同的側面進行討論,使得整本書呈現出回文式的樂章。人的思考也不應該是單線的,只有複線甚至多元的思考模式才能更加深入到問題的本質。書中還提及了許多一直影響我的學者,他們的研究橫跨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性別研究以及文學等領域,每次在我苦心思考的時候,他們的思想給我帶來了心靈的震撼,讓我懂得要通過內在發現自己來發現外在的世界。我只是站在巨人們的肩膀上,企圖可以點燃新的光亮,照亮自己,也為他人借一點光。除了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同時還創造了幾段小詩,試圖捕捉一些無來由的思緒。
我因擁有身體而活著,支持著我豐富的意識生活的是另外一番艷麗的潛意識主導的生活風光,正如我無法看見自己的臉,我無法完全自由地用意識來詮釋潛意識埋藏的身體生活,但,我將重新啟動身體的感知,去深入地感受這個世界的變動。生活中真正的修行並非靜坐冥思,而是在無常的人事中篤行有度,隨心所欲不逾矩。
此外,這本書的創作也是我對於書籍、閱讀以及出版的探索和發現。自從古登堡印刷術發明開始,紙張和印刷帶領人類在知識走進高速發展的時代,書籍開啟了人類以視覺為主流的標準化閱讀模式。人類視覺經驗和功能得到強化和延伸,人類社會主流的媒介都是以視覺為主,通過視覺來解讀社會文化,沉浸在視覺盛宴中的人似乎忘記了起讀者對身體的知覺,社會對疾病帶來的文化性問題的關注。對罕見病患者而言,這本書更是一本來自「 同道之人」的共鳴之歌。而作為健康王國中過客,閱讀之後也會有所反省,自身是否也是參與造成疾病隱喻的共謀,是否能明白生命的意義,同時,也對喚起在生活中被麻痹掉的身體感知,重新去思考身體以至於你我的價值。
最後,這本書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新鴻基地產和三聯書店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創作平台,讓我有發聲的機會,還有創作比賽中一眾的評委,感謝你們的青睞并為我的創作提供了寶貴意見,當然不能忘了本書的責任編輯李安女士及其他編輯、設計等人士,如果沒有諸位的幫助和支持,初出茅廬的我要在出版人生的處女作實屬困難,請讀者也不要忘記這些隱藏在書本後默默付出辛勞的專業人士,一本書的出遠比看上去要艱難得多。
最不能忘記的是要感謝病中為我提供過援助及鼓勵的個人與團體,它們是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2012 級人類學碩士班、翻譯系2006 級本科班及廣州市第七中學等的全體同窗師長,還有我曾服務合作過的單位機構,如廣州歌莉婭225、廣東時代美術館、三度文化傳媒、紅專廠、城市畫報、廣東美術館等中的前輩好友,以及其他廣大媒體與社會人士,乃至為我細心治療照料的廣州市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胸外科與神經內科眾醫生護士,請恕不能一一列出。感謝所有為我流過淚水和汗水的人,正是你們,孕育了這本書的創作。
─────
阿諾德.范.蓋內普在作品《過渡禮儀》(The Rites of Passage)中提出「 通過儀式」的概念,並將通過儀式分為分離、閾限(邊緣)和聚合三個階段。其實,人在社會中成長,就是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轉化的過程,比如成年禮、婚禮、葬禮等。這是生命必須經歷的,也是每個個體獲得特殊經驗的重大時刻。
疾病的懲罰
我還記得從醫生口中得知患病的一刻,傷心、難過、恐懼、憤怒、無奈千百種情緒交集在心中,特別是當我問及病因時,醫生只是給我一個「個體生活習慣差異」的答案時,我根本不能接受。「 家裡有人得這病嗎?」
「 沒有。」
「 之前有感染過什麼病毒嗎?」
「 沒有。」
「 平時生活有什麼不良習慣嗎?」
「 ⋯⋯ 沒有吧。病因是什麼呢?」
「 這可說不準了,個體不一樣吧,要有心理準備,需要長期治療的⋯⋯ 這種病想得開才好得快。」
荷馬(Homer)的《伊利亞特》(Iliad)中, 希臘統帥阿伽門農(Agamemnon)搶走阿波羅神(Apollo)的女兒,觸怒了天神。於是阿波羅在希臘軍中降下可怕的瘟疫,吞噬了眾人的生命,以示懲罰。如果疾病的懲罰人,是一種很特別的動物。當身體健康的時候,很少會真正關注身體的存在,似乎它就是每個人理所當然的附屬品,不會跑到別人那兒去。於是,身體也自然而然地隱身在空氣中。但,只要出現疾病並感受到它帶來的痛苦,身體的存在感馬上就會重現了。疾病成了身體唯一的存在處所,只有身體的不在場才意味著健康。如果用人話來說,就是人都是犯賤的,失去過之後才懂得珍惜。看來,疾病,就是最好的修道院,走進去的人都會成為最虔誠的教徒。
當一個人生病了,特別是不能馬上恢復的大病,就會開始為過去揮霍無度的生活懺悔,求神拜佛,天天禱告,痛改前非,拿出所擁有的一切做交易,為的就是換回那個曾經不受重視的身體。我想,聽到這裡,連自己的身體都要冷笑了,誰讓你忽略我,這場病就是對你的懲罰!不錯,正如桑塔格所說,疾病的生物性事實往往隱含著很頑固的道德批判,疾病成了墮落的標誌。但在面對社會的道德價值取捨之前,我們往往首先會受到自我的審判。
說因為希臘統帥一人的過失而禍及全軍,那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又是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罪惡?我只能首先審判過去生活中種種的劣跡:過馬路衝紅燈、坐車不讓座、隨手扔垃圾⋯⋯,以此來合理化疾病的出現,這樣我才能欣然地接受疾病這個懲罰,但是我不能再深入地去挖掘,因為這種非他即我的邏輯本身有致命的錯誤。
疾病,被視為超越生理性的事實,成為了對個人生活的批判。醫生總是把生物性事實和個人意志密切聯繫在一起,也許是為了安慰病人,但「 犯罪-懲罰」的邏輯卻就再次把「 錯誤」歸咎於病人,加重病人的自我愧疚,讓病人深信他們之所以會生病是因為自己,自己才是最該恨的人。
除了恨自己,毫無由頭的疾病不僅意味著受難,同樣意味它對正常生活的中斷。作為一個年輕的女性,研究生即將畢業,看上去擁有的是如此光明的未來,就連我在手術臺上的時候,幾位麻醉師也悄悄在討論,這麼年輕的女孩身上要留著這樣的疤痕,太可憐了。
疾病的懲罰,將人從健康王國放逐到疾病王國的時候,身上就帶著疾病的枷鎖,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識別出來,相對於疼痛的折磨,讓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無期徒刑。它令正常的社交生活戛然而止,它吸引了常人一切的注意力,但不是關於疾病本身。病人很容易會感受到自己和健康人的差異,這種感覺在一次次的身體與自我的割裂中不斷放大。漸漸地,病人就被放逐得越來越遠。
為了避免洩露我是病人的身份,我只有隱瞞,甚至假裝成一個健康的人,我開始切斷社會交際的管道。不再參加聚會,不再出現在任何遇到熟人的活動場合,不再在社交媒體上更新近況,不主動聯繫任何人,不聽電話只回資訊,幾近從集體生活中消失。我把自己的行動空間縮窄到醫院與家的範圍之內,我企圖把自己邊緣化,放在一個絕緣的壓縮空間。身邊沒有人知道我生病,同學、朋友、師長都不知道,這種畫地為牢的生活滋生出的孤獨感讓我接近崩潰。最終,他們在各種媒體上得知我病重的消息時,必定非常驚訝。
躺在病床上,我對於身體失控的事實表現出一種極度的焦慮。儘管我不能說話,轉身也困難,但從來沒有放棄任何一個再次掌握自己身體的機會。我會留意每天吃過的藥物名稱、時間、數量,暗自記下每天打過的各種針劑,頻率、劑量,每天接受過治療的時間、次數。
我的腦袋在清醒地高速運轉,只要護士在護理過程中出現疏漏,我立馬提出抗議。連主治醫生,我也不放過,甚至曾經懷疑他的專業而對治療方案提出異議。所以他曾經對我說過:「 作為一個中大的學生,你的表現非常出色,但作為一名中山醫
(廣州市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簡稱)的病人,你卻表現得非常差勁。」醫生的權威從來不容挑戰,肉隨砧板上,一個合格的病人除了安靜地配合醫生治療似乎別無他法。這就是醫生對一個病人的期待。也許在醫生的眼中,每一個病人都是一個個編號待完成的項目。但對於病人來說,醫生卻是將他們從疾病的泥潭中拉出來的稻草。可惜醫生總是不明白,治病和修理機器是不一樣的。人,不是一架由各種機器部件組成的,只要把壞的部件換掉就能再次運行。人,是有血肉、有情感的哺乳類動物。疾病所褫奪的不只是健康,而是人對身體的自我控制。醫生對病人情緒的忽視、將疾病從身體中抽離出來,只會使得身體走向失控的邊緣。這種失控帶來不信任、懷疑只是放大的副作用。可我也不得不醒悟,大衛.列布雷頓(David Le Breton)2 所說的病人要付出「 活著的代價」。認真扮演作為一個病人的角色,積極與醫生、護士配合,尋求康復。在迷茫中尋求康復的曙光,企圖回歸健康國度的戲碼一再上演,可惜總是缺少大團圓結局。
在這種持續的規訓之中,病人的身體和身份被一次又一次地強化,永遠走在康復的路上,但卻永遠達不到治癒的狀態。每一個病人都是被死神綁架的西西弗斯,為了接受讓死亡在世間消失的懲罰,不得不把身體當成巨石,在從疾病王國的山腳推上健康王國的山頂之際,就會滾回山腳,永無止境的勞動從來沒有成功的一天。
有一天晚上,年輕的護士照例為我做睡前吸痰護理,結束之後她突然正兒八經地對我說:
「 雖然我來了這個科室不是很久,但你是我見過最堅強的病人了,我相信你很快會好起來的。」儘管安慰劑療法從來未得到醫學承認而被視為偽科學,但不得不說,她的安慰劑讓我做了一個好夢。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疾病王國中的身體生活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296 |
社會人文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現代散文 |
$ 342 |
醫病分享 |
$ 342 |
醫療保健 |
$ 342 |
其他類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疾病王國中的身體生活
本書以身體、疾病及社會為主題,從作者身患罕見疾病的經驗出發,記錄了在醫院中接受治療及康復過程中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思考。但,這本書遠遠不止是一個治癒式的勵志故事。而是一次從自我出發發現世界的過程。
作者兼具人類學研究的背景,將身體作為自省式田野調查的對象,以身體與疾病為原點,討論兩者所帶有的生物與社會特性。
此外,還深入身體知覺、器官、性別、死亡、中西醫療、科技等相關問題的討論當中,儼然一曲跳躍又和諧的複調。作者以人類學的洞察直面真實,深刻地指出社會中慣有秩序對病人的種種規訓。這是一個生命體在疾病的陰影之下身體與精神對話以抗擊痛苦之旅,也是一個思考的迷宮,處處都是入口,處處都能帶領讀者走向新的世界。
作者簡介:
鍾玉玲
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碩士。曾於設計雜誌及藝術書籍出版單位、創意機構任職編輯,獨立策展人,業餘參與組織策劃文藝活動,持續關注以藝術實踐為名的自出版活動。現為人類學研究員,受米歇尔•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等思想家影響,以時代變動下的日常生活方式為主要研究方向。作品散見各藝術設計雜誌及出版物。
TOP
作者序
在我過去二十多年的人生當中,沒有一件事比患上重症肌無力這罕見病更讓我刻骨銘心。這是一種由神經-肌肉接頭處傳遞功能障礙所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早在兩三百年前,英國已經有該病的確診記錄。但社會普遍對它瞭解較少,當時許多來探病的人甚至誤以為我和霍金一樣成了「 漸凍人」。時至今日,每兩萬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患上這個病。當我從醫生口中得知這些資料,不知可悲還是可笑,只能感歎應該早點買張彩票。
從來沒有認真關注過自己身體的我,只有從患病的一日起,才被一種史無前例的身體變化所震撼。我彷彿進入了新的世界,身邊的人事景...
從來沒有認真關注過自己身體的我,只有從患病的一日起,才被一種史無前例的身體變化所震撼。我彷彿進入了新的世界,身邊的人事景...
»看全部
TOP
目錄
自序
起
疾病的懲罰
身體的意識
感
感官新世界
頭髮
媽媽的手
疼痛的苦難
衰老與死亡
人
植物人的玻璃眼睛
午夜的大悲咒
手臂上的十字架
女體
思
自我改造
看不見的臉
身體之美
殘肢展覽會
疾病的浪漫化
術
透視身體
超越中與西
真實的人類
起
疾病的懲罰
身體的意識
感
感官新世界
頭髮
媽媽的手
疼痛的苦難
衰老與死亡
人
植物人的玻璃眼睛
午夜的大悲咒
手臂上的十字架
女體
思
自我改造
看不見的臉
身體之美
殘肢展覽會
疾病的浪漫化
術
透視身體
超越中與西
真實的人類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鍾玉玲
- 出版社: 台北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15-08-28 ISBN/ISSN:978986913108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32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