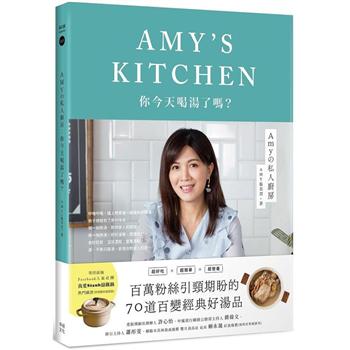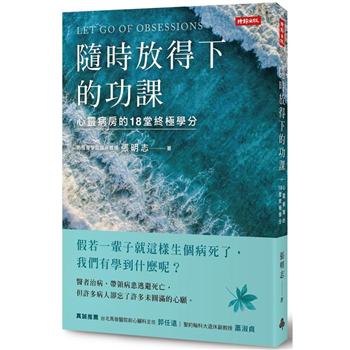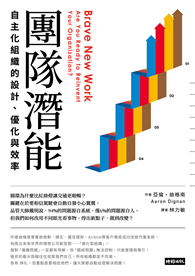圖書名稱: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
讀者們久等了!
2017年,《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初版二刷終於來囉!
本書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作者馬尼尼為的全新文字與版畫創作。作品記錄一場問題重重的異鄉婚姻,與當中的破敗點滴,同時透視初為人母的內心幽微。
《帶著你的雜質發亮》獲選 參加2013. 10 法蘭克福書展、入圍2013開卷好書獎 文學類華文好書。
參考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228000812-260116
對一位女性來說,結婚、生子而後成為母親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嗎?
馬尼尼為說:「我的孩子。我結婚這件事,是擦不乾淨的。這婚姻是一條一條很慢的刮痕,擦不掉的。」
作者新作,接續上本書《帶著你的雜質發亮》,一樣是對自身生命的回望,但主題已由對異鄉婚姻生活,以及對台灣社會現狀種種的無法適應,轉移為一位突然成為母親,而被更深的禁錮在婚姻角色之中的女性。這場婚姻裡,女人不只要面對許多顯性與隱性的暴力,她的時間、精神與力氣也被孩子與家事掠奪殆盡,令人生變得更加空洞。這個「空洞的掠奪」,作者以蒼白的形象加以譬喻,述說著這樣的生命消耗:
一層白。我的人生被敷上一層白。我不知道這淹上來的白還要撐多久。我想停下來。這一層白已經蓋過我了。還有第二層白。第三層白。神給我一個孩子。也給了我白。茂密的白。盎然的白。
相對於他人不假思索,以為理所當然的甜蜜喜悅;結婚、成為人母的生命體驗,對馬尼尼為而言,是痛苦的開端。書寫的內容已不僅是面對新生兒的無奈,更是面對自我生命處境的吶喊,極端誠實地對尚未懂事的孩子述說,全盤寫出她對母親身分的抗拒、愧疚、自我懷疑。
它不是你看見所有理所當然的母愛!
作品,是一位「非良」人母、「非典」女性的真誠告白!
《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一書,同時放入作者大量的「家庭主婦的廢物版畫」創作。這些是作者,除了書寫之外,用以面對生活裡無法逃脫的「白」,她自我疼痛的反芻與救贖。弄點文字吧,印壓一切廢棄與朽壞,成了她生活裡不可或缺的出口,用力刻錄她的生命!
我的孩子,你好好玩耍。不必負責任。
當然會下雨,腳會溼。
當然會有一點疲倦。一點悲哀。
我的孩子,把耳朵臉頰貼到貓的身體上,
用鼻子吸她的毛。
做一個沒有用的人。
**
我找到你。我在你實實在在的肉體上感覺到生命。
找到世界的群鳥。神的寬慰。找到死寂之中令人振奮的氣息。
我找到的這個世界是我一個人的。
非常的自私的世界。
這裡要承受一個人的失落。一個人深切的悲傷。
雖然這裡的愉悅無比的巨大。
我越陷越深。
深到一個神都看不到的世界。
深到沒有人可以靠近我。深到我鄙視性愛與男人。
深到覺得自己一敗塗地。但還是精神奕奕。
有時我對自己說,要接受這雜渣的宿命,這窄迫的家庭。
我知道這長長的毀壞之後,我必定變成另一個人。
這每天的空白使我變老。這以後,我會緩緩地舒展開來,我一定會開出一朵奇麗之花,它的模樣將令你感到不安。
我寫了一張,再一張。一張一張劇烈的空白。
我找到自己的腔調了。花了很長的時間。
母親們都經歷這樣的漂白。這個空洞。每天都被孩子挖出去的空洞。他黏貼在我身上緊緊的空洞。用文字很慢一點一點地掃掉。很慢。我已經寫了很多次這種空白。我的生活沒有了縫隙,全都是一整片被他壓平的白。每天我都奮力地從這片白的大海裡冒出來吸一口氣。
一年了,我帶著你一年了。你黏在我身邊一年了。這一年很長,比小時候家鄉的月亮還老。你成了一個紮紮實實的孩子,我摸得到硬硬的頭顱,柔柔軟刺刺的頭髮,溫熱的臉頰,粗壯的腿,凸出的生殖器。你有時會自己玩了,自己翻書,自己拿起杯子模仿我喝水,亂敲亂打發出各種噪音。會笑得樂不可支。
孩子,我看著那隻貓的時候一定是容光煥發。若沒有她壓進我的皮肉,我一定常常哭。這層毛很適合我。被人兇了,去找她,不用說話。在她身上浪費時間。滾掉時間。我好像是聞這種味道長大的。貓體味。我要在這毛裡居住、散開、鬆掉、打滾、彈跳。這層毛把所有的雜事都吸進去了。我聽見她身體裡的聲音。我喜歡那個縮在裡面別人聽不見的聲音。泡在裡面非常的舒服。她壓平我腦中疲倦的皺褶。壓平肌肉的緊繃。我每天都要聞她睡在那個箱子裡的氣味。拿起她的小手聞她的口水味。這個人類進不去的柔軟世界。我每天都靠掛在這個世界的外面。
孩子你會不會很孤單。我看著你,試著不要去想。我在陽台種更多的樹,澆水,聽鄰居罵孫子,聽水從我的花盆穿過答答地落到樓下的屋頂,聽樓下鄰居罵我把水滴到她的屋頂,孩子在門邊看我。這很多的葉子會撫慰我。有時候會載我一程。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看陽台的葉子。一片一片,張開,再張開。
我的孩子,貓味會讓你的頭腦強壯。這貓是所有人都可以躲藏的地方。是上帝遺留在人間的體味。神留下來的酥軟。你要學她鎮定地看這個慌亂的世界。銀亮亮的安靜。銀亮亮的溫暖。這褐色的孩子,已經長成母親。母親們孩子們都來找她。
我的手變粗。要洗菜洗米切菜。水槽裡的水,穢臭,阻塞,流速極慢。一堆的果皮菜碎。一堆排好洗淨的碗。你要有耐性每天洗碗。那些家事像根棍子打我。沒有整理床上的被單及皺皺的床。我碰不到外面的世界誰也不能碰觸我。地板、衣櫃、桌子。枝幹低懸變成一張牆。寫滿的筆記本。洗襪子的水。洗內褲的水。喝完一碗湯。不夠力氣的生活。
你會站起來迎上我。我要替你擦拭溜溜的口水。你的水果要削皮切片打碎,要一口一口餵。那滿是口水的小手,還要把所有玩具丟滿地。要穿掉很多的衣服,玩掉很多的玩具。濃濃的朝氣,肌膚的味道,緊緊摟著你就可以聞到。這個靈魂,用力滑出這個世界,要用更多倍的力氣去適應這個世界。
我厭倦這種和家庭緊繫的生活。每天這棕橘色的溫柔。神的光,從我指尖流抵心臟,大腦。流抵我的陰影,到那被孩子用穿的乳尖。
人一定是需要這種沒有聲音的陪伴。我要很多很多這種跟貓在一起的空白。荒廢生命的空白。沒有作為的空白。
我的孩子,人到後來都會變得很孤單。
我在學漂浮。在窄小的房子裡漂浮。在孩子的身體裡漂浮。在床墊裡漂浮。
我也在學碎紙。在打結的頭髮裡碎紙。在眼球的淚腺裡碎紙。在孩子的浴盆裡碎紙。
我也在學跑。在咳嗽的時候跑。在硬硬的樹皮上跑。在長長的疤上面跑。
我在學整理。整理惡臭。整理沒有說出來的事。整理壞的生活。好的不需要整理。
我沒有學煮飯。我沒有學煮好吃的東西。我沒有學做好吃的麵包。我沒有學做好吃的餅乾。
我沒有學跟人打招呼。沒有跟人笑。我沒有學穿得很好看。沒有學穿得很性感。
我沒有剪好看的頭髮。我沒有梳頭。
我的孩子。殘渣滋養一切。
我的孩子,我結婚這件事,是擦不乾淨的。
這婚姻是一條一條很慢的刮痕,擦不掉的。
孩子這世界有很多的離棄,很多的菜渣,所有一乾二淨的環境都是一種假象。
外面的世界雖然是明亮的,但不多久黑暗便降落,周而復始,一如人生。
在這裡的沸沸揚揚,我是支吾的。
我躺在有怪味的浴缸,修剪我的頭髮。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陳腔濫調。總之孩子你要原諒我,我沒有辦法在帶著你的時候變得快樂洋溢。我沒有說故事給你聽,沒有歌唱。我聲音很粗,哼不出來,唸不出來。我不知道如何去滋養你,去堆疊濃密的愛。我喜歡泥炭土。喜歡咖啡。喜歡貓毛。
這個時候,你已經紮紮實實地撲到我體內,不管我問題重重。
我無法拔足奔跑,無法逃離這岔出去的路。我已跳入這個被綁緊的世界,這個被冠以母愛的場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要去做一個新的人。要習慣這個世界的煩惱。要給你好的氣息好的營養。要收納所有的不良習慣。要摒除一切負面的情緒。我討厭這種小心翼翼的生活。一種被視為母愛的生活。
這肉身已被你撞上,結實地臌起,你撥動我的體液。我在這裡不斷地沉下,萎縮。腫脹,又浮上來。你蹲在子宮裡浮著,搖搖晃晃地要吞沒我,要我一身狼狽。抓劃著我,勾勒著我的乳房。凌駕一切,攪動我。我的肉體慢慢地被你敞開,穿過去。微弱又有力。擠壓著胃、腸子、膀胱,細軟地變形。你就這樣緊緊地揪著我,一天比一天更強一點。騷動著我,擰著我,揉出臌臌的焦慮。
這羊水撫育出肉的粗壯,還有熱,因為你擠進了我的熱。日正當午的熱焊接在皮上。稀爛的汗珠黏滿頭,若團糾纏的棉線。人被泡得軟軟的,彷彿體內塌了一座水池,精神也長出了更多的毛球,老是失了神。
母親的角色是被冠以燦爛的。我卻覺得自己殘缺不全。孩子正在成形,不能弄壞。他動不動就揮動起來,一開始就尖尖地擠著我。我看見殘餘的自己被抖出來,這陌生的孩子,爬進我的身體裡。身體是緩慢腫脹的顏色,不俐落又多疑又煩躁的柔弱。我攪拌著日夜,胡思亂想黏上我。膚上漸浮出來的黑痣,得一再換洗的內褲。這一切挾帶著朦朧的關於改變的預感,說不上來好壞,像是一樁可有可無、無所期待的喜事。
過了很久。彷彿你在我身上住了很久。那種恍惚的重。我已經過人生半部分可恥的變化。我是壞姿勢的母親。我不敢說愛你,不敢喚你寶貝,我沒有辦法像其他母親一樣;但我也沒有辦法去嫌棄你的一切,沒有辦法置你不理。這隱隱的不安。要斷掉的不安。
那個時候,肌膚下的你一波一波地進到我肉身裡。我找不到你的樣子。我病態地和貓鬼混,用力地摸貓,擠滿了罪惡感。這些年來,我敬重的人群是一群貓。其他人像馬路一樣又黑又粗又硬。所有的事物像去掉了氣味的影像,扁平的,卻遠遠地磨擦著我。孩子你得經過最窄的通道來到這裡,去脫離你的母體,去和所有人一樣攀爬在這裡。你會怪我和其他母親不一樣。
我作了生產的惡夢。我看見胎盘脫落。透明胎盘內的嬰兒對我微笑。拖著臍帶。我驚慌地大叫。姐姐替我把胎盘塞回陰道。惡夢又來了。胎盘又出現在我胯下,陪著傾瀉的羊水,那透明的胎盘令人心驚,我拖著它,放在塑膠袋裡,拎著在胯下,坐進車子到醫院。車子剛開動,帶著下腹的異樣與驚恐醒來,滿頭的汗,腹部繃得緊緊的。
還有一次,我夢見自己生了一個醜怪的女兒,慌亂地沒敢和她相認。還有一次,在夢裡醒來,家裡一整片的泥濘,獨留下一臺冰箱,裡頭的食物不見了,都是泥濘。家裡所有的傢俱也都不見了。泥漿覆蓋了所有的地板。我站著看,雙腳泡在泥裡,空氣中的陽光有霉斑。
書寫沒有減輕任何的病態。這段時間,我還作了很多關於故鄉的夢,中學的老師、同學……一醒來就在記憶模糊的邊緣,彷彿你也在攪動我這個無人知曉的過去,拖長過去的痕跡。我討厭那些舊同學。我討厭那些人的衣著光鮮。我暈頭轉向,穿梭在過去與未來的喋喋不休裡。在故鄉的皺褶裡找到一份還可以辨識的母愛,輕輕刮一刮,有一點渣。我們好似在重覆我和母親的戲分,因此這段回憶才會一再地開始,有時從我母親睡在地板上開始,有時從她騎腳踏車載我開始,載我滑下那長長的斜坡。這樣的夢,以及另外一些不會在你命裡有戲分的人,隱隱約約地滲透在你的體內。
我撫育出一堆舊衣服,一堆一堆的舊衣服。在狗吠不止的夜,生硬地撫摸皮下的你,慢慢搓洗出一片片悲傷的碎屑。我抓住了一些舊的東西。我聞見你嶄新的氣味,你一點一點脫離我的氣味。我們得馬上起程,我甚至還沒從生產的斷層中爬起來。我抱著你,一枚又青又硬的花瓣。我倉皇地站在你的哭聲裡。你的哭聲使勁地敲打我,嘩嘩地洗去我這個踉蹌旅人身上的灰燼,崩裂成群結隊的關於你父親的野蠻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