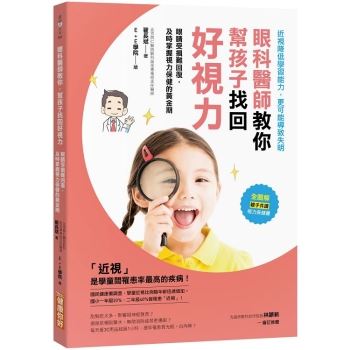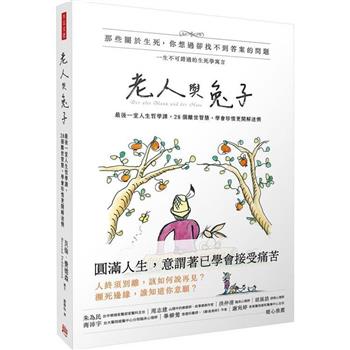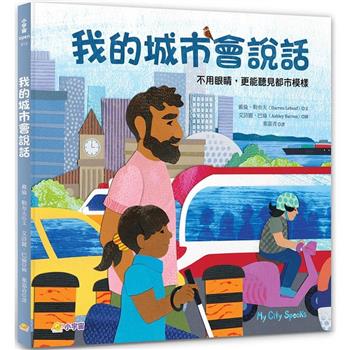前言
概觀
本書的標題 ── 《再多活一天:焦慮與憂鬱症患者的心靈處方》,是我在絞盡腦汁找尋能以一言概括親身經歷、章節標題與附錄的最佳詞句時,腦海裡所浮現的句子。每個人在思考如何以一句話描述自己的人生時,或許都能從中得到些許安慰。若要我選出描述我人生的一句話,那必會是「再多活一天」無疑。這也是為何第一章以此為開頭:選擇再多活一天,讓我熬過深不見底的黑暗時光;看見另一絲希望的微光,讓我能繼續堅持下去。
最近我問一位知名的精神科醫師,焦慮與憂鬱症主要是源於環境的影響,還是生理上化學不平衡所致。他的回答是:「通常兩者兼具。」其他的專家學者則抱持著不同的見解。我相信患者原本在生理上可能有先天與生俱來的傾向,而主要的誘發事件則透露出早已存在的焦慮與憂鬱情緒,進而引發「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發作。雖然誘發事件甚難掌控,但我們可以學習如何採取更好的方式來因應。
不久前與一位朋友促膝長談時,他告訴我:「我不想當我自己了。」在這種「精神痛苦」中掙扎的人往往並不想如此受苦,就像病人不想生病一樣,但這樣的患者常常孤立無援。我誠摯希望本書能為上述患者提供因應技巧,以及精神上的鼓勵。
我從未懷疑過自己在上帝整體計畫中的意義,直到第一次憂鬱症發作。我失去了所有存在的意義,因為意義與外界事物有關,個人與之相比則相對顯得渺小。我開始認為我的生命沒有貢獻,充其量只是白佔土地,由別人取代我的位置一定能有更好的發揮,因此在內心最深處不斷反覆苦思自己存在的意義。一位執教於耶魯大學、才華橫溢的教授曾向我解釋懷疑與信心可以共存,但真正的敵人是不信。在基督徒的存在意義之外,我無法為自己找到更好的活下去的理由。盡管身處懷疑與信心並存的糾葛之中,我依然相信自己在上帝整體計畫中有其意義。
另一個焦慮與憂鬱症患者所必須辛苦面對的困境是表面上喪失潛能。做父母的,眼睜睜看著兒女在人生的黃金時期,不敵這些疾病所帶來的錯綜複雜後遺症,以致於生命的能量被吸乾,不得不重擬計畫與夢想,他們為孩子失去了潛力而憂傷;為焦慮與憂鬱症所苦的成人,則為自己喪失了潛力而感悲痛。回顧焦慮與憂鬱的來時路,我們只看到所失去的一切,而看不見所得的收穫,人生中短短數年寶貴的時光,彷彿就此被這些惱人情緒掠劫一空!經過漫漫的長路,現在我才終於明白:我的價值並不會因為做得較少而有所減損,外在的世界只不過是以與神不同的標準在運行而已。依據表現來計算我們的價值有多少,並非神衡量的方式。對祂而言,我們「是怎樣的人」和「做些什麼」一樣重要,畢竟最終,生命的價值在於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會注意到本書中我提到的「愛心探病餐」。我是在《暗影之聲:在心理疾病中找到希望》(Shadow Voices: Finding Hope in Mental Illness)這部紀錄片裡,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美國國家心理疾病聯盟主席喬依斯.布蘭德(Dr. Joyce Burland)醫師指出:「心理疾病是唯一不會有人帶探病餐來看望你的疾病。」對肉眼看不出來的焦慮與憂鬱疾病,這種形容何其真實!我非常清楚:活著的痛苦甚至可能超過死亡的痛苦,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歷過。所謂的「愛心探病餐」,此概念指的是將烹調好的菜餚,盛裝在有蓋子的烘烤盤裡送到病人面前。沒有比帶食物去給病人更讓他們開心的事了。準備一道「愛心探病餐」、送去給有需要的人,能減輕病人些許的負擔與煩惱。
然而,焦慮與憂鬱的問題在於它們是肉眼看不出來的;我們無法直接指出哪裡生病了,因此,不一定會有人送來「愛心探病餐」。本書裡,我會分享我跟焦慮與憂鬱搏鬥的親身經歷;每日默想就是這段旅程的結晶。在康復過程的數月中,我開始了解健康不代表焦慮就此消失;終其此生,我永遠會經歷比一般人更高程度的焦慮。我的目標不是要消滅焦慮,而是接受焦慮,以及不時出現的情緒波動。如此,出人意外的力量也會隨之而來。
書中默想的部份已經證實能帶來生命。我說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沒錯─一位治療師透露:在一名病患身上使用這本書後,的確救了那個病患的生命。
大眾愈來愈意識到焦慮症的高發病率與毀滅性影響。例如:美國《婦女生活》(Women’s Day)雜誌總編輯珍.查斯納(Jane Chestnut)最近公開坦承自己患有焦慮症,並決心以專文探討,讓心理健康議題的報導成為《婦女生活》雜誌的一個主要使命。
「下次你在超市賣場的結帳處排隊,或卡在車陣中動彈不得時,觀察一下周圍的人。很有可能排在你後面人或他所認識的某個人,正為焦慮與憂鬱所苦。每年都有將近百分之十九的美國成人罹患焦慮症,罹患憂鬱症的比例則是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女性罹患這些疾病的可能性更高達男性的兩倍。」 ──《婦女生活》,二00八年五月六日
在罹患人數如此驚人的情況下,讀者就可分為兩類:焦慮或憂鬱症患者,或是認識的人當中有罹患此症的人。後者包括專業與非專業的協談人員,以及親友。
閱讀本書的收穫
讀者會感受到親身的驗證
讀者會了解他們並非唯一為焦慮與憂鬱所苦的人。讀者會覺得自己「糟透的感覺」有人能真正同理看待。讀者看了本書作者所表達出的想法、感覺與經歷肯定會心有同感。
讀者會感受到適時的安慰
藉由經文閱讀、默想、行動步驟和禱告,讀者將學會辨別並採取行動對抗扭曲的思考模式與感覺,使負面情緒得以舒解。
讀者會經歷到盼望
讀者可以利用以往未曾運用過的資源,透過令人耳目一新的創意手法,戰勝焦慮與憂鬱。每則默想都會激發讀者帶著期待的目光抬頭仰望,不再低頭沉溺於挫折與絕望之中。
我的親身經歷
這是我個人飽受嚴重焦慮與憂鬱症的故事,記錄所經歷的種種苦楚,目的不在於規範或預測他人的狀況。我只是一介典型的普通人,不是什麼特殊人物,但我嘗試藉由分享自己走過憂鬱與焦慮低谷的歷程,向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伸出援手。我深信我並不孤單;事實上,我確定我絕不孤單。
因為可能丟掉工作的恐懼,我一直在絕望中掙扎。被資遣可能導致的後果,在我腦海裡演變成財務危機的最糟情景,面對此一現實,我最擔心的事情與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不時浮現。由於先天基因就有焦慮與憂鬱的傾向;加上工作時經常出差、長時間與親友疏離,導致這些情緒開始惡化。焦慮變得無法掌控;事實上,它已耗弱了我的心神。
即使有些時候我仍可正常生活,但有些時候則嚴重到失能的地步。處理日常事務的能力時好時壞,困擾我到一個程度的是,我的身體因睡眠不足與失去食慾而開始出現筋疲力盡的症狀。清晨早起讓我白天累得要命,專注力降到最低。我沒有跟任何人透露我的情況有多糟;此舉似乎太冒險了,因為我害怕會因此失去工作。二00七年一月時,老闆通知我公司必須評估整體的營運績效,愈發使我被資遣的恐懼感升高。這件事我沒對人提起,也不知往何處求援。
我的母親於同年的二月離世,我的心裡為層層的失落感與迷惘所掩蓋,使我原本已搖搖欲墜的精神狀態更雪上加霜。返回工作崗位所須做的調適,跟目睹母親緩慢痛苦步向死亡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她在與帕金森氏症搏鬥十四年後辭世,離開時並不安詳:她幾乎說不出話,獨力與死神對抗;護理人員有好幾次都認為她的心跳停止了,但實際上,她的心仍然在跳。陪伴在她病床邊的六天裏,我內心沈浸在失業的恐懼中,而眼前所見,更是令人擔憂不已。我母親當時因不能進食,全身已瘦成了皮包骨…
我內在的人生羅盤不再指向北方,情緒開始陷入低潮。三月以前,我開始經歷極度焦慮,發作期幾乎不曾間斷。我對幾位治療師透露實情,請病假成為對話中我想極力避免的話題。我的工作已經岌岌可危;請病假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以下敘述是那年八月前我經歷的情況。
當時我嚇壞了。我無法回到生活的正軌,感覺自己的精神狀態就像一個溜冰的人,跌倒卻爬不起來。身體的感受是全面的恐慌,覺得彷彿有人正往我的靜脈注射劇毒;要命的恐怖感刻骨銘心。悄悄潛入的恐慌加劇,身體和心理的痛苦撕裂了我。真實的事與不真實的事都令我惶恐懼怕;光是要辨別兩者間的不同,我便頭痛欲裂。
☆
外子開車載我前往治療師處接受治療。我最後決定告訴治療師我的感覺有多麼糟,真的再也無法忍受了。我脫口說出充滿絕望的話語,而不論我說什麼,這都是正確的選擇。幾天之內看過數位治療師之後,一位精神科醫師開出一張立即請病假證給我的公司,在那個禮拜還未結束前,公司已簽妥所有相關文件。我不願意面對這一切,也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所以就賴在床上,逃避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覺得空虛又孤單,焦慮感揮之不去,整日與焦慮共舞。縱使偶爾會暫時忘卻焦慮,專注在別的事上,之後又會再回來重拾舞步。這就像在排隊的隊伍中位置不見了,只好重新從最末端再開始排起,但卻老是到不了最前端。這支舞,是我已脫離正常生活和現實的一個比喻。我需要治療──真正的治療。
長達一年多,我都隨身帶著同樣的檔案,裡面包含這一年來、我坎坷生命的相關文件。檔案裡有就醫紀錄、我複印的檔案、治療師手繪的圖表、一份介紹不同抗憂鬱藥與它們對神經傳導物質的選擇性作用的參考資料,以及由湯米.尼爾森牧師(Pastor Tommy Nelson)主講、《今日家庭生活》(Family Life Today)廣播節目的文字稿(第一次廣播名為「墬入黑暗深淵」,在我請病假的三天後──二00七年八月廿七日播出)。
在這段情緒起起伏伏的期間,我在日記中奇蹟似的記錄了一些「保持理智的方法」,而這些原則是讓我得以繼續前進的動力。其中第一篇紀錄「只要再多活一天就好」,就如同「大力水手卜派」般支撐著我;而這些紀錄,後來就集結成現在您手上的這本書。不是每篇文章都在描述痛苦的絕望情緒;在書中,我試著寫下對焦慮與憂鬱症患者有益的事物。只專注在探討我自己的憂鬱症並非本書宗旨。
我對自己筆下文字的感覺是戒慎惶恐的。每篇紀錄都喚起我身心狀態岌岌可危、令人幾近窒息的回憶。雖然我在治療過程中確有進步,但速度就像蝸牛爬行般緩慢。
病假讓我得到立即的緩解;然而,緩解感並未持續太久。請病假畢竟只是一個立即且暫時的解決方法,因為緩解感稍縱即逝。這時,神似乎將縱橫交錯但一致的訊息,分為不同主題向我說話。在開始請病假的第一週,一個朋友在聽說了我的情況之後,付費讓我去參加「信心女性」(Women of Faith)會前工作坊,主題是「神賜給你人生的一個夢」。我虛心的接受邀請,雖然我以前從未參加過「信心女性」特會。
抱持著存疑的態度,我前往參加。然而正跌入情緒深淵的我,跟這場會前工作坊會有何關係?不過,當我坐在本田中心的觀眾席時(譯註:是一座位於美國加州的橘郡安納罕市中心的室內體育館,由日本本田技研工業冠名贊助),我覺得彷彿穿越了時空,像是出了一場可怕的車禍,被飛機載運到醫院一樣。一週前,我還全神貫注在秋季的出差日程和工作職責上,但當我坐在特會中時,這一切都從我腦海中消失,使我整個人處於嚇得呆若木雞的狀態。
坐在兩個朋友中間,我覺得很安全、可以窩著,情緒上沒有任何防衛。我想躲起來,同時又想聽演講的內容。席拉.沃爾許(Sheila Walsh)談到她如何對抗童年時期的痛苦,而亨利.克勞德博士(Henry Cloud)則談到如何重拾個人夢想。我沒有夢想,有的只是惡夢連連。靈魂深處,我知道是神在對我說話。我離應許之地千里之遙,但神對我有個計畫,而這一切始於聽聞這麼多從焦慮與憂鬱症中康復、充滿希望的見證。
會後,我知道我必須正視自己焦慮與憂鬱的問題,但卻不知從何著手。沒有任何相關的指南可以引導我度過這段病假期間,我只能從醫師的建議開始。這使得我很多時間毫無規畫,只能沉溺於絕望當中。
心理諮商協談是醫師的建議之一。但我是帶著混亂的猜想、恐懼、不理性的確信,以及自我的貶抑進入諮商治療的。我的治療師專攻認知治療,但這是一個我完全不熟悉的領域;諮商治療中,我也發現自己的想法有多麼缺乏條理,某些扭曲性想法出現的原因,我根本答不上來。隨著一週的時光過去,上述的情緒只有不斷的增強。
為了穩定我的情緒,醫生也建議我服用抗憂鬱藥、運動並休息。我努力嘗試不同的抗憂鬱藥,有些抗憂鬱藥會讓我感到頭暈或噁心想吐。我設法尋找一個適合我、不會引發不良副作用的藥物處方,也開始加入當地YMCA開設的水中有氧運動長青班。選擇這個班是因為我可以跟得上步調,畢竟我有好多年沒運動了。
有時候,活著就是我唯一成功的事(我會把這些日子稱為「DVD時光」,並將此行為合理化,認為坐著看電影至少會比自找痛苦要好)。我會邀請朋友來跟我一起看影片,如此才不會形單影隻。
在病假結束好幾週之後,發生了一個關鍵性的事件──我得了惱人的流感。這就像我感染了一種致命的病毒,且已餘日無多。我為家人備餐的微薄心願再也無法達成,轉而以速食代替。這時,我拋開所有的壓抑與自尊,打電話給一個向她吐露秘密似乎安全的昔日好友,請她帶探病餐過來看我。我找對人了;接下來兩個月,晚餐都會準時抵達,以充滿藝術美感的方式排列在餐盤上。我會試著先把屋子整理好,然後等著看到她的臉龐和當晚帶給我的「愛心探病餐」。除了感激這些來得及時的餐點,我更感激與她重拾過往友誼,且情誼愈發深厚。
請病假的期間,我一直擔心家裡的財務狀況。這一切會不會危及我的工作?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對財務危機的恐懼一直縈繞於心,而我也從病假惡化到短期的失能狀態。當病情無法以肉眼判讀時,醫生要如何診斷病人?我體內的基因和生物化學機制環環相扣,誘發駭人的焦慮情緒。就像遭到一柄大錘猛然敲中頭部,我在剎那間頓悟到:重返安寧已然是個無法實現的目標。最佳的情況也只會是我的焦慮與憂鬱高於正常值;我會一直感受到某種程度焦慮的情緒。往前看的話,這個「新的正常的自我」不意味著焦慮就此消失,而是意味著儘管在焦慮狀態下,我當學習如何正常生活。這樣的診斷,讓我同時有解脫與被束縛的感覺,因為它不但道出我能接受、自己的確罹病的事實,也說明這種病症,不會完全從我的人生離開。
神啊!我的先天基因如此組成,祢是否參與其中?我會大膽詢問全能的上帝。神啊!我來到世上的過程,祢是否參與其中?神啊!讓我如此成長於母腹,是否是祢的旨意(《詩篇》一三九篇13節)?難道不能有更好的選擇嗎?
回顧過往,神在我踏上焦慮與憂鬱之旅時,使用我身邊的每件事、每個人來幫助我。銘刻在我腦海裡的,是帶「愛心探病餐」來看我的昔日故友提起癌末教授蘭迪.鮑許(Randy Pausch)的那一天,當時夏日炎炎,我們正要過馬路。由他所著的《最後的演講》(Last Lecture),讓我深受啟發。蘭迪書中的字字句句似乎能呼應擁有夢想這個飄忽的主題,且即使我一直惡夢不斷,神安靜的聲音似乎在對我說著夢想和希望並未遠去。我很喜歡蘭迪.鮑許說的這句話:「磚牆存在的目的不是讓我們無法出去,而是要給我們機會看清,自己有多想要那樣東西。換言之,磚牆存在的目的是阻擋那些不夠想要的人。」
這是個多麼反其道而行的想法:阻礙就像一個過濾器。對我而言,這種想法言之有理,也似乎與聖經的思維一致。耶穌時常問那些生病的人是否想得醫治?答案連想都不用想,但真正的問題是:他們有多想得醫治(《馬可福音》十章49-52節)。可能無法康復的想法,讓我甚為苦惱。
我有本日記,上面記錄了我每天的焦慮程度,數值由一到十,一是平和寧靜,十是極度焦慮,我持續記錄了將近九個月。請病假後不久,一個治療師朋友告訴我「憂鬱症」會持續六個月至一年。當時我嚇得倒抽了一口氣,但時間證明他說的千真萬確。我的治療師指出,我所經歷的任何事,在我身上都會是一般人強度的三倍。剛開始時,我作了一些錯誤的決定,我曾有機會被診斷為「長期失能」,可是治療師告訴我,這麼做的病人,也會開始將自己定義為「失能」的狀態。因此那時我跳過這個選項,決定挺身對抗,為我的人生、工作和家人奮力一搏!
我的焦慮浪潮會在一天結束時退去,並在早晨時湧現,想來是其來有自。每天,我必須有意識的對抗自己的焦慮思緒,於是通往辦公室的階梯變得像是通往刑場的路(譯註:在 1935 年美國南方的冷山監獄裡,關的都是等著處死的重刑囚犯。從死囚牢籠到路的盡頭就是電椅,而「Green Mile」就是其間一段約一英哩,鋪著陳舊綠色的油布地氈走道)。一見到我的辦公桌,我整個人神經緊張起來。還記得第一次見到我的辦公室時,曾認為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獨立建築,但如今它卻令我恐慌,而焦慮也開始衝擊我的大腦。腎上腺素不分晝夜在我的體內奔流,就像恐怖份子正在威脅我的生命!
關心我的朋友不斷警告我,說我給自己太多的工作量了。除了他的顧慮之外,外子也定期跟我商討留職停薪的可能性,但堅定的決心和對被資遣的恐懼,讓我勉力持續下去。有時,我能非常順利的完成手邊要做的事,而有時焦慮則會讓我什麼都做不成。我給自己很大的壓力保持「正常」,決心隱藏我的焦慮憂鬱情緒。然而,我好孤單,感到絕望透頂。
在這段期間,向我伸出援手的朋友對我而言意義非凡。她們從以前開始,就一直像是堅固又安全的桶子,在我滲漏的桶子下面承接滴答漏下的水。治療師告訴我,焦慮的人會覺得自己的桶子底部似乎有五個洞,一切不斷的從洞裡滲出。這是我有生以來聽過最真切的描述。上述這些女性友人扮演的便是承接我漏下來的水滴的角色。若讓她們坐在同一個房間裡集思廣益,世上就沒有什麼問題能難倒她們。這些女性友人由於種種不同的原因,成為我生命中的英雄。
我了解為何有人會患上社交恐懼症,因為我曾親身經歷過。當你情緒不堪一擊時,與別人相處就太過冒險。我覺得只要做錯一件小事,或旁邊有人斜眼看我,我便會覺得腿軟。我想在餘生裡都閉門不出,與世隔絕。我不需要,也不想要任何惡名。我想要絕對的孤獨,這對一個平時從旁人身上得到能量的人來說,實在不符常理。
我不敢斷言自己不會復發。但藉由神的恩典,醫師與治療師的協助,以及親友們無條件的愛與支持,我已經找到痊癒之路。我衷心希望與各位分享,在這段焦慮與憂鬱之旅中對我有助益的原則。願神祝福你並保守你!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再多活一天:焦慮與憂鬱症患者的心靈處方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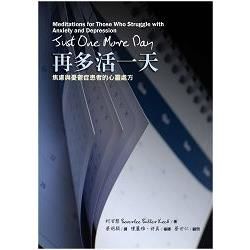 |
再多活一天 作者:(Beverlee Buller Keck) / 譯者:蔡明穎 出版社:舉手網絡 出版日期:2016-05-0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72頁 / 25k正 / 14.8 x 21 x 1.4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2 |
宗教命理 |
二手書 |
$ 234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心靈關懷 |
$ 253 |
心靈勵志故事 |
$ 253 |
📌宗教79折起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輔導諮商 |
$ 288 |
心靈勵志故事 |
$ 288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再多活一天:焦慮與憂鬱症患者的心靈處方
作者於本書中將其與焦慮和憂鬱症親身搏鬥的經歷娓娓道來,讓讀者從四十篇以默想形式撰寫的小品文中獲得新的見解、釋放與希望。每一篇小品文包含一段經文、一段默想,以及一段祈禱文。作者柯百黎希望透過閱讀本書,讀者得以從中獲得「只要再多活一天」的安慰與決心。
作者簡介:
柯百黎在加州的聖華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長大。門諾弟兄會的農夫們在此地辛勤耕耘,將它變為「美國的水果籃」(the fruit basket of the nation)。大學畢業後,她進入學園傳道會服事,在華盛頓大學、北加州及英國等地投入學生事工。後來她認識了德溫,兩人婚後因德溫要在泰博特神學院(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進修神學,所以遷往南加州。結束泰博特的課程後,百黎曾在兩間教會服事,擔任婦女事工部與教會資源事工部總監。這段時期,她也擔任在演藝界發展的女兒茉莉的經紀人,約十年之久。她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金融服務公司擔任教會公關經理。百黎目前與丈夫住在加州橘郡的鄉間小屋,兩人育有一女。百黎喜愛寫作、閱讀、游泳、旅遊,並享受與家人及親友共處的寶貴時光。
譯者簡介:
台大外文系畢,輔大翻譯所中英口譯組碩士,曾於英國留學與工作。喜愛閱讀、旅行、學習新事物,相信友誼與甜點能使人生更美好。
TOP
章節試閱
前言
概觀
本書的標題 ── 《再多活一天:焦慮與憂鬱症患者的心靈處方》,是我在絞盡腦汁找尋能以一言概括親身經歷、章節標題與附錄的最佳詞句時,腦海裡所浮現的句子。每個人在思考如何以一句話描述自己的人生時,或許都能從中得到些許安慰。若要我選出描述我人生的一句話,那必會是「再多活一天」無疑。這也是為何第一章以此為開頭:選擇再多活一天,讓我熬過深不見底的黑暗時光;看見另一絲希望的微光,讓我能繼續堅持下去。
最近我問一位知名的精神科醫師,焦慮與憂鬱症主要是源於環境的影響,還是生理上化學不平衡所致。他的回答是...
概觀
本書的標題 ── 《再多活一天:焦慮與憂鬱症患者的心靈處方》,是我在絞盡腦汁找尋能以一言概括親身經歷、章節標題與附錄的最佳詞句時,腦海裡所浮現的句子。每個人在思考如何以一句話描述自己的人生時,或許都能從中得到些許安慰。若要我選出描述我人生的一句話,那必會是「再多活一天」無疑。這也是為何第一章以此為開頭:選擇再多活一天,讓我熬過深不見底的黑暗時光;看見另一絲希望的微光,讓我能繼續堅持下去。
最近我問一位知名的精神科醫師,焦慮與憂鬱症主要是源於環境的影響,還是生理上化學不平衡所致。他的回答是...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只要再多活一天》的相關評論:
「這是一本親身經歷焦慮與憂鬱症的基督徒所寫的靈修書籍,對那些正為同樣疾病所苦的人,本書可協助他們敞開心胸與人分享痛苦。我誠摯希望本書能有機會接觸到大多數有此需要的讀者。」
--羅納德.卡爾森博士 (RONALD CARLSON, PSY.D)
臨床心理學家
「妳記錄焦慮與憂鬱症的真貌,加上自身的經歷,給予讀者堅不可摧的希望與連結感。妳精采的見解,以及妳個人旅程中所觀察到的細微差別,闡明最私人、同時也是最普遍的事實,對此我十分感謝。相信妳的書會有許多不同年齡的讀者。」
--葛林.麥克萊倫博士 (GLEN...
「這是一本親身經歷焦慮與憂鬱症的基督徒所寫的靈修書籍,對那些正為同樣疾病所苦的人,本書可協助他們敞開心胸與人分享痛苦。我誠摯希望本書能有機會接觸到大多數有此需要的讀者。」
--羅納德.卡爾森博士 (RONALD CARLSON, PSY.D)
臨床心理學家
「妳記錄焦慮與憂鬱症的真貌,加上自身的經歷,給予讀者堅不可摧的希望與連結感。妳精采的見解,以及妳個人旅程中所觀察到的細微差別,闡明最私人、同時也是最普遍的事實,對此我十分感謝。相信妳的書會有許多不同年齡的讀者。」
--葛林.麥克萊倫博士 (GLEN...
»看全部
TOP
目錄
目錄
推薦序:憂傷靈的良藥
前言:概觀
我的親身經歷
第一天:再多等一天
第二天:緊緊抓住
第三天:照顧自己
第四天:未來
第五天:帶著神的形象
第六天:無法可施時,請尋找群體
第七天:日常供應的備用計畫
第八天:認識艾笛
第九天:憤怒
第十天:神差派的同行者
第十一天:向真理看齊
第十二天:覺得受孤立
第十三天:為生活留白
第十四天:羈絆
第十五天:如履薄冰
第十六天:快樂
第十七天:治癒
第十八天:冒險
第十九天:患難之交
第二十天:溺水的救生員
第廿一天:事情不似表面所見
第廿二天:康復是你的工作
第廿三天:我的...
推薦序:憂傷靈的良藥
前言:概觀
我的親身經歷
第一天:再多等一天
第二天:緊緊抓住
第三天:照顧自己
第四天:未來
第五天:帶著神的形象
第六天:無法可施時,請尋找群體
第七天:日常供應的備用計畫
第八天:認識艾笛
第九天:憤怒
第十天:神差派的同行者
第十一天:向真理看齊
第十二天:覺得受孤立
第十三天:為生活留白
第十四天:羈絆
第十五天:如履薄冰
第十六天:快樂
第十七天:治癒
第十八天:冒險
第十九天:患難之交
第二十天:溺水的救生員
第廿一天:事情不似表面所見
第廿二天:康復是你的工作
第廿三天:我的...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柯百黎 譯者: 蔡明穎
- 出版社: 台灣舉手網絡協會 出版日期:2016-05-06 ISBN/ISSN:978986915043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開數:25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高:14mm
- 類別: 中文書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