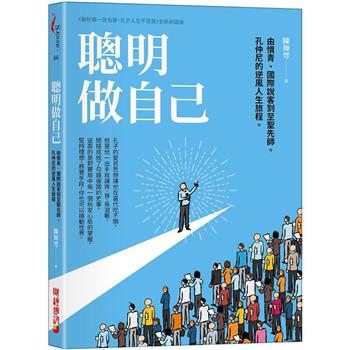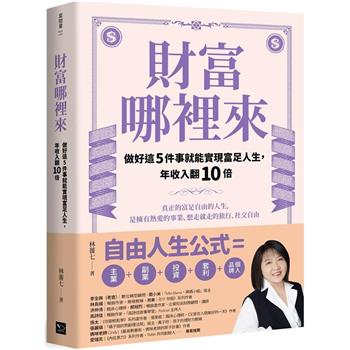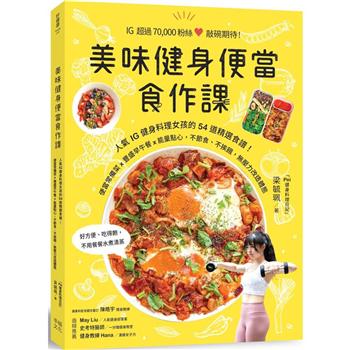★麻辣家族聚會居然是「她」搞的?
★七年級最嗆的華文鬼才代表作!
★亞洲周刊2015年十大小說!(獲選作家包括王定國、王安憶、王良和、劉大任、陳雪、顏歌、葛亮、遲子建、陳冠中、英培安)
★「作為一個作家,靠版稅活著,我覺得需要為我生活的時代留下一個自己的版本。」──顏歌
★2012中國人民雜誌未來大家Top20!
★2013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新人!
★德國出版社超過五位數字歐元搶標!已售出5國國際版權!
你這麼大的人了,還這麼瓜?
我們這一家,不搞的烏七八糟就沒個味道了!
在平樂鎮上,大概沒人不識春娟豆瓣廠廠長薛勝強吧!他是我爸爸,那真是有本事,天上飛的,地上跑的,黑白兩道沒有搞不定的。對婆娘更是像攪豆瓣似的得心應手,連二奶都能安頓在奶奶的同一棟樓裡。
直到那天爸爸忽然心臟病發,差點成了牡丹花下的風流鬼,嚇得二奶從五樓衝到三樓向奶奶求救,一切就此東窗事發!
適逢奶奶的八十大壽,這爛攤子就莫名其妙地收場了。全家人開始忙著搞壽宴,連去歐洲當教授的大伯、鬧離婚的姑姑都被找回來一起操辦,但爸爸夢都夢不到,一家子各有各的心事。偏偏就在壽宴彩排時,所有計謀、盤算、秘密,像算準了時辰的炸彈,一股腦地爆開來……
薛勝強的怪話精選
‧平樂鎮真是屁股樣個地方,人人嘴巴還臉盆那麼大。
‧算逑了,就是個婆娘嘛。
‧心妖作怪要過什麼生,弄得雞飛狗跳的。
‧哪個砍腦殼的亂翻嘴?
‧哪個敢管今天老子就喊哪個吃不到兜著走!
‧都是四十幾歲的人了,社會上吃得溜轉了,夜總會裡也一起唱過歌,喝過酒,耍過小姐了──一句話,都是男人嘛!
‧真的是把老子當悶豬兒在整哦!
‧老子這輩子啥大風大浪沒見過!老子還怕錘子!
‧心妖作怪要過什麼生,弄得雞飛狗跳的。
各方推薦
★苦苓 自由作家、張國立 作家、戴立忍 導演 幽默推薦!
我愛《我們家》!故事非常生動有趣,並且超級感人。你很難忘記這家人的故事,因為他們是如此活靈活現。 ——Anke Goebel,德國藍燈書屋編輯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我們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24 |
小說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小說 |
$ 288 |
小說 |
$ 288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我們家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顏歌
本名戴月行,1984年出生於中國四川。
十歲開始出版第一本作品,曾榮獲由中國小說協會、中國散文學會等學會主辦的「第四屆中國少年作家杯全國作文大賽」一等獎。2004年被《羊城晚報》隆重推為最具影響力的十大「80後」作家之一。在網路的人氣與張悅然、郭敬明不相上下!
文風變化多端,早期的作品偏於空靈飄逸的浪漫唯美派,後期則轉變為簡潔白描的文字、現實和虛構交織的風格,對人性有非常獨特犀利又多面的比喻。目前有包括《陶樂鎮的春天》、《五月女王》等十本作品。另有短篇作品散見於《收穫》、《人民文學》、《作家》等雜誌。
2011至2012年在美國杜克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時,完成廣受好評的長篇小說《我們家》,並獲得2013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新人獎;新作《平樂鎮傷心故事集》獲選亞洲周刊2015年十大小說,是華文創作備受期待的青年小說家!目前定居都柏林。
作者微博 tw.weibo.com/yangemay
作者部落格 site.douban.com/110350/
顏歌
本名戴月行,1984年出生於中國四川。
十歲開始出版第一本作品,曾榮獲由中國小說協會、中國散文學會等學會主辦的「第四屆中國少年作家杯全國作文大賽」一等獎。2004年被《羊城晚報》隆重推為最具影響力的十大「80後」作家之一。在網路的人氣與張悅然、郭敬明不相上下!
文風變化多端,早期的作品偏於空靈飄逸的浪漫唯美派,後期則轉變為簡潔白描的文字、現實和虛構交織的風格,對人性有非常獨特犀利又多面的比喻。目前有包括《陶樂鎮的春天》、《五月女王》等十本作品。另有短篇作品散見於《收穫》、《人民文學》、《作家》等雜誌。
2011至2012年在美國杜克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時,完成廣受好評的長篇小說《我們家》,並獲得2013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新人獎;新作《平樂鎮傷心故事集》獲選亞洲周刊2015年十大小說,是華文創作備受期待的青年小說家!目前定居都柏林。
作者微博 tw.weibo.com/yangemay
作者部落格 site.douban.com/110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