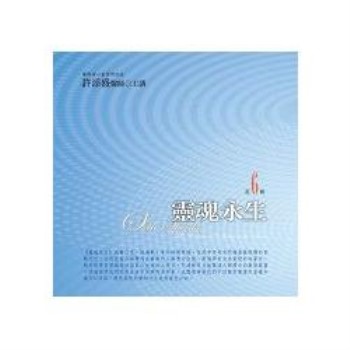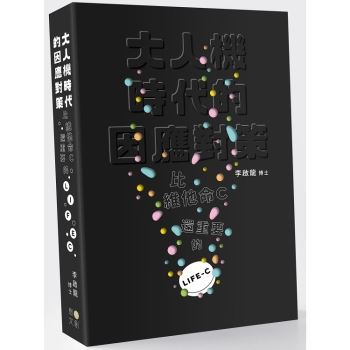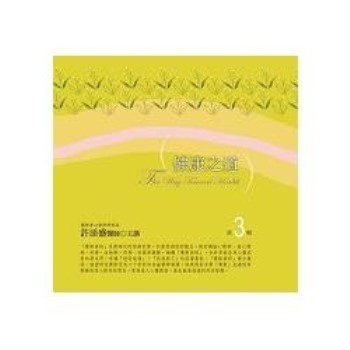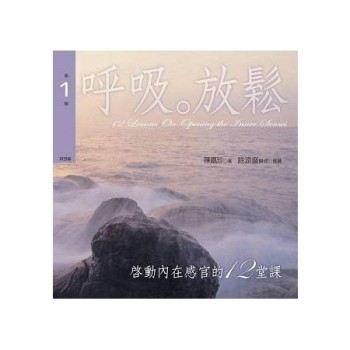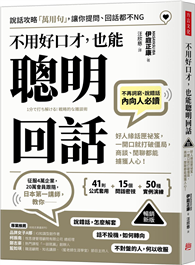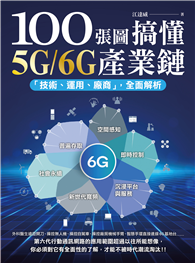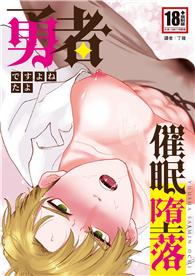100歲冥壽的作者,80年前的回憶,50年前的作品,場景橫跨3地,歷經2度出版,卻又塵封20年,這,就是《前夜》。
林衡道的創作動機,是為下一代留下歷史見證。因此《前夜》可視為一本半自傳。全書以林衡道本人的經歷為基底,描繪日治時期上層權貴的利益糾葛和紙醉金迷,深刻道出臺籍知識份子受殖民統治,宛若次等公民的無奈與掙扎,也真實呈現1937-1945年間,中日戰爭下的眾生相。《前夜》宛若一部紀錄片,讀者可與林衡道一同重回上個世紀,與故事主角穿梭在臺北、東京、神戶、上海等地的街頭,身歷其境地感受時代洪流。
《前夜》作為林衡道系列的首部作品,榮獲李乾朗、戴寶村和凌宗魁等專家學者推薦,同時收錄林衡道的大事記和珍貴相片,盼能以系列作品讓世人重新認識「臺灣古蹟仙」──林衡道。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前夜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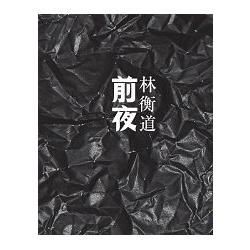 |
前夜 作者:林衡道 出版社:德屹科技創意有限公司(一本文化) 出版日期:2015-10-2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76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前夜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衡道
林衡道(1915-1997),生於日本東京,父親是臺灣五大家族之一,板橋林家本記第五代的林熊祥,母親為福州名儒,曾任溥儀太傅的陳寶琛之女。
有「末代少爺」之稱的林衡道,雖畢業於仙台東北帝國大學經濟學科,卻一輩子醉心於文史領域。不僅出任省文獻會主委,也為臺灣文物保存貢獻心力,長年提著白蘭洗衣粉袋、穿著樸實的皮鞋,在各地尋訪名勝古蹟,因而獲得了「臺灣古蹟仙」的美譽。此外,林衡道對文學領域也有諸多涉獵,而《前夜》,正是林衡道眾多著作中難得的小說體裁創作。
林衡道
林衡道(1915-1997),生於日本東京,父親是臺灣五大家族之一,板橋林家本記第五代的林熊祥,母親為福州名儒,曾任溥儀太傅的陳寶琛之女。
有「末代少爺」之稱的林衡道,雖畢業於仙台東北帝國大學經濟學科,卻一輩子醉心於文史領域。不僅出任省文獻會主委,也為臺灣文物保存貢獻心力,長年提著白蘭洗衣粉袋、穿著樸實的皮鞋,在各地尋訪名勝古蹟,因而獲得了「臺灣古蹟仙」的美譽。此外,林衡道對文學領域也有諸多涉獵,而《前夜》,正是林衡道眾多著作中難得的小說體裁創作。
目錄
我讀「前夜」…………………………………………………003
緬懷古蹟芬芳──追懷博學多聞的古蹟仙…………..………007
前夜……………………………………………………………014
後記……………………………………………………………304
林衡道大事記…………………………………………………307
編輯室手札……………………………………………………314
緬懷古蹟芬芳──追懷博學多聞的古蹟仙…………..………007
前夜……………………………………………………………014
後記……………………………………………………………304
林衡道大事記…………………………………………………307
編輯室手札……………………………………………………314
序
推薦序
緬懷古蹟芬芳──追懷博學多聞的古蹟仙
林衡道先生在關心臺灣鄉土文化的人心中,是一位古蹟專家,他早在一九五○年代即投入心力調查研究臺灣的民俗掌故與各地的名勝古蹟,他的研究方法最令人敬佩的是用腳力走遍大小鄉鎮,特別是窮鄉僻壤的小巷,將幾乎被人遺忘的古厝、古廟發表在《台灣文獻》刊物上,他將書籍記載的歷史文獻與現場可觸摸的實體古蹟連結起來。一九八○年代,當時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開始對全臺的古蹟作評鑑,林老師不辭辛勞地到現場勘查。因此可以說,今天臺灣所指定的主要古蹟,大多數經過林老師的慧眼加以品評鑑定。
林老師不是坐在書桌前或埋首圖書館的學者,他是以雙眼與雙腳來作學問,因而也啟動了古蹟之旅的風氣。有許多學校的社團或社會上喜好文史的朋友,相繼邀請林老師利用假期安排行程,坐大巴士到中南部遊覽古蹟,可謂開啟知性遺產之旅的先河。他那臺灣古蹟百科全書式的講解風格,既博學又幽默,人們因而尊稱他為﹁古蹟仙﹂。甚至國防部的軍隊莒光日教育課,也聘請林老師上電視臺教學,他講述臺灣古蹟與中國歷史密不可分的關係,符合當年國防部的政治目標。
熟悉林老師的人都認為他雖出身板橋林本源富豪家庭,但其成長、受教育與社會歷練皆非常人能比。他個性天真,為人親切又平易近人,實踐富而好禮的處世精神。聽他講課或介紹古蹟,可以獲得書本裡找不到的知識,他常說「歷史記載是假的,小說陳述才是真的」,因為歷史經常是刻意修飾的產物,小說描述的才是真實人生。在勘查古蹟的巴士中,他從不休息睡覺,反而對著同行的人述說他一輩子精彩而豐富的經歷,從一九二○年代開始,福州、臺北、東京、仙台、紐約、上海、蘇州及南京等城市都有他的蹤跡,他的故事真是說也說不完,聽他講
故事真是一種享受。
林老師多采多姿的經歷,是伴隨著大時代的歷史發生的。他所處的大時代是亞洲面臨大風暴的時代,從一八九五年乙未割臺,臺灣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臺灣首富板橋林本源家族面臨了複雜的歷史抉擇。而在日本殖民五十年中,林老師得到高等教育薰陶,他為家族企業學習經濟學,但興趣卻是文學與歷史。他一輩子不能忘懷的是文學,中西歷史名著及大文豪的小說皆有涉獵。日本的詩歌也是林老師熟悉的領域,他曾在淡江大學日文系講授日本文學。無奈造化弄人,他沒有走上成為文學家的路,反而從商從政,但其內心深處,對文學的熱情並沒有完全熄滅。終於,誕生了這本小說《前夜》,讀這篇小說的人一眼就明白,小說鋪陳的即是日治時期臺灣富豪家庭的矛盾與處世之道,明顯影射當時臺灣上流社會的某些家族。小說中寫到的大稻埕建昌街、鐵道飯店、北門、市役所、北投、松山等都是臺北真實的場景,也是林老師最熟悉的地方,以這些地點作為小說的背景,更是反映了一些實虛相生的情節。如果運用這些場景,其實可以拍攝出一部動人的紀錄片。
但林老師畢竟還是樂觀的,他的小說以《前夜》為名,暗示著「前夜雖然漫長,但破曉終會到來」。我其實並非林衡道老師教授過的學生,但有幸經由古蹟連結,長期請教他關於臺灣古蹟史事,受益匪淺,於是跟著大家尊稱他為老師。經由拜讀過他大部分的著作,包括《台灣勝蹟採訪冊》、《台灣的歷史與民俗》、《台灣公路史蹟》、《鯤島探源》、《台灣的寺廟》等,我們吸收了他寶貴且獨到的觀點,例如他認為一九三○年代間興建的臺北郵局、中山堂及臺灣大學校園建築等多用的淺綠色或褐色面磚,被稱為國防色,具有防空保護色作用,為戰時體制之一環,屬於真知灼見,令我每次走過中山堂及臺北郵局,就會想起侃侃而談的林老師。他常說很欣賞大正民主時期的建築,例如公賣局、鐵道飯店、鐵道部等,這些紅磚建築都接近英國式,反映較自由的氛圍。
一九八○年代,文建會展開古蹟勘查與鑑定工作,我們一群歷史與建築的研究者們有幸跟隨前輩,可謂無役不與,回想起來,現在文化部古蹟有關業務之奠定基礎,實得助於林衡道教授。如今林老師與同輩份的楊雲萍先生、陳奇祿先生皆已作古,回憶他們為臺灣文化所作之貢獻,並熱心提攜後進,令人更感到典型在夙昔之風采。二○一五年是林老師百歲誕辰,欣逢林老師的小說《前夜》重刊面世前夕,殊為難得。先前之版本,我尊敬的陳三井教授已有精闢的推薦序文,我不揣淺陋的寫此追憶感言,實不敢稱序,而是藉此緬懷林老師精彩的一生,祈請讀者諒察賜正。
緬懷古蹟芬芳──追懷博學多聞的古蹟仙
李乾朗
林衡道先生在關心臺灣鄉土文化的人心中,是一位古蹟專家,他早在一九五○年代即投入心力調查研究臺灣的民俗掌故與各地的名勝古蹟,他的研究方法最令人敬佩的是用腳力走遍大小鄉鎮,特別是窮鄉僻壤的小巷,將幾乎被人遺忘的古厝、古廟發表在《台灣文獻》刊物上,他將書籍記載的歷史文獻與現場可觸摸的實體古蹟連結起來。一九八○年代,當時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開始對全臺的古蹟作評鑑,林老師不辭辛勞地到現場勘查。因此可以說,今天臺灣所指定的主要古蹟,大多數經過林老師的慧眼加以品評鑑定。
林老師不是坐在書桌前或埋首圖書館的學者,他是以雙眼與雙腳來作學問,因而也啟動了古蹟之旅的風氣。有許多學校的社團或社會上喜好文史的朋友,相繼邀請林老師利用假期安排行程,坐大巴士到中南部遊覽古蹟,可謂開啟知性遺產之旅的先河。他那臺灣古蹟百科全書式的講解風格,既博學又幽默,人們因而尊稱他為﹁古蹟仙﹂。甚至國防部的軍隊莒光日教育課,也聘請林老師上電視臺教學,他講述臺灣古蹟與中國歷史密不可分的關係,符合當年國防部的政治目標。
熟悉林老師的人都認為他雖出身板橋林本源富豪家庭,但其成長、受教育與社會歷練皆非常人能比。他個性天真,為人親切又平易近人,實踐富而好禮的處世精神。聽他講課或介紹古蹟,可以獲得書本裡找不到的知識,他常說「歷史記載是假的,小說陳述才是真的」,因為歷史經常是刻意修飾的產物,小說描述的才是真實人生。在勘查古蹟的巴士中,他從不休息睡覺,反而對著同行的人述說他一輩子精彩而豐富的經歷,從一九二○年代開始,福州、臺北、東京、仙台、紐約、上海、蘇州及南京等城市都有他的蹤跡,他的故事真是說也說不完,聽他講
故事真是一種享受。
林老師多采多姿的經歷,是伴隨著大時代的歷史發生的。他所處的大時代是亞洲面臨大風暴的時代,從一八九五年乙未割臺,臺灣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臺灣首富板橋林本源家族面臨了複雜的歷史抉擇。而在日本殖民五十年中,林老師得到高等教育薰陶,他為家族企業學習經濟學,但興趣卻是文學與歷史。他一輩子不能忘懷的是文學,中西歷史名著及大文豪的小說皆有涉獵。日本的詩歌也是林老師熟悉的領域,他曾在淡江大學日文系講授日本文學。無奈造化弄人,他沒有走上成為文學家的路,反而從商從政,但其內心深處,對文學的熱情並沒有完全熄滅。終於,誕生了這本小說《前夜》,讀這篇小說的人一眼就明白,小說鋪陳的即是日治時期臺灣富豪家庭的矛盾與處世之道,明顯影射當時臺灣上流社會的某些家族。小說中寫到的大稻埕建昌街、鐵道飯店、北門、市役所、北投、松山等都是臺北真實的場景,也是林老師最熟悉的地方,以這些地點作為小說的背景,更是反映了一些實虛相生的情節。如果運用這些場景,其實可以拍攝出一部動人的紀錄片。
但林老師畢竟還是樂觀的,他的小說以《前夜》為名,暗示著「前夜雖然漫長,但破曉終會到來」。我其實並非林衡道老師教授過的學生,但有幸經由古蹟連結,長期請教他關於臺灣古蹟史事,受益匪淺,於是跟著大家尊稱他為老師。經由拜讀過他大部分的著作,包括《台灣勝蹟採訪冊》、《台灣的歷史與民俗》、《台灣公路史蹟》、《鯤島探源》、《台灣的寺廟》等,我們吸收了他寶貴且獨到的觀點,例如他認為一九三○年代間興建的臺北郵局、中山堂及臺灣大學校園建築等多用的淺綠色或褐色面磚,被稱為國防色,具有防空保護色作用,為戰時體制之一環,屬於真知灼見,令我每次走過中山堂及臺北郵局,就會想起侃侃而談的林老師。他常說很欣賞大正民主時期的建築,例如公賣局、鐵道飯店、鐵道部等,這些紅磚建築都接近英國式,反映較自由的氛圍。
一九八○年代,文建會展開古蹟勘查與鑑定工作,我們一群歷史與建築的研究者們有幸跟隨前輩,可謂無役不與,回想起來,現在文化部古蹟有關業務之奠定基礎,實得助於林衡道教授。如今林老師與同輩份的楊雲萍先生、陳奇祿先生皆已作古,回憶他們為臺灣文化所作之貢獻,並熱心提攜後進,令人更感到典型在夙昔之風采。二○一五年是林老師百歲誕辰,欣逢林老師的小說《前夜》重刊面世前夕,殊為難得。先前之版本,我尊敬的陳三井教授已有精闢的推薦序文,我不揣淺陋的寫此追憶感言,實不敢稱序,而是藉此緬懷林老師精彩的一生,祈請讀者諒察賜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