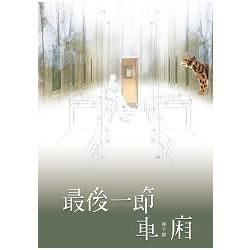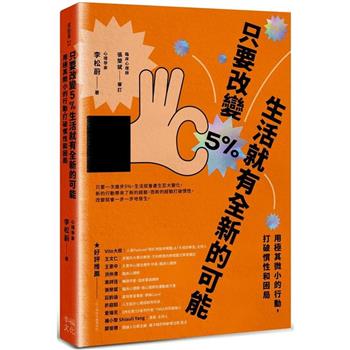推薦序
在充滿回憶的平原中
多年以後,臉書在地球上消失了,我依然會記得,每當瀏覽臉友近況時,會特地點入謝予騰,讀那直言不諱的日記:一、二、三,漫談切身瑣事、評論新聞事件、反思文學文化,或單單純純就是一首詩。
人總將當下的感官知覺習常化,如火車頭,朝鐵軌於遠方交錯的那個點前進,匆忙急躁間,常忽略拖曳在後的車廂,沉甸甸的習以為常,那就是回憶,就是《最後一節車廂》,讓我回首憬悟,回到那時間可大把大把揮霍的年少,困守不城不鄉的小市鎮,腔口桀驁不馴,態度無所謂,口氣直率──而予騰比我更直接,接到球就傳,有想法就迸,準確、俐落、轉瞬即發。
這本小說集中的人物,有業務員、學生、原住民、中心打者、女友/砲友與主述者自己,絕非英雄偉人也沒那麼邊緣弱勢,人生轟轟烈烈不起來,虛無是虛無,難以提升至哲學的高度。住在無聊的小城市、破碎的郊區、灰澹的鄉野,驚喜與歡欣撩不起,連厭惡都懶得生成,如同省道呼嘯而過的車聲,百無聊賴⋯⋯可有可無的學位、欲振乏力的業績、浪蕩無頭的青春,在人生的匝道,他們相遇了,猶如一堆數字的聚合,生與死如此輕易,愛與性可有可無,這是齣衰敗島嶼公路電影,窗景浮現Motel與加油站,間雜農田與鐵皮屋,荒蕪空洞路迢迢,那些怠速的心靈,不知要在哪個交流道下去,反正死路一條,索性「逆向而行」,將虛無飆至極速⋯⋯
連罵髒話的力氣都沒,危機就懸在那兒,無法落地。
予騰乃詩人出身,已出版《請為我讀詩》、《親愛的鹿》兩本詩集,精妙的描繪與比喻,在這本小說集青筋浮現,有時俚俗、或者親切、常是活跳的、更是深情隱含寓意。不僅只字句段落,予騰在敘述手法與結構上,交雜心理與現實、人物與象徵,形成迷離的氛圍,現實與想像取消了分隔,如〈死訊〉,主角成為獵物,而讀者也成為作者的獵物,物我不分,悵惘惚恍⋯⋯
〈最後的打席〉真是雷霆萬鈞,轉動日本漫畫的節奏,繃緊美國職棒之大肌肉,以細密的描繪鋪底,只是一個打席!只是一個打席!短短幾分鐘,每一球都讓人喘不過氣來──最終結局,棒子擊中球那「鏗」一聲,依然迴盪在我的耳蝸中。
不知文學安拜(empire)是如何判決《最後一節車廂》的,我這個比予騰資深一點的老鳥,若要勉勵,就是期待予騰不僅憑靠血氣與蠻勁,而能多琢磨球路。你看大聯盟投手不只滑球與曲球,軌跡的變化已經無法迷惑怪獸般的打者,而要使出多種變速球,利用速度的落差,讓打者揮棒落空。也就是:
在這個沒有對與錯的世界,沒有誰能替誰負責的這個世界,就和球一樣,不斷不斷的一直轉動著。
予騰與我,出生且成長於臺灣南部,如同平原上眾多的創作者,正飽蓄著能量,用文字、圖像與戲劇日夜轉動創作⋯⋯在這片處處充滿回憶的平原,搭乘《最後一節車廂》,耳聽熟悉的語言、欣賞流逝的風景、捕捉變化的光影⋯⋯
然而,車廂密不透風,就快要無法呼吸。
打破滯悶,請讓平原的遼闊,全面展開。
鄭順聰(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