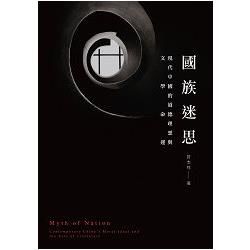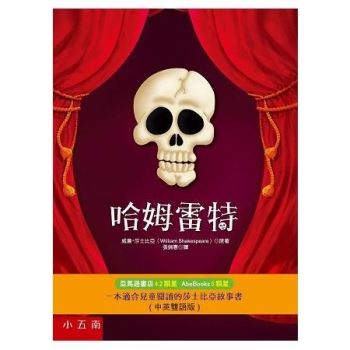緒論
日本學者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1941- )在1970年代後期注意到,日本的「『現代文學』正在走向末路,換句話說,賦予文學以深刻意義的時代就要過去了。」而在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大陸,逐漸擺脫了為意識形態服務的當代文學同樣也「似乎已經失去了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不過,似乎也沒有必要為此惋惜,因為當「這個現代文學已經喪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壞力量,成了國家欽定教科書中選定的教材,這無疑已是文學的僵屍了」。如果文學的「末路」是從這個方面說的,就意味著文學本身不會走向消亡。在一百多年前,對於「不攖人心」的傳統詩學早已失望的魯迅在西方的摩羅詩人那裡,發現了詩歌具有一種反抗挑戰、爭天拒俗的精神力量,因而寄希望於「摩羅詩力」,「來破中國之蕭條」。在此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也正是在一種質疑舊文學語言道統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基調中確立了現代中國文學的新傳統。在這樣承載著啟蒙使命與道德理想的變革語境中,中國新文學比之後來的文學,在道德理想方面顯得更為自覺與沉重。
美國學者詹姆遜(Fredric Jameson,1934- )曾提出一個備受爭議的假說:「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學均帶有寓言性與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些本文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力比多趨力的本文,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這種虛構第三世界文學的假說自然不難找到反證,其中所隱含的第一世界霸權腔調也自然會遭到反殖民主義者的強烈反彈。不過,反顧近現代中國文學史,在危機重重的年代,無論是「為人生」,還是「為藝術」;是「人的文學」,還是「性靈文學」;是啟蒙為旨,還是革命為綱,總是無法擺脫一種國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儘管在1930年代,左翼陣營和右翼文人在民族主義問題上曾交戰不休,但反抗也好,迎合也好,都表露出一種中華文化傳統血脈中過於深沉的家國情懷與骨子裡過於沉重的道德使命感。可見,「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雖然語氣絕對,但如果沒有「總是」一類的措辭,西人/胡人的假說其實也並非一派胡言,一無是處。
自晚清以來,中國頻頻遭遇東西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在危機時代中孕育發生的現代文學,自然格外有一種夏志清(1921-2013)教授所說的「感時憂國」精神。不過,夏先生也指出,現代中國文學雖然蘊含著與西方現代文學一樣的民主與科學嚮往,但中國現代作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爾斯泰、湯瑪斯‧曼等人,是「熱切地去探索現代文明的病源」,而是「非常感懷中國的問題,無情地刻畫國內的黑暗和腐敗」。因此,中國作家的展望很少逾越國家範疇,從未把中國的特殊困境視為一種現代世界的普遍病症。這種流於「狹窄的愛國主義」限制了現代作家的世界視野與探索勇氣。愛國主義當然無可厚非,但愛國主義流於狹隘,就會陷入一種國族主義的迷魅。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視野來看,國族迷魅不僅規定著現代中國的文學精神與視野,而且困擾著現代中國的詩學選擇與命運。現代文學回應國族主義的徵召參與強國救種、救亡圖存的現代化議程,其道德勇氣與愛國熱忱無論如何都需要高度肯定,吊詭的是,不同的詩學選擇往往殊途同歸,如同魯迅所感歎的「彷彿思想裡有鬼似的」,最終在與國族政治的糾纏中陷入一種同樣沉重的命運。對現代作家來說,國族主義釋放了他們的道義情懷,也壓抑了他們的文學才華。在發揚一種愛國熱情的同時,現代中國的詩學精神也滿涵著一種道德焦慮,乃至背負著一種道德陰影。本書選擇性別與國族、啟蒙與救亡、左翼與革命、新詩與現代等幾種不同議題,探討不同派別的文學選擇在國族政治中的命運浮沉。從晚清時期的秋瑾(1875-1907),到五四時期的丁玲(1904-1986),從留日時期的魯迅(1881-1936),到抗日時期的周作人(1885-1967),從青春時期的左翼文人,到歷經生死的九葉詩派,他們的悲壯與艱辛,苦澀與掙扎,理想與困頓,沉潛與昂揚,牽扯著近現代史上一條曲折動盪的文學線索,也折射出國族政治背後豐富複雜的詩學寓言。
與前現代的中國傳統文人、後現代的中國當代作家相比,現代中國的文學者是一群身份、角色認同更為複雜,責任、使命意識更為強烈的知識份子。他們不僅僅從事文學活動,而且也不願意僅僅以文學創作為滿足,他們在寫作之外,教書辦報,走上街頭,到民間去,組織社團,參加政黨,與啟蒙、革命、救亡等不同時代的文化思潮發生了種種衝撞,摩擦出了種種火花。在道術為天下裂的現代中國,他們視「倫理的覺悟,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賦予了自己的文學創作一種強烈的道德使命感,一種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也因此,他們在各自的詩學選擇中,追尋著不同的文學理念,也遭遇了不同的人生命運。
在社會角色與責任意識上,知識份子無論是知識的創造者還是傳播者,無論是道德的立法者還是闡釋者,也無論思想信仰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之間又有怎樣的分歧,文學與道德作為精神生活的一體兩面,始終是他們關注的基本問題。從魯迅在1908年提出「立人」主張,周作人在1918年提出「人的文學」以來,現代文學者的寫作理念就一直閃耀著著道德理想的光芒,而他們的文學創作就是一種道德理想的具體實踐。魯迅從留日時期就在呼喚中國的「摩羅詩人」與「精神界之戰士」,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則在某種意義上回應了魯迅孤獨的吶喊。「五四」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一大批以思想啟蒙為使命的現代文藝青年。這是一群在漆黑漫長的暗夜中開始獨自覺醒、並試圖喚醒其他沉睡者的人,一群飽受暴風雨的無情打擊卻始終在仰望星空的人,一群流浪於荒原之上卻始終沒有放棄行走的人。在現代中國,滿懷新文學道德理想的正是這樣一群新生的人,所遭遇的也正是這樣一種險惡的環境。他們為此做出了自覺的選擇,也為此判決了自己的命運。在權力的迫害中輾轉流徙的魯迅所描繪的那位走在茫茫荒原上的「過客」是現代中國文學者的普遍象徵:聽從心中的命令,卻無法看到前途;但無論現實如何讓人絕望,卻依然心存嚮往。也因此,反抗絕望的現實體驗讓魯迅真切地感受到了「真的知識階級」在中國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在經歷了清黨運動的白色恐怖後,他在1927年發表演講說:「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厲害的」,「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這是一個堅持自由思想與批判精神的文學者對於現實政治的敏感與自身命運的殘酷預言。而魯迅同時代的文學者及其後來者,以良知的堅持與命運的磨難,見證了魯迅身後比預言更為殘酷的現實。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是:不同立場的中國新文學者為什麼會在不同時期、不同年代懷念曾經經歷或未曾經歷的「五四」,為什麼都有一種化解不開的「五四」情結?而「五四」又為什麼會成為張愛玲(1920-1995)所說的一種「民族回憶」的東西,一種時間也無法湮沒的「思想背景」?這大概是因為,「五四」被新文學者賦予了一種普遍而神聖的意義,對以「新青年」為象徵的知識人來說,「五四」就是以自由思想、批判精神為基本價值的現代知識份子的降生日,是以民主觀念、科學精神為基本內涵的現代思想的耶誕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段極為短暫的歷史,但卻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自由與個性最為解放的時期。它的歷史是短命的,影響卻是長久的。不論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來排斥它,改造它,扭曲它,篡改它,其所宣導與張揚的自由精神、人權意識、科學觀念、民主思想都無法被遮蔽與掩蓋。而所謂的愛國觀念,如果缺乏獨立、自由、民主、人道的現代思想基礎,就會走向極權與奴役的反面,成為周氏兄弟在留日時期就極力駁斥的「獸性的愛國」。這一點,陳獨秀(1879-1942)在《新青年》時期的文章〈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也有過相當清楚的辨析,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這樣的愛是具體的和理性的,不是抽象的和狂熱的;是寬廣的人類情懷,不是狹隘的族群利益。
「五四」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內心縈繞不已的共同情結,同時也還有著一種現實的追懷與受難意識。中國現代文學界並不缺乏優秀的思想者,只要有一點陽光,他們的思想同樣會燦爛地綻放。可惜的是,他們生存的空氣過於潮濕與陰暗。在有著幾千年封建帝制傳統的中國,權力的形式在翻雲覆雨的鬥爭中不斷更迭,權力的性質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因此,思想可以自由爭鳴的黃金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一個是先秦的諸子百家爭鳴,一個就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它們的歷史都很短暫,生長在權力鬥爭夾縫間的思想運動註定不會長久,一旦天下一統,王官之學恢復,自由思想就會被權力所絞殺,思想的百家爭鳴就會重回定於一尊的中世紀傳統。也因此,西方思想界在自由爭鳴與持續批判中,出現了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爾、尼采的群星璀璨、大家輩出的景象,在中國則永遠只有一位孔子配吃皇帝的冷豬肉,是只許一家獨尊,不容二日並出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知識份子是最為不幸的一群。他們經歷著世界上最為漫長與黑暗的中世紀歷史,雖然也創造出了燦爛的思想文化與文學經典,可那需要為正義與尊嚴付出怎樣沉重的代價。從屈原的自沉汨羅,到司馬遷的慘遭宮刑;從魏晉名士嵇康的廣陵散絕,到明清兩代多如牛毛的文字獄;從陳獨秀「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髮老書生」的獄中賦詩,到後來反右運動、文革時期更大規模的思想冤獄……一部中國文學史,實際上也是一部詩人的精神史與受難史。早在1940年代,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的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就預感到中國知識界不太樂觀的命運。他在1943年致柯里博士的信中說:中國文化人「正在極其耐心地等待著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那種百家爭鳴、自由講學的好時光的再次來臨。事實上這種好時光可能永不再現了」。從這一方面說,詩人懷念「五四」時代,是因為他們永遠地失去了這個可以自由思想的時代,也是因為他們在失樂園後仍然沒有放棄告別中世紀的永恆夢想。
與「五四」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新文學者為什麼會在不同時期、不同年代提到魯迅,為什麼會被稱作現代中國文學的教父?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有爭議的人物,也是後來的歷史無法繞過的人物。人們提及他,無論是認同,還是不認同,是讚美,還是貶斥,都要把他和「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掛起鉤來,把他與左聯時期的革命文學掛起鉤來。他會成為革命文學首當其衝的祭旗對象,也會成為左翼文學首當一面的精神旗幟。他欣然遵從啟蒙運動主將的命令,不惜為自己絕望的文學裝點希望的花環;也堅決反對左聯元帥、革命工頭的話語霸權,即使他已經獲得一種旗幟的尊奉與榮寵。無論是親近還是疏遠,是攻擊還是拉攏,他似乎都永遠是風暴的中心,都是最不合時宜、又最合乎不同需要的人物。他的思想貫穿了一個時代,也影響了一個時代。有爭議的人物不是最完美的,卻也是最真實的。魯迅扭曲的文字是那個扭曲時代的產物,用這扭曲的文字,他最大程度地挖掘出了時代的精神真相,最大限度地表達了自由思想的要求。即使在晚年屢屢受到蘇俄革命宣傳的欺騙,我們也能從那被騙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種寧願自己受騙、也不放棄人類理想的善良與真誠。他的文字至今還有人願讀,我想就在於其中有真實,也還有我們當代人實際的生活感受:「夜正長,路也正長。」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1908-1977)說:在魯迅那裡,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線索」,對所有通過閱讀魯迅來閱讀自己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普遍的內心感受。
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另一個讓人倍感沉重的問題是,除了個別善於變化的「聰明人」外,為什麼堅守自己文學理想的作家所遭遇的都是一種悲劇命運?在他們當中,有堅持啟蒙的獨立思想者,有呼籲民主的激進思想者,有讚美革命理想的左翼文人,有將人性作為神廟的自由文人,卻無一例外地以理想開始,以悲劇告終。魯迅把中國歷史看作是中國人做奴隸是否安穩的宿命迴圈,周作人則在中國的現實中常常感到一種歷史「重來」的鬼影,是有著自己深刻的現實體驗的。魯迅在《醉眼中的朦朧》一文中將文人的思想交鋒稱為「紙戰鬥」,是一個形象的說法。文人的思想表達離不開紙頁,也是以紙頁文字來發揮道德影響力的。在民主意識完全真空的年代,他們的思想權利沒有權杖可以保護,也沒有刀槍可以依靠。在紙頁上,他們擁有思想之內的力量,在紙頁下,他們無法擁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尤其在迷信權力與尊崇正統的中國思想語境中,自由思想不會擁有真正的生存空間,知識不會得到真正的尊重,詩人也不可能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位置。魯迅在1933年曾為自己的小說集《吶喊》題詩云:「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大約半個多世紀後,魯迅的一位經歷了政治運動災難的青年朋友聶紺弩(1903-1986)也留下了同樣感慨萬千的詩句:「多文為富更多情,心上英雄紙上兵」。寥寥數語,道盡了文學者在希望與絕望間的無數艱難與辛酸。經歷了《新青年》同人李大釗(1889-1927)被軍閥絞殺的事件與血腥恐怖的清黨運動後,周作人從西哲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那裡所借用的「思想的蘆葦」的說法,是中國文學者實際位置與命運的最好寫照。然而,思想者不掌握可怕的權力,卻會揭露出可怕的事實。他們的肉身會被悲劇時代的戰車瞬間碾碎,他們的思想卻會讓經歷了悲劇時代的人永遠刻骨銘心。
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在《存在與虛無》一書中指出,悲劇與史詩是一體化時代的產物。在現代中國威權統治的一體化時代,鮮有史詩性的文學,卻多有史詩性的悲劇。在法國大革命走向混亂與恐怖的時候,啟蒙主義的批評者「從過時的杞人憂天者轉變為有遠見的先知」。很多年後,我們在魯迅的雜文裡,在穆旦的詩歌裡,在沈從文的憂慮裡,在食指的「相信未來」中,在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中,在無數個民間傳抄與秘密收藏的地下文學中,處處可以找尋到一種在當時看來幾乎是杞人憂天的語言。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警告極權主義者說,「當一個更高的權威可以剝奪我們言論或寫作的自由時,它不可能剝奪我們思想的自由。」正因為這樣,即便在魯迅所感歎的「無聲的中國」,我們仍能感到一種自由思想的力量在地層深處潛伏與流動,即便它所生存的空氣如此壓抑與難以忍受,即便它所生存的世界遍佈思想的異化與扭曲。暗夜中的中國產生了許多魯迅所憎惡的聰明人,也產生了一些像穆旦那樣不凋的智慧樹。聰明人為謀取現實利益,不惜放棄良知而順應時代,智慧者為堅持自己的獨立思想,則不惜受難而反抗時代。也因此,近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由秋瑾、丁玲、魯迅、胡風(1902-1986)、聞一多(1899-1946)、穆旦(1918-1977)這些思想受難者和殉道者所延續的精神譜系,而他們也以自由乃至生命的犧牲,見證了一個時代在「方生未死」之間的前進與掙扎,腐敗與墮落。
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在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這是一個革命家的理想,文學者並沒有如此旋轉乾坤的力量。文學的意義不在於解決什麼問題,它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解釋問題;文學也不負責提供答案,解答問題從來都不是文學能夠擔負的職責。但是,它至少可以為我們揭示一種文學世界的真實,開啟一扇走向精神永生的窄門。
在現代中國的文藝運動中,我們不能要求新文學者絕對正確,他們義無反顧地追求真理,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是真理的化身。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說得好:「人們同世界的接觸是短暫的、個別的和有限的,然而他們怎麼能夠懂得那麼多的東西?」魯迅的文學影響了無數的知識青年,但對有著強烈的中間物意識的魯迅來說,「肩住黑暗的閘門」和供人踏越的「梯子」是他有意選擇的角色,「導師」、「偶像」之類都不過是「紙糊的假冠」。在有限的人類世界中,有限的人類只能產生有限的思想,當有限的思想一旦放置於無限誇大的時空,接受上帝般的信仰與崇拜,這樣的思想就會走向死亡與僵化,直至成為壓迫思想自由的教條與鎖鏈,或者淪為意識形態的清算與鬥爭工具。當知識者一旦把自己視為絕對真理與正統權威的化身,即使他們曾經擁有自由思想,也註定會成為壓迫思想自由的幫兇。對於這一點,晚年胡適(1891-1962)在經歷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命運後有著痛心疾首的認識,他在為雷震(1897-1979)所辦的《自由中國》所專門撰寫的《容忍與自由》一文中指出:「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而絕對真理的思想方式一旦與絕對的權力相結合,就會發生絕對可怕的後果,給人類文明帶來極大的災難。遠如孔子(西元前551-西元前479)的儒學,講求忠孝節義的倫理道德本身沒有什麼錯,可一旦被皇權利用,成為定於一尊的儒教,就異化為一頭吞噬人性的禮教怪獸了。而西方普及公平正義與道德理想的基督教信仰一旦被尊為一種官方宗教,出現教皇的時候,迫害思想自由與科學精神的火刑柱與宗教裁判所也就隨之出現了。近如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人生而自由的思想與天賦人權的觀念,在法國大革命那裡卻演變為斷頭臺遍佈、血流成河的大混亂與大崩潰局面;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超人學說與強力意志,是希望人類獲得一種精神進化與提升,但在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的德國那裡,卻淪為一種釀造極權意識與種族滅絕的法西斯主義;馬克思的人類解放學說與自由平等理想,在史達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1953)的蘇聯那裡卻演變為一種殘害異己的大清洗與大屠殺。這播下龍種、獲得跳蚤的教訓在中西歷史上都是極為殘酷與沉痛的。正因為這樣,在史達林時期的大清洗曝光後,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從知識份子的責任出發,對知識份子從柏拉圖以來的哲人王夢想提出了質疑,他指出:知識份子應該明白自己也有「一無所知」的地方,「我們應當像蟑螂一樣,謹慎地探索前進的道路,努力獲知最本質的真理。我們應當停止扮演無所不知的預言家」。保羅‧約翰遜則從「千百萬無辜的生命犧牲於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計畫」中看到了知識份子的信仰狂熱與「理性的逃亡」,他提醒說,知識份子要「同權力杠杆隔離開來」,製造「正統思想」的意圖使知識份子變得十分危險,「其本身常常導致非理性的和破壞性的行為」。他因此告誡人們說:「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份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在現代中國文學者那裡,左翼文人的獻身精神足以讓人欽敬,其革命的非理性狂熱也足以讓人深思。其實,任何壟斷真理的思想都會帶來惡果,對於啟蒙運動也同樣如此。美國學者施密特(Schmidt. J.)告誡說:「如果啟蒙的夢想只是看到一個沒有陰影、把一切東西都沐浴在理性的光芒之中的世界,那麼這個夢想實際上就蘊含著一些不健康的東西:因為想看到一切東西就是想站在上帝的立場上,或者想站在圓形監獄的瞭望塔中衛兵的立場上。也許啟蒙運動教會我們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我們既不是神又不是從外面來巡視世界的衛兵,我們是從世界當中來說話的男男女女,必須鼓起勇氣來爭辯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魯迅與其時代的中國文人沒有寫出像雨果(Victor Marie Hugo,1802-1885)的《九三年》那樣的文學巨著,但他們所參與的文學運動,本身即留下了一幅類似「九三年」的歷史場景:革命與人道、理性與狂熱、自由與流血……道德理想的複雜糾葛與思想之間的衝突交鋒,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以這種方式發生過,也從來沒有如此尖銳而激烈過。
魯迅的英雄夢碎也許不應只是惋惜,在失敗體驗中魯迅更真切地認識了自己與社會的本相,也讓後來的我們能夠更真切地看到歷史與現實的本來面目。日本學者伊藤虎丸(1927-2003)在談到重寫文學史的必要性時指出:「書寫文學史的起點必須置於現在,尤其當置於對現在的不滿。歷史,不是從過去的『事實』中翻找出來的,而必須是在與『對現在的不滿』鬥爭中表現出來的。不是有了過去才有現在,而是有了現在才有過去」。歷史考證只是思想探尋的知識基礎。對於現代中國知識者的詩學選擇與命運的思考,還原歷史僅是一種手段,反觀「現在」才是真正的目的。
1989年學生運動之後,中國知識份子在1980年代重新積聚的「回歸五四」的啟蒙熱情與幻想再次以失敗而告終,宿命迴圈的中國文學界又一次進入了魯迅所感歎的那種或高升、或退隱、或前進的分化處境與歷史怪圈。《新青年》團體解散後,在空蕩蕩的戰場上,成為散兵游勇的魯迅感到無比孤獨與悲涼。對於「只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他並不稀罕,他的傷心在於,「同一戰陣中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剛剛被「熱情者們的同感」溫暖與激動起來的心,又不得不再次冰冷下去,重回「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的那種大孤獨與大寂寞。魯迅的文字意氣此後無比寒冷,多半還是因為對《新青年》與啟蒙運動心太熱或太熱心的緣故。如今,寫下這種感歎的人遠去了,連同他的時代。而「現在」,人們熱心的種種「頭銜」不一定是魯迅所在意的,魯迅所在意的啟蒙理想也不一定是人們所熱心的。對於當代文學從烏托邦主義走向世俗享樂主義,這樣的憂慮並不是情緒化的:「當代文化生活的重要標誌之一,卻是魯迅式的『有機知識份子』逐漸分化和退場,並最終把知識份子的文化活動改造為一種職業活動。職業化的進程實際上消滅或改造了作為一個階層的知識份子。」我不希望如此,但又疑心這是真的。
整整一百前,魯迅對現代中國的詩學精神發出了這樣的召喚:「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整整一百年後,魯迅的召喚能否讓現代文學走出迷魅,魂兮歸來,這需要每一個「現在」的人做出自己的回答。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國族迷思:現代中國的道德理想與文學命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66 |
華文文學研究 |
$ 300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42 |
文學作品 |
$ 361 |
華文文學研究 |
$ 361 |
華文文學研究 |
電子書 |
$ 380 |
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國族迷思:現代中國的道德理想與文學命運
1. 作者從性別、詩學、浪漫派、啟蒙、文學改革的各種角度,探討中國國族主義在其中發揮的影響與改變,讓文學與政治、社會之間的牽扯暴露無疑。
2. 從晚清開始的時間線依序而下,一併見證不同時期國族主義所對個人或團體產生的牽引,及其所造成的殊異結果。
3. 最終對於國族主義在中國文學界的影響,以雖然確實因此產生了輝煌的文學作品,但也給文學帶來陰影作為總結。
在危機時代中孕育發生的近現代中國文學,格外有一種「感時憂國」的精神。不過,愛國主義如果流於狹隘,就會陷入一種國族主義的迷思。從整體視野來看,現代文學在參與強國救種、救亡圖存的現代化議程中,其道德勇氣與愛國熱忱值得高度肯定,然而弔詭的是,不同的文學選擇往往殊途同歸,最終在與國族政治的糾纏中陷入一種同樣沉重的命運。
對現代作家來說,國族主義釋放了他們的道義情懷,也壓抑了他們的文學才華。在發揚一種愛國熱情的同時,現代中國的詩學精神也滿含著一種道德焦慮,乃至背負著一種道德陰影。
本書選擇性別與國族、詩學與實學、啟蒙與救亡、左翼與革命、新詩與政治等幾種不同議題,探討不同派別的文學選擇在國族政治中的命運浮沉。
作者簡介:
符杰祥
200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兼任中國魯迅研究學會理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等多項,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出版學術專著《文章與文事:魯迅辨考》等多部。
TOP
章節試閱
緒論
日本學者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1941- )在1970年代後期注意到,日本的「『現代文學』正在走向末路,換句話說,賦予文學以深刻意義的時代就要過去了。」而在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大陸,逐漸擺脫了為意識形態服務的當代文學同樣也「似乎已經失去了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不過,似乎也沒有必要為此惋惜,因為當「這個現代文學已經喪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壞力量,成了國家欽定教科書中選定的教材,這無疑已是文學的僵屍了」。如果文學的「末路」是從這個方面說的,就意味著文學本身不會走向消亡。在一百多年前,對於「不攖人心」的傳統詩學...
日本學者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1941- )在1970年代後期注意到,日本的「『現代文學』正在走向末路,換句話說,賦予文學以深刻意義的時代就要過去了。」而在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大陸,逐漸擺脫了為意識形態服務的當代文學同樣也「似乎已經失去了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不過,似乎也沒有必要為此惋惜,因為當「這個現代文學已經喪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壞力量,成了國家欽定教科書中選定的教材,這無疑已是文學的僵屍了」。如果文學的「末路」是從這個方面說的,就意味著文學本身不會走向消亡。在一百多年前,對於「不攖人心」的傳統詩學...
»看全部
TOP
目錄
緒 論
第一章 當性別遭遇國族
─近代中國的「西方美人」與文學寓言
一、前言:歷史交匯中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二、 蘇菲亞/茶花女的鏡像倒錯與「西方美人」的文化政治
三、「舉國徵兵之世」與晚清的蘇菲亞傳奇
四、「中國的文藝復興」與五四的茶花女故事
五、文武興替中的女性典型與歷史塑造
六、結語:秋瑾與丁玲「母女」兩代的文學寓言
第二章 當詩學碰觸實學
─教父魯迅的現代思想與文學態度
一、由「富強」而「立人」:魯迅現代思想的發生
二、由「心聲」而「立人」:魯迅啟蒙思想的詩學原理
三、「棄醫從...
第一章 當性別遭遇國族
─近代中國的「西方美人」與文學寓言
一、前言:歷史交匯中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二、 蘇菲亞/茶花女的鏡像倒錯與「西方美人」的文化政治
三、「舉國徵兵之世」與晚清的蘇菲亞傳奇
四、「中國的文藝復興」與五四的茶花女故事
五、文武興替中的女性典型與歷史塑造
六、結語:秋瑾與丁玲「母女」兩代的文學寓言
第二章 當詩學碰觸實學
─教父魯迅的現代思想與文學態度
一、由「富強」而「立人」:魯迅現代思想的發生
二、由「心聲」而「立人」:魯迅啟蒙思想的詩學原理
三、「棄醫從...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符杰祥
- 出版社: 秀威代理 出版日期:2015-08-26 ISBN/ISSN:978986918196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2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